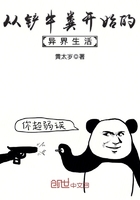“当阿育王石柱倒垂的莲花坠下,即是我要寻之人。”
“顶骨涌起,即是我要寻之人。”
“能躲我菩萨手段,即是我要寻之人。”
“圆满觉悟世间一切真理,即是我要寻之人。”
“可役使鬼神,即是我要寻之人。”
龙树菩萨圣心坚定,坐在禅床上,默念着到此世间的缘由。
这些话,龙树菩萨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了,自己可用的虽然就是其中的几句,但他还是每次都要念完全部。
阿育王石柱,在孔雀王朝立着,可照彻众生善恶之相,当然也包括佛陀本相,最高神自然也会映现。
龙树菩萨回忆与那个少年相遇的一点一滴,每个细节都被定格回放,手里的牌位自然不会放过,只是普通的木牌牌,上头铁钩银划刻着“东厨司命”,一个蕞尔小神,木牌牌上微弱的仙气缭绕,时断时续,可见接受的供奉太少,西塘灶君这么不受欢迎吗,龙树菩萨轻笑一声,没有嘲讽的意味,只是单纯的轻笑。
龙树菩萨这个段位,早已脱离了通过嘲笑别人给自己带来快乐的阶段。
他只是有些好奇,攥着牌位的那个少年,因为在他躲自己抚摸的手的时候,太蛇皮走位了,而且还是忍受了自己强大佛性的前提下的走位,龙树菩萨第一次对自身的佛性产生了怀疑。
虚空里龙树菩萨与药王菩萨会面。
“他躲了我一次。”龙树菩萨唇如频婆果色,面净如满月,身不倾动,身兼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只不过三十二相不太炽盛,不太分明,不太圆满,不太得处,比不得佛陀的比较炽盛,比较分明,比较圆满,比较得处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龙树菩萨记下了佛祖,决定深入接触,看是否是自己要寻之人。
“谁躲了你,龙树菩萨可是找到了吗?”
“只是觉得有趣。”
“有线索就好,总比我乱撞来的痛快,我在孔雀王朝快呆废了,今年的八百个新生儿我一个都没放过,可就是没有一个是的。”药王菩萨三指持药树,神情里满是无奈。
曾用雪山圣药供养比丘众僧,后听闻佛陀说法,成就菩萨果位。虚空内,两位菩萨现了本相,药王菩萨顶上肉髻有十四摩尼珠,珠有十四楞,楞间有十四华。他一手托着天冠,因其殊精微妙,非人间所有故称天冠,冠上有十方佛及诸位菩萨。
“药王菩萨,心生沮丧了吗?”龙树菩萨露出慈悲的微笑。
“沮丧倒不至于,就是有点怀疑,你说佛陀预言,到底真假?”药王菩萨摸着顶上肉髻,挠了两下,出于对佛陀尊重,重新戴上天冠。
“佛陀不会有错,更何况不是一位佛陀,只是我们还没找到。”
“新生儿都被我拎到阿育王石柱那里,去一次绝望一次,那些倒垂的莲花纹丝不动,我都想捶倒石柱,看那些莲花有没有掰断的可能。”药王菩萨又把天冠摘下,只见摩尼珠左右宛转。
“药王菩萨,你以医道成就菩萨果位,未来会成就佛果,为净眼如来,咱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界大劫,万不可意气用事。”
“佛陀预言,我将来能成佛,这话你信吗?我有多久没有下界了,受众生供养,却不曾广施药草,解除众生疾苦。这次下界,我怀着愧疚,治了许多宝宝恶疾。”
“你怎么巡视的都是初降生的婴孩,所有药铺你查了吗?”
“查了,没有任何消息。”
“西塘天台宗的老和尚焚身了?”
“焚身?”
“对,你的药王品做的孽。”
“哎,何苦呦,药王品可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
“就不该宣传你这事儿,搞的现在和尚一上头就玩火自尽。”
法华经是诸经之王,被誉为诸山中的须弥山,众星之中的月天子,诸小王中的转轮法王,三十三天王之中的帝释天,而药王菩萨本事品是法华经二十八品的其中一品。
药王菩萨曾燃指焚身,以供佛奉经,有天台宗的和尚,修法华的行者欲效法药王菩萨,燃臂焚身,不少人都真的这么干了。
“药王品,如清凉池,能满一切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裼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虽有如此种种好处,但不值得借鉴,真该把我那一品从法华经里删掉。”
“佛陀不会同意,这话以后少说,我只是知会你一声。”
……
沈从文天生一股书生意味,只是两道眉毛长残了,无限逼近发际线,好比是法国的伏尔泰,不在本国生活,老是流亡到国外。
米小烫每次看到表哥,总会调侃他的眉毛:“表哥,你这眉毛又稀了些。”
“你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女孩子有过节?”
“什么女孩子?”
“还装,是不是喜欢人家?”
“哪有。”米小烫拼命的想出一件抵抗鞋,给自己增加点韧性。
“表哥我都知道了,你喜欢大师姐纪犹行,不过情敌不少呢。”
“情敌什么的,我从来不放在心上。”
“等到纪姐姐被抢走,你再说这话吧。”
“我有把握追上她,其他人不足挂齿。”
“听说有个少年与纪姐姐青梅竹马,他是你的劲敌。”
沈从文知道佛祖对纪犹行不感兴趣,他们以姐弟相称,不过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俩人自从数年前,就不太亲近了,肯定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是大家不了解的,对于佛祖帮助那个施胖子的事,他就更不放在心上了,只要不是佛祖亲自下场争夺,沈从文有极大的信心打赢这场仗。
“你说佛祖啊,他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才华,把你拎出去挑战,你都能打败他,看你这小模样俊俏的,一定是新入书院的最美男子。”沈从文把佛祖贬低的一无是处。
当年佛祖的语文老师,说话必用成语,那个老师极为推崇蔡东藩,就是那个写了从秦汉到民国一部五百多万字的大部头书,接着批判当年的网络文学,说那些大部分是渣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牛骥同皂,三个差不多的成语被语文老师堂而皇之的引用着,并且以诗书传家嫉恶如仇的语文课代表没有反驳她,当时佛祖很失望。语文老师接着把哈洛卜伦评价托尔斯泰的话强行夺来,安插到蔡东藩头上,说他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如果真的按照语文老师说的那样,蔡东藩代替托尔斯泰去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结局肯定是这样的,还没轮到但丁与莎士比亚动手,蔡东藩就让荷马给挑死了。
世上总有那么一小撮无知且无畏的人,沈从文就是那个无知无畏中的一员。
他是真的不知道佛祖的强大。
他泡起妞来,令妞都闻风丧胆。
几家书院的学术交流还在持续,几位山长个个愁云惨淡,谈及先师,一个个唉声叹气。
倒是跟他们同来的弟子们,都很活泛,相互切磋,女的都被纪犹行发展成了闺蜜,男的被书院上舍修行者带着参观居室与平日里修行地,观夜山是必不可少的一处景观。
国朝四十年推行整个大陆的统一官话,这让说惯了西塘方言的土著们都不习惯,这对于佛祖来说不成问题,对于其他人来说要困难的多,那几家书院弟子一口标准的国朝官话,令人自叹弗如。
不过西塘土著们,很少有能流畅的用官话与其他书院的人交流的,私下里自然少不了人家的鄙视。
施施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对其他几家书院的女孩子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佛祖不知道他这算不算移情别恋。
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施施然心态的变化,那就是他开始学说国朝官话了。
国朝官话让浸淫十几年西塘方言的人来说,就好比是泰戈尔的诗用孟加拉文来念,具有很强的韵律感,但译到西班牙文或者匈牙利文乃至中文,读来就失掉了隐藏的那种流畅的节奏。
施施然讲的国朝官话总会带有浓重的西塘方言味,就像斯大林讲俄语时总会带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但施施然比斯大林更严于律己,几天后再听,施施然已经说的有模有样了,西塘方言偶有抬头的迹象,被施施然决然的用手指头摁下去。
草色还青,像一道道遒劲的生命,粲然一笑,豪迈不减,隐隐间声音全部遁去,世间一片空寂,极目处青山与云朵接壤,生出别样的蓬勃。
施施然自从可以吐字清晰的用官话阐述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没事就会往其他女弟子扎堆的附近那里溜达,故意高声与其他人交谈。
施施然并不能代表国朝官话在西塘普及的典型。
初皇以知闲校作为国都,把全国的多数富户迁到知闲校,知闲校的读书音被誉为国朝雅音,每次听到施施然怪异的口吻,佛祖都想捶死他。
“好好说话,西塘方言多好听呐,为了泡妞不至于这么努力吧。”
“佛祖,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种胖子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你如此用情不一,别说纪犹行了,就任何一个女孩子知道你这样都不可能答应同你在一起。”
“刺激你懂吗?”
“什么?”
“我自悟了一招,我找别的女孩子,你说纪犹行会不会吃醋,以前我只在乎她一人,突然有其他女孩子同她争抢我的爱意,她肯定心里不舒服不平衡,乃至对我产生别样的情愫,兴许就此以后,对我大为改观,不再对我爱答不理。”
“你想多了弟弟,人家顶多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不再对她热情,然后觉得你太容易被别的好看的女孩子勾搭走,人家只会暗地里松一口气,终于不再纠缠自己,她一定暗地里感谢那个抢走你目光的女孩子。”
“总要试试才行啊,不尝试一番,我心有不甘,沈从文与她日渐亲密,我再不反抗,那就压迫死了。”
“我觉得要打击对手,得先找到对方的短板,沈从文的软肋在哪,你熟悉他吗?”
“听闻他以前情史丰富。”
“这是一渣男啊。”
“何为渣男?”
“玩弄女孩子感情的就是。”
“那他就是渣男。”
沈从文没进书院之前换女朋友就像王维在七言乐府《桃源行》里换韵,那是无比频繁,王维在一首三十二句的诗里分别用了上平十一真韵、入声一屋韵、上平十三元韵、入声十四缉韵、上平十五删韵、入声十七霰韵、下平十二侵韵。而沈从文八岁拥有第一个女朋友童丫丫,九岁分手同年结交了一个叫张小朵的十二岁小姑娘,十三岁劈腿一个叫董宁宁的十六岁小姑娘,张小朵哭的死去活来,十五岁他又爱上了声音甜美的蒋凤凤,无情的踢开董小姐。纵观沈从文的年少时代,一个又一个小姑娘被他伤透了心。
当一个少年陷入爱情里,所要干的事,旁观者往往看不懂,就像施施然费劲心思想要搭讪几个其他书院女弟子,百爪挠心不得其法。这令张道年这个小灶君非常不理解。
“你喜欢一个姑娘,为什么还要跟另一个姑娘牵扯上呢?”张道年躺在木牌牌里边回忆哲学语录壁上的话边问施胖子问题。
“仙长,论及你们仙界的规矩懂的多少,我不如你,但论及人间的礼法,你不如我。”施胖子一脸你根本不懂凡人的情情爱爱的表情。
张道年确实不懂,要懂了,那就动了凡心了,神仙队伍里不允许有谈恋爱的。
张道年从没想过要与一个姑娘拉着手是什么感觉,神格衰弱它也是神格,神格强大的排他性,让他思念不了一个姑娘。
可以这么说,张道年是没有思念的。
这在佛祖看来,很可悲。
当一个人的漫长的人生里,没有一个可以念叨的对象,这得让人多么绝望。
佛祖挂在心里的,现在也只有陈又又这一个姑娘,偶尔把那种心思晾晒在国朝的天空下,总有一种想潸然泪下情绪存在。
思念姑娘的时候,是佛祖最安静的时候,因为他需要集中最大的精神,回想她的一颦一笑,她的跳动的马尾,亦或者她那笔直修长的双腿。
现如今佳人不再,佛祖非常懂施胖子,懂他那种在爱情里患得患失,为了不重蹈覆辙,佛祖觉得为了祭奠自己逝去的青春,也要帮他一把。
胖子就连平时正眼瞧不上的国朝官话,他都练成了,就等一个契机,佛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施胖子当然只得求佛祖帮忙,因为佛祖的颜值还是很耐看的,圈了不少女孩子的芳心,他在众多书院弟子惨不忍睹的容貌里,算的上干净阳光,脸上没有坑坑洼洼的青春痘印痕,说话语调不急不缓,春日明媚的阳光照射下,更显身姿挺拔。
央求了几日,实在拗不过他,佛祖也就答应了同他去见几个姑娘。
因为约女孩子,都是以佛祖的名义约的。
梦华书院女弟子秋梦,秋梦与纪犹行真的很像,这也是施胖子选中她的原因。
“你跟人约好没有。”
“约好了。”
“京都的女孩子,眼界很高,我估计你会吃瘪。”
“又不是真的与她在一起,可以把真实情况告知,然后许她点好处,帮忙演出戏,最终能达到刺激纪犹行的目的就行。”
“人家要不来呢?”
“我报的你的名,我说你要不来,佛祖会很不愉快,佛祖不愉快,佛祖会让你在旧边墙书院过的也不愉快。”
“人家知道我是谁?”
“我也说了,我说你是山长周伯言的私生子,你叫周佛祖,你有这个让她们不愉快的能力。”
“周你爸爸,滚。”
俩人在旧江江岸见了秋梦,秋梦在梦华书院里的地位与纪犹行在旧边墙书院的地位相差无几,都属于众多学子的梦中情人,秋梦一双眼睛无比清澈,仿佛有洞彻人心的力量,看的佛祖一张脸成了红布,那种纯善的目光,能令世间的罪恶掩面遁走。
“秋梦姑娘。”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谁是周佛祖?”
声音也好听,软软糯糯的,让佛祖的身子都麻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姑娘。
佛祖一脸生无可恋,用肩膀一怼胖子,胖子扭头看了佛祖一眼,轻声咳嗽,然后开始饱含深情的用国朝官话朗诵佛祖来的路上现琢磨出来的搭讪用语:“黄昏的江边,景色是那般美,美的不可方物,江里落满黄昏的尸体,林间漂浮着夕阳的味道,漫天星月,点缀了谁的愁,隔岸灯火洞察了谁的殇,天际的归鸿,奔向下一个黄昏,满川风月醉在了滩头,清歌低唱间,轮回运转。”
“请问这位胖叔叔,你想说什么?”
施胖子的世界一片昏暗。
只感觉天旋地转,喉头发甜。
“没什么,只是我大哥看上你了,你考虑一下,跟不跟我大哥在一起处对象。”佛祖看施胖子马上要昏过去,赶紧点明来意。
秋梦姑娘脸都红了,她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同意吗,你看我大哥快不行了。”佛祖望着秋梦,有些咄咄逼人。
秋梦扬起小巴掌,啪,呼佛祖脸上了。
“混蛋。”
声音夹杂在春日的风中远远传来。
佛祖叹口气,有点忧伤。
“是不是太过直白了?”佛祖问胖子又像在问自己,“可老子向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