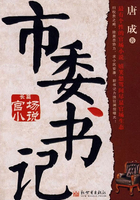我被推进病房的时候,她正在洗胳膊。用了淡蓝色的塑料盆,还有白底碎花的小毛巾。她洗得很认真,压根没把我的动静当回事,她甚至连眼皮都没往我这儿扫一下。她的胳膊浑圆白皙,指尖修长,她把胳膊整个地放入塑料盆里,淡蓝的盆水把她的手臂映得像深海里的鱼,鱼略略地游动着,手指也舒缓地张开,像珊瑚的触须,鱼和珊瑚须腾出海面,她小心地用毛巾慢慢拭干,她垂着眼睑,睫毛又密又长。她只在移动身体的时候显出她的病态来——我爸说满医院里只这科室不能算病号,全是喜气洋洋的大人孩子。但是,她就是有一种住院者的病态来。
一房八张床位,我刚好得到一个空缺。在我床铺顶头的墙壁上,贴着一个号码:42。此后的几天,再没人呼唤我的名字,如监狱一样,我们将被室友和医生护士用数字来召唤我们的身份。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五天后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喜滋滋地返家,如果有些不顺,比如炎症,并发症,产后综合征,我得被留下来作为病人而接受治疗——还有五天猪年就到了。
两个小时后我就觉出自己的运气了。又有两个病人被推进来,安置在病房中间的过道上,床号挂在床尾的栏杆边,没了顺应的数字,写的是加一,加二。一个是才从高危房转过来的,过了观察期,便挪到我们这间普通房。一个是才生下女儿的高龄产妇,比我先进的产房,现在才闹完,哼哼唷唷一路叫唤着。
十个女人的病房,一下子像沸腾的水锅一样闹腾开来。大家很开心地回忆彼此生产的经验,忍着痛地开怀大笑。很快,像久识的朋友一样稔熟。
只有她,我左侧的43号,拖着蹒跚的步子,来来回回地清洁着自己。去水房里打了水回来,抹脸,抹上身,抹下身,抹手指,抹脚趾。做完了清洁自己身子的繁琐工作,然后开始清洁她的周遭,不锈钢勺,搪瓷碗,马克杯,暖瓶,床头柜,甚至床栏。盆都是塑料的,大小不一,顺溜着排在她的床下,全是蓝的,浅蓝,粉蓝,天蓝,湖蓝,然后是搁在盆壁上的小毛巾,也全是白底碎花的,桃红,芽黄,丁香紫,葱心绿——倒没有蓝。
她不跟我们说话。有几个热闹点的女人,才做了母亲,如我一般地多少有了些兴奋,叫唤她:“43,你小心点身子,别干净得像个屎壳郎一样了。”满房的人眼睛便全转向她,笑,悄悄地笑,也有大声地笑。她看一眼我们,又接下去做她的清洁,她总有做不完的清洁,那么小小的一片天地,她总能找到拾掇它的理由,床头柜上的一粒饭,柜子抽屉里一卷摊开的手纸,被角上的一点折痕。有时候我想,她总有一天会把被子也拆了洗了晾在我们房外的阳台上。也只有她,每天换下内衣内裤,在水房里洗净了,在一房产妇的尖叫声中打开阳台,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秘密曝晒在冬日冷寂的阳光下。
不是说产妇是经不得水的吗?不是说产妇是经不得风的吗?我们对她也是很有意见的了。
别的床,来访的人总是络绎不绝的,亲戚,朋友,同学,单位的慰问团,还有丈夫那边更是层出不穷的关系,每张床位到了探访的时间总是热热闹闹的,到了饭点的时间就更虚张声势了。我们这个科室的病人似乎是没有到病区食堂打饭的,全都被娇贵着,粥是红枣糯米熬的,汤是鲫鱼猪蹄炖的,青菜是鲜见的,只有鸡蛋母鸡牛奶,管够着送来。她呢,床前真是冷清,只一个父亲一样的男人,半谢了顶,佝偻着背,每晚忙嗖嗖地过来。也不多说话,她也从不让让他,揭了保温瓶就往嘴里送下几口饭菜去,然后推了保温瓶,半卧在床榻上,拿过父亲递上来的水,喝几口,再放下。有时候会听到这时她才想起般地问他:“吃过了?”男人便淡淡地点头。此刻她倒是安静了,也不忙着收拾清洁了,一直便半倚在床栏上,眼睛直勾勾地发着呆。男人总低了头,坐在她脚边的一张椅子上,总有报纸在那里等着他看,旁边过来过去的人会小声地说:“哎,稍让一让,我过去。”男人便起了身,有点手足无措地瞪着别人过去,或者,“哎,稍起来一下,我拿个东西。”男人便盯着别人拿东西,像严肃的监工一样,从人家的手指直盯盯地看,好像人家不拿什么,他便不依不饶了样。那种神情是生涩的,却也是认真的,无法理喻的较真。
这种病房里,除了偶尔探访的客人中有男人外,倒是叫人尴尬的地方,年轻的老公倒不在例,因为他们的虎虎生气,带来了生命的那种豪情,让人觉得闲适和彼此在战场上共过生死的交情。而老男人,总让人觉得龌龊和不合时宜,与生命的欣欣向荣是截然反之的,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古怪和狎昵。我父亲也就来过一趟,很识时务地走了,他说:“婆婆妈妈的。”很知趣地不入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兴奋,谈的多是平常连和女朋友都不会触及的私密话题,在这间病房里,理所当然地成了科学的探究。而他,那弯曲的背,那肉松皮弛的脸,那灰搭搭的羽绒服,怎么也觉得怪异和脏相。他一来,我们全噤了声,有点隔膜地看着他,就像一握嫩绿的韭菜里放进一棵蔫白菜帮,或者一群白免里混进一只毛色杂陈的癞皮狗,我们是排外的,把那些猥琐萧瑟的老男人冷酷地撇在我们的门槛外。这个男人的固定造访得罪了我们的生机,我们此时也恹恹的,不再彼此谈笑,或者开点身体的玩笑,往常的嬉笑变成了这一小时里的不耐。
总是让人好奇的,有人耐不住,问她:“43,那每天来的男人,是你爸?”
她不吭气,她在清洁自己。
又有人接着问:“43,你老公呢?你老妈呢?”这本最该来探访的两个人,何去何终了呢?
有人便叹了气:“就晚晌才送一顿饭来,你中午怎么解决的?”
她这时终于抬起头来,放下毛巾:“我吃过的,也不饿。”她的口音带着乡村的调,我们突然有点同情她来,到底是比我们低一截的人,原来对她过于讲究卫生的那种发酸的鄙薄,突然膨胀成了对个一心想成为我们中一员的农村女人的怜爱。“你生的什么啊?”大家都瞪着她看,每天五次的喂奶哺乳时段里,从没见她去过育儿室。
“儿子。”她小声地说。
后来知道她是难产,很受了点罪,坐胎,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的。孩子先是放在氧气罩里,两三天都没开奶,她自己也是滴奶不流,医生着了急,每天让看护用奶瓶子喂,好像也能吃了,但仍在特护室里。
我们小小地叹口气。
她仍旧每天仔细地清洁她的身体,她的周遭。还是不爱跟我们搭话。逢到什么她都说不上嘴,老妈呢?老公呢?孩子怎么回事呢?这些都是有点凄凉的话题,还有,那每天只给她送一餐晚饭的老爸呢?家里的其他亲戚呢?
我妈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她。我妈如我们一样,喜欢弱弱的人。我妈喜欢漂亮干净的人,也如我们一样。她其实长得相当好看,真的,水色在产妇苍凉的面皮下,仍能看出那种爽利,但是,她的漂亮,怎么说呢?漂亮的人,如果是高贵的,让人有一种不敢侵犯的招摇,如果是甜丝丝的,让人有一种亲近她的渴望。而她的漂亮,有点让人觉得俗丽的,觉得下里巴人的,觉得本应让人忽视的。偏又加上她无来由的洁癖,本该不是她这种人所应有的洁癖,似一个村妇得了忧郁症的,似一幢摩天大厦里晾出一床破棉絮的,让人有点反胃的难受。而且,不光她爱干净,有那么点漂亮,她竟然还带着点傲气,不明所以的傲气。这真是让人怎么也想不通的,这真是让人怎么也喜欢不上来的。
我妈背着她大声地对我说:“你别臭讲究,不要胡洗瞎洗的。伤口得用高锰酸钾洗,护士不每天来帮你们的?不要用水,不要用毛巾擦伤口。出了月子,身子养好了,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我妈说:“嗨,一个农村女孩,瞎干净什么,一点科学都不懂。”
管我们病房的那个男医生,据说是个硕士,个子小小的,不知因为学这科是不是自己也觉得有点怪,对着我们的目光,倒充满了与他个头儿不符的凛然。每天他有例行的查房,到了有些床位,刚做了母亲的女人,还脱不掉女儿般的羞惭,摇着脑袋,说:“还好,我没事。”他也不坚持,拿了查房册,记一笔,走开。真有事的母亲会自觉找他的,当了一房的女人,褪了裤子,分开双腿很配合医学地让他看诊。他的眼神扫得很快,像是这一行很怕人家诋毁他一样,他很快地说了方子,让跟班的护士配药,极少说让人脸红的这一行的术语。43,也从不让他看,也只说:“还好,我没事。”他停一下,总弯身看看她的病号牌,每次都那样,像第一次见诊的病人般,他拿着笔在他的查房册上记着什么,淡淡地说:“你孩子,现在正在发黄疸。”她有点急:“要紧么?”他仍旧头低着:“也还好吧?反正你着急也没什么用。”他走了,她的眼睛钉在他远去的背脊上,恍恍惚惚的。
“43,”同房的有人叫她,“那你还不去看下你儿子?”
她把脑袋移回来:“医生也说了,我去没什么用。”
我们都把眼神换一下,想不出她怎么是这样的个性。
后来,又来了个女医生,也是年轻的,还架着副眼镜,听说也是硕士毕业的,一心准备再考博。她抱着手臂和男硕士查了我们的房,很轻描淡写地说:“没意思透了,都是些顺产的,手术也只是坐胎和双生剖腹的,没一点课题。”她踩着高跟鞋哚哚哚地出去了。
房里静了一会儿,有人终于骂起来:“他妈的,是不是人啊?讲出这种话来?把我们当什么了?!”
有人应起来:“真好笑,刚才怎么不见你发火。刚才你要发了火,我和你一起剁了她!”
我们开始恨恨地声讨那个女医生来,妈的,她生过孩子吗?
43号挪着身子走出去了,她唤:“医生,给我查查好吗?”
我们都看着她,过了一会儿,那双高跟鞋在走道里响起来了,女医生冷着脸,问她:“你怎么了?”
她有点嗫噜,退到床上:“你要不要看一下?”
女医生等着她脱了裤子,只扫了一眼,就有点惊:“怎么弄成这样?”女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不那么让人讨厌了,敬业的人总是让人没法不尊敬的。女医生把头探过去:“都有味了。怎么烂成这样?”女医生叫起来:“你等等,我把你的医生找过来。”她说的是男硕士。43这时涨红了脸,把裤子提起来,叫:“不,不让他看。”女医生回了头,漠然地看她一眼,女医生又让她把裤子解下来,女医生对她的病要比对她本人感兴趣得多,女医生凑在她的身下看着,眼睛明显地带着腾腾的焰火。护士过来了,听女医生的吩咐记了病状和主诉。43问:“要紧吗?”医生点点头:“得做手术。这块烂的地方,时间太长了,必须切除!”43惊道:“我,你要切掉我的下面?”女医生点着头,饶有兴味地看着她的身下。我们都凑过头,43早把被子做了帐篷,只留给医生唯一一点可窥的空间,女医生也横眉冷对鄙夷地斜睨着我们,把自己的身子做了那帐篷的门帘,我们全都意兴阑珊地撤下。
她很快做了手术,没法遮掩的,那总来的男人曝出了身份,不是父亲,是实实在在她的老公。倒不是很惊讶,只觉得有些奇,年龄隔了三十多,广东人,也不像个有钱的,不知她贪图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就说了43床的事,好像是广东人哄了她,她便跟了他。她父母是本省乡下的,虽不富,但也不算穷得揭不了锅,而且祖祖辈辈守在那块乡里,女儿出了这桩事,便觉有失脸面,从此翻脸不认这个女儿,生死由她,结婚也不管,生了孩子更不理,再不相往来。我总觉得这是大家的猜测,和许多这样的故事差不太离,杜撰一点也错不了根的。毕竟43是从不多言的人,她怎会对着陌生人去讲她的故事?后来她很快回来,到底是小手术,算不上女医生的课题。她走路时的样子更蹒跚了。
那天夜里,她突然大叫起来:“妈妈!妈妈!”声音浑浊而苍老,如垂暮之年的老者的低嚎,恐怖,惊心,冰凉,刺骨,像远际的星空,像不可测的海底,墨蓝的一种冷寂和绝望。我们扯着了日光灯,全叫唤她:“43,43,你怎么了?”她浑浑噩噩地应着,仍旧翻身睡去。病房里稍大点的那个高龄产妇对我们说:“才做了手术,可能麻药劲过了,痛的!”但一房的人都被那声音吓住了,再不肯闭上灯去。
我妈开始同情她,主动搭讪她,我妈说:“你不要老是洗老是洗的,毛巾,水,都不是药,你这样做只会刺激伤口的。”她瞪着眼睛看看我妈,拿了毛巾的手,悬在半空里。我妈转回身子对我:“可怜见的。”我妈到底是老人,比我们见多识广,一眼就猜出那男人与她的关系,我妈不说破,我妈只瞧不上她,我妈想,这样的女人,既不是小姐的身子,也不是小姐的命,做许多招眼的讲究干什么呢?但我妈还是怜惜她了,为她在夜里鬼哭狼嚎地呼着她的妈。她的妈怎么样她了呢?没人说得清。刚做了母亲的一帮我们,在育儿室里,对着老护士粗手大脚推过来的一车七个婴孩,小心地抱起自己的宝贝,羞羞地唤着“妈妈,妈妈”,宝贝细软的身体,不敢轻易碰触的薄如蝉翼的肌肤,我们将来会舍得为着什么抛下他(她),来成就一番道德吗?
加一走了。收拾衣物的时候以为她会流泪,但没有。我觉得有些难受,换了我,也许会大哭一场,可我妈说:“她的决定是对的。有什么呢?总比将来养个不好的孩子强。”我妈还说:“这么小,也没什么感情的,不妨事。”加一走的时候很隆重,从头到脚全是红的,包得像个粽子一般得严实,她的那个传说中的婆婆亲自过来接的她,她婆婆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怎么也不能在月子里落下毛病。”年青的老公也笑嘻嘻的,一点没有刚失去孩子的那种我们想象中的悲恸。接她的车停在楼下,她被那些红裹得喜气洋洋,像一团焰火钻进那辆豪华车里,还冲我们招着手,脸面是没心没肺的笑意。
加一的儿子在氧气箱里待了三天,仍旧没有开奶。她婆婆很坚决地说:“我们不能要了。现在讲究的是优生优育,养活了,大脑也成问题。”签了字,医生把氧气箱的电源拔掉,她和她婆婆看着那条幼小的才来到世上三天的生命,渐渐地发青发紫,僵直了胳膊和腿脚,不再动弹。
我们听着加一的描述,有点瑟瑟地发着抖,到底还是理智的,想着看过的那些弱智儿童,肌肉萎缩的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的少年,也盛赞她的决定。43没有吭气,她淡淡地听着,好多人已经忘掉她的孩子也还待在特护病房里,茍延残喘地等着看护喂食。
我顺利地在年三十的上午出了院,和我的宝贝能在自己家里过这个年——婆婆已经为他打扫了房间,准备了银锁,一纸箱的衣服,包被都做了十二床,由着他尿了。我笑嘻嘻地在老妈和丈夫的陪同下领回了我的儿子,护士褪开医院的包被,露出他不安分乱踢乱蹬的身体。护士说:“看哦,手是好的,脚和腿也是好的,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哦,唷,脐带正好掉了,省你们事了。看哦,我们是完完整整交给你们的啊。签个字吧。”我签了字。
路过看护室的时候我见到了43,不是哺育孩子的时段,她踮着脚,朝着那些玻璃窗里望着。特护室里充满了令人生畏的仪器,与生命不相符的仪器,这些冰冷的仪器,给这些刚降临人世的小宝贝,做着维持生命的努力。男硕士拿了查房册出来,看见43,愣了愣,转头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