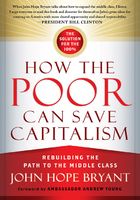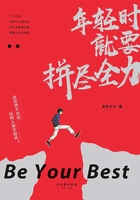1
你在写书,所以你来问我,你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对吧?你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现在你回来了,你来打听我这个老家伙当红军的事情,那我就跟你讲。我当红军那时候的这个广城畈,跟现在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要大惊小怪的。我讲这个没有什么不一样,虽然都这么多年了,但广城畈就这么个场子,没有什么变化,下边那个丰乐河也就是那个样子,南边的天龙庵、金鸡寨也没变,往西霍山,往北六安城,往南往东棠树新街都没有变化。你想一想,自古以来,这个场子就这个样子。有人讲大炮来轰过,不过我跟你讲,大炮算个屁,大炮在广城畈轰一下,最多掀几块土,能有什么变化?我跟你讲,你要写那时候,那时候跟现在没有什么两样,田也还是那个田,菜园也是那样的,那时有个沟坎,现在也都还有,你不要指望讲你写那时候,你就写今个跟那时候有很大不一样,你要这样写,那我不同意。
2
我种田,种的就是这个本家的老刘大地主的地,其实也没有什么多想。种地本身就很辛苦了,这个倒是光就种田那个劳累来讲,我说过确实有苦的地方,但这么苦你还要想着去跟地主计较,这在当时不大可能。我跟你讲这个,是说我跟地主没有那么大仇,有的人家可能跟地主仇很大,但我不是。那时我已经成家了,家里有了好几个小孩,并且我媳妇那时候还要继续生小孩。可以讲,事情都很明白的,就是说日子得过下去,而且也确实没到你日子过不下去的场子。我就讲这个,跟你说,就是这么回事。但我没有想到,这时候,离我当红军已经很近了,我不像别人容易招人注意,我对广城畈、河嘴庄、丰乐河、界河、我对这一块地方,从下地起就清清楚楚,哪家哪户什么情况也都明白得很。
我是想不到自己要去当红军的,并且那时候即使有过一个姓李家的李老六来跟我讲过话,我起先也没有注意。李老六的父亲是个大地主,这人不光是大地主,而且在省城上有熟人,在县城里有家业。叫李朗斋的这个大地主,我没有见过,但我们广城畈那块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是在西边太平街那块的大地主,在我们畈上的西头靠青龙嘴那一块有地。不过这个李老六,跟我本来也不认得,大概是他跟我们河嘴庄边的秧塘庄上的史家的一个丫头是同学,她们都在县城念书,所以这个李老六就到畈上来。这个史家我倒是很熟,因为我到他家那边做过活,他们待人很不错,那个读书的叫老八的丫头是个很爱笑的人。于是,这个李老六有一天就跟老八到我干活的田边来,她俩来跟我讲话。她们那个年龄,也就十几岁,我不晓得她们读书有什么用,但她们找我讲话,我又不好回绝,毕竟史家的八丫头多少也还是后庄上的一个叫得响的丫头。我就听她们讲,但起初她们什么也没讲,后来那个李老六单独到我家门口坐着,先跟我媳妇讲她要到我家来喝茶。我媳妇讲家里只有粗茶。
这个李老六当然不是喝茶,后来我媳妇就听出来了,李老六是要问我做衣裳的事情。不过我不是那种专业的裁缝,我只是一个在年底会为穷人家做点衣裳的人。对啦,就是穷人家,像自己差不多的人家,至于地主家,我是从不会为他们做衣服的,而且也只有为地主家做衣服的,也才算是裁缝。我这个人不叫裁缝,虽然我会做衣服,但平时,我自己都不当自己是个裁缝。对了,你听好了,我讲我是裁缝,是为了跟你讲明白,李老六为什么要来找我,要不是为了讲清楚这个事,我都不想讲我做衣裳的事情,当然如果说只有为地主家做衣裳的人才叫裁缝,像我这样给穷人家做衣服的人就不叫裁缝的话,即使现在我也是不同意的,所以我还是称自己是一个裁缝的好。但首先我是个种田的,李老六来找我,不是因为我种田,这个你听到了,对吧,她一个在县城上学的丫头怎么会要找我讲什么种田呢,对,她是讲裁缝的事情。
3
她家是大地主,她自己在城里念书,从她那个样子,我看出来她根本不会叫我做衣裳,再说地主家的衣裳我根本做不来,而且她穿的比农村地主穿的要好,她父亲是李朗斋,那么大的地主,她有哥哥在省城,她怎么会要我这种裁缝做衣裳呢。我不想多讲,她就又问我做衣裳是不是有模子啊。我讲我是有模子,这个倒是肯定有的,模子就是那些样子,有些是纸糊的,有些是木牌子,也有竹架子,反正农村人衣裳就那些样子,我能当裁缝,就是我手巧。我小时候,我阿老——对,阿老,就是我父亲的意思,你是广城畈人你应该听得懂——我阿老就叫我跟月店庄的一个人学,我那时候不想学,但我阿老打我,讲你种田是本事,做衣裳也是本事。你不晓得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不一样,做衣裳反正也不是什么很高的事情,基本上比种田恐怕还要差一些。可以讲就是不怎么正经。我阿老跟别人不一样,他虽然跟我一样,是种别人家田的,但他自己读过不少书,他自己以前跟我讲他对皇上都有认识,他都知道。皇上虽然也认为天下人种田重要,但他讲,很早很早以前,古人都讲过农村人要会很多手艺。对了,我阿老就讲皇上就是站到你面前,他也不会讲去学做衣裳是件什么丑事。
所以我就到月店庄去过几次。后来我就学会了做衣裳,主要就是会剪子,你要把袖筒、褂角都能剪出来就行。所以我讲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本事,就是学东西时候,凡是自己心里有点谱的,上手就快,我犁田也是这样——做农活我就不说了,我还是说做衣裳。这个李老六跟我讲模子,我媳妇在外边听得就刺耳了,说一个城里读书的大地主丫头跑来跟干农活的土裁缝讲什么模子?后来这个李老六就讲开了,她问我,为什么对种田就没有怨言。今天,我跟你讲真话,她那时跟我讲这个,我差点没有翻脸,但她这个人做工作有点水平呢,她讲那话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能做衣裳,那你为什么还要种田犁田耕地,你就当个裁缝不好吗?我是这么理解她的话的,所以我心里也就在想她这个人要是自己不做衣裳,却来找我,有什么道理?我就说我要出去把牛拉到大堰那边去。牛是大地主家的,我去放牛也不是必须的,但我不想再跟她绕了。
这时那个史家的老八也来了,她跟李老六两个人在我家大门口的稻场上笑。我不晓得她们搞什么鬼,原来八丫头是从她家什么地方找了个模子,是做女人夹袄的,这个模子我没有见过,因为穷人家很少做这种夹袄,她俩在那比划,我就有些糊涂了。我到牲口棚牵牛时,刘大地主的三少爷就在那儿抽烟,他见我过来,就问我现在来搞牛干什么,还不如跟他到河边上去看水。那时在发水,我跟这个三少爷没有什么话头,我又有些生八丫头和李老六的气,所以我就冲这个三爷,我讲三爷你到河边干什么,河边水大,你又胖,当心你掉水里去。这个三爷听我讲话这么冲,他也就不跟我讲了,他远远看到在我家稻场那儿的两个女丫头。我去大堰放牛,原来那个八丫头跟李老六在我家稻场那边又站了很久,我媳妇好像跟她们在那讲话,我看她们应该差不多走了,我才往回。
我在拴过牲口后,从西边的田头过那排阴森的榆树林时,看到一把油纸伞在树下边晃荡,下边人在招手,雨有点大,我起先没有认出来,后来我看见了,还是那个李老六。这下子我就很生气了,我心想这个读书丫头,喝了墨水,怎么比我媳妇还要笨,讲个事情怎么就没个完呢。我就躲到榆树下,树大,叶子密,雨落的不多,她举着伞,天色有点暗,主要是从这个地方能看到河水,可以讲河水不小,水是才发上来的。她见我躲到树下,她就有点激动了。她讲,你会做衣裳,那你就会做旗子。我讲什么叫旗子。我是不明白她讲什么旗子。她讲就是旗子。我讲,人家死人时,我做过旗子,是那种跟被面被单差不多,可以举起来,拴在竹竿上的旗子,但你讲的旗子是干什么的?她讲,我讲的旗子,我讲出来你不要害怕。我讲,你现在倒真跟我讲正事了,我看你这样子好,不像之前在我家那里讲东讲西的。她又讲,要你做一面旗子,在埠塔寺那块有人要用。我听得有点糊涂,没头没脑的,什么埠塔寺有人要用,那为什么要我来做?我又不晓得那个场子要旗子干什么。
4
我媳妇认为问题很严重,一个城里的念书人到农村来讲种田的怨恨,这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我媳妇马上就转过脑子。她问,那为什么她单单要跟你讲呢,跟你刘行远讲这个有什么意思,你是她什么人?你又不是种她家的田,你老刘家自己就有大地主,虽然没有李朗斋大,但在广城畈也是首屈一指的,她个李朗斋的千金怎么要对你讲这个?我讲你就不要问这么多,我怎么晓得。我媳妇后边还是问到做衣裳的事情,她讲那还是做衣裳,对吧。对,做衣裳。还讲史家八丫头那边有模子。我媳妇本来不想讲做衣裳,因为讲这个就会讲到李老六会找我做衣裳,她自己一方面是不相信,另外她也认为这很不正常,一个大姑娘,在城里念书,找一个土裁缝,或者讲一个为穷人做衣裳的人,做什么衣裳?她倒不会想李老六对我有什么想法,她只是不想自己把自己给绕到这个糊涂的问题里去。我见我媳妇跟我讲这么多,我是不想让她以为我有什么要瞒她的,所以我就讲,她同学里有家里穷的,就是穷学生。为什么有穷学生?因为她在县城念书的同学里,基本上都是地主家的小孩,但问题是有些地主也有折本的,或者当了田地的,基本上是小地主,所以有落魄了的,所以她就要为她同学,怎么讲呢,做几件衣裳。你看,这不是穷人家的衣裳吗?
我媳妇听我这话以为不错,再讲她看史家八丫头也一起来家里,心想都是同学,反正有个照应,再讲别人找来做衣裳总不是件坏事。我好不容易把我媳妇给对付过去了,但天黑以后,我又到大墩那块去,当然早就没有李老六的影子了。
李老六在第六天的时候又来找我,没错,你可能想得到吧,见面的地点就在大墩上了。时间是早上,天刚亮,她前夜是在史家住的,这样她来找我,在大墩上见,就不显得特别,而且前一天史家八丫头到我牛后边跟我讲了,讲第二天天一亮就到大墩去,李老六在那等我。我知道史家八丫头是个很懂事的姑娘,我是看着她长大的,我信她。于是我就跟李老六在那大墩上见面,那时河水已经发到最高处了,基本上淹到大墩的底座,河水涨这么高,你就看不出它有多凶,反而很平。我照例是牵着牛来的,牛在大墩下边,靠田拐那块菜地边吃草。我上到大墩上,东边还没发白,是青色的,我看见李老六从秧塘庄那边走过来,她是空手的,她远远就看见我。她向我挥手,我们农村人没有这一套,这完全是县城的做法。我没有向她挥手,我反正是看见她上大墩来了。
她站到我边上,她讲,刘行远,你比我来得早,你真行。我想她这姑娘真不简单。她望着河水又问我,你看这水好大,你看河水这么大你有没有想到人应该总要干点事情。我想她这是要跟我说事情了,不过我不认为做事情跟河水有什么关系。李老六讲,我老早就认识你了,我好小时候,到你们广城畈来玩,就看到过你。我讲你那时才多大。她说,也没多大,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吧。我心想我总比她大个七八岁吧。但是,她李老六是地主家的人,她是李朗斋家的,她要是我们老刘家的,也就不分什么地主不地主了。她又讲,我那时看你,就看到你有头脑。我摇了摇头,我想她这么讲话一点没有意思。我就问她,你还是来跟我讲做旗子的事情吧?她点了点头。我讲,那行,就讲做旗子,不要讲什么种田,不要讲别的什么。她却摇了摇头,她讲,你不是榆木脑袋,你很清楚,不然你不会瞟学都能学成个裁缝。我马上反对她,我讲我不是裁缝,我只是个给穷人家做衣裳的。她讲,你头脑要改一改,我跟你讲,你就是裁缝,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想她这么讲就是为了我给她做旗子。当然,不是给她做,而是给埠塔寺做。我说,你不要讲我有本事,你叫我做旗子,那我就做,我想好了,你从太平街跑下来,叫我做旗子,我总不能讲我不做吧。她讲,你做旗子,不是为我。我讲,你讲过了,是为埠塔寺那边的人做。她讲,你不要榆木脑袋,对不住,我又要讲你了,我不讲你不行,都讲做旗子了,所以我跟你讲种田,为别人种田是不对的,你要有个认识,你不是糊涂人。我说,你讲做旗子跟为别人种田有什么关系。她讲,不是什么关系,而是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分开看,就讲种田,为别人种田交租子,你想想,凭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说,李老六你不能跟我讲这个,你不是我们刘家大地主的小孩,我不跟你讲这个,还是讲做旗子。她往河边走了一点点,下边就是水,水面很平静,水很浑黄,我晓得水里边的劲道很大。我喊了她一声,我讲,老六,你回来,站过来,你就讲做旗子。
她看着我,我看见她眼睛很亮,她不是畈上人,但太平街跟广城畈也就几座山头,几个山冲相隔,可以讲我们都是一个场子的人。她这个丫头,你这么近,看,就能看到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她不像一般人,这我早就看出来了,她很慢很慢地在我前边晃着。我讲,干什么用?她讲,埠塔寺那边有人要用,他们是为你们做的。我头皮有点发麻,我问她,他们干什么用?怎么讲为我们干事情,干什么事情?她说,他们要的是这样的旗子,你听好了,他们是做大事情的人,他们为你们做事,为穷人做事情。她讲我是穷人,这个我承认,我是个种田的穷人,也许祖上多少代是过富人家,但现在是穷人。那他们到底干什么?我问。她讲,他们就是为你们穷人做事,为你们穷人,他们什么都能做。我听她讲话,知道她是认真的。她扭过脸,现在天色亮一些了,她又说,我小时候看见你在大路上走,我就看见在广城畈这一块,不光你们河嘴庄,就是整个畈上,也就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把旗子做好的时候,丰乐河的大水已经退去,天空显出那种要干裂的样子。我跟你讲我们广城畈这一块就是这样,天色跟人脸色不一样,没有什么大规矩,总是这个样子,先是大水,很可能后边就会大旱,而且那时候天气要是干,你就没有办法。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我做好了旗子,我到大堰那块去了一趟,我是路过地主刘天阁家,他算是我的远房叔父吧,我没有看见他。我要看见他,他总要跟我打招呼,他在庄上的时候,他总是转转,碰到什么人,也会拉拉家常。我对刘天阁一般都不多话,因为他晓得我小时候在他家私塾那里偷偷瞅过字,他以前还考过我,问我能不能做门对,就是对联,我有时斗胆跟他讲副对子,他就会很认真。总之,他要讲对子我自然讲不过他,但他不是讲你讲不过他,他就放过你,他会讲你讲的对子有点意思,他还要请先生来,硬是让你在塘埂上站着跟先生一起把那对子继续讲下去。有一次,我讲福来千亩丰,还有一句什么我记不太清。他先是夸我,晓得农事农活要靠天,下边一句他就讲不好,特别不适合贴到门上去,具体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到大堰去,没有看到刘天阁,但怎么会想到刘天阁呢,特别是在做好旗子的时候,我想可能是跟叫我做旗子的李老六讲到的种田怨人的事情有关系,不过我自己还没有把这个前后头绪理出来。我是准备晚上往埠塔寺送,为什么要晚上送,这个倒是李老六这个丫头跟我交代好的。她讲你往埠塔寺送旗子,你只能晚上送,她讲你晚上送才安全,她也交代过我,做旗子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所以我做旗子我媳妇也不知道,我是瞒着她,在晚上做的,我零零碎碎做了好几天,又没有模子,我自己要摸着做,白天还要把那旗子埋到屋后小房子的土里去,那是个堆杂物的地方,晚上取出来。我媳妇只有在后半夜才会睡得死,等到快天亮时,她又会醒得早,加上我那几个小孩都挤在一块儿,所以每天能做旗子也就夜里那一两个钟头,好在我还是把旗子做好了。
我想如果晚饭后马上就走,可能好些,就跟人讲自己是到霍山去,因为霍山那块有一个远房亲戚,不过为何早也不说,突然在这个大旱天要到霍山去,别人会不会讲什么话,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过我跟我媳妇不能讲我到霍山去,因为我媳妇多少也还是有些头脑的,她不会相信我到霍山去。我就跟我媳妇讲,我讲我要到东边去。她问我到东边去干什么?我就讲我到东边去,往新街那块去进布料,九十铺也要路过,那边有麻。我媳妇晓得我到那块去是干正事,她才会答应。但我又交代我媳妇,要是有人问我到哪去,你就讲我到霍山去。
后来我想我之所以跟别人和我媳妇讲我去了不同地方,并且要我媳妇跟别人也讲我是去霍山,那可能是因为我总觉得即使是对媳妇,你还是要讲一点点真话,我是想到我讲到东边去,我媳妇会知道九十铺、新街那一块跟埠塔寺大致是同一个方向,无非是稍稍区别一些而已。至于我为什么要晚上出发,我没有办法跟我媳妇交代了,我怎么也讲不清楚。
吃晚饭的时候,我那三个孩子就站在桌子前,我有些不想去了,我看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没有人问我一句话,我媳妇还像以往一样,跟他们讲吃饭要快,不要拖拖拉拉,吃的是熟菜,其实也就是顿顿吃的那种,小孩们虽然嘴上不讲话,但他们晓得如果他们嘀咕几句,我可能就要骂他们,说不定还要打他们。我那个岁数时就是那个样子了,每逢我心里有事,或者讲我真有些怨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我一打他们,他们就不做声,我知道他们就会退到房拐子那里去,这样我就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当然,那天我没有打他们,我想如果我打他们,我在夜里走路,我心里就会慌,我就会想我这几个小孩跟着我不容易,就像李老六讲的,我在农村跟别人不怎么一样,我偷瞟过几年书,所以人家把你看得跟别人不一样。晚饭吃完了,我跟我媳妇讲,我先前在大堰那块看鱼在跳。我媳妇问我,有几条鱼在跳。我讲,总有十来条吧。我媳妇就到厨房去捣鼓,过一会儿,她过来跟我讲,她讲没有事,我看过了,十条鱼不要紧,要是几十条就不好了。我始终也不晓得为什么十条鱼就没有事,而几十条就会有事。我媳妇把我几个小孩都喊到里屋去了。这时我跟我媳妇在大门口那块又讲了几句话,我讲我最怕到霍山去了。我媳妇晓得我这是讲给风听的,她是个老实人,她没有办法接话,她就讲走夜路你不要乱讲话,小心野物。我就跟我媳妇讲你瞎讲什么东西。我媳妇就回里屋去了。
我这时候往后边小房去,我取了东西,没再跟家里人打招呼,我也没有到前边那进房子去——我父亲住在那一头,我想我最好不跟他讲一个字。于是我马上就加快步子,没有从大堰走,而是绕到庄子后头,向秧塘庄沿子走,我知道只要过那个庄沿子,天就会黑定,那时候,我才能从秧塘的北沿绕回到三月潭,从三月潭下那个河湾,然后从河湾上扬水圩,我才能踏上去埠塔寺的路。
5
就从这河嘴到杨水圩,进墩子湾,再到半个店,然后一直向东向北插,绕许多山头的山路,我跟你讲,我是都在想我怎么一下子就有了穷人那种心情了,这是照今天的话来讲的,你要写书,你问我这些事,我都原原本本讲给你听。你看,你上午要我在我家门口指给你看去埠塔寺的路,你从这畈上,往东北方向看,被王家榜后边的第一个山头就挡住了视线,所以你是看不到的,你自己是广城畈人,但你恐怕也没走过这种山路,因为除非特殊,从这个场子到那埠塔寺的这山路是没有人走的,人家是不走这个路的,就是向东沿大路走,走到曹丕塘才有另外的路通向埠塔寺。
所以从王家榜那后山走,从一开始我就是要走这个没有人走过的路,虽然李老六,这个六丫头没跟我交代要走哪条路,她自己可能不认得从这个场子到埠塔寺要走的别人不认得的路,但她跟我讲,叫我晚上送去,那我就晓得我要自己找路走。上午,我指给你看那个方向时,你嘴巴冒着一些话,我晓得你可能多少有些吃惊,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在路上就有了穷人的心情,并且我想我孩子,我媳妇,我是担心她在家里头说不来话,虽讲她会跟别人讲我去了霍山,但她又是晓得我去的不是霍山,而是往东边进布料去,到九十铺,到新街,这路她晓得,但要是我走这山路,让她晓得,她就不会同意我去,想必她会想到即使不出别的事,光是豺狼就可能把人吃了。对了,我在那晚是听到狼叫的,我晓得狼都不是一个两个的,一般都有六七个以上,我在畈上都遇到过,但在这山路上,我带着旗子,我没有点火把,我就是晓得,我什么也不能让人看见,我就是指望反正在天亮之前我得赶到埠塔寺,因为我心里慌,我又很凉,虽然夏天,你晓得光是天上的星星就能照见这长着松树的山路。
我在想着心疼我小孩的时候,我就不怕狼了,我怀里有一把刀,我就想要是狼来咬我,我要么杀掉狼,那么我自己割自己一刀,我不能让狼一口一口咬我。我记得我阿老以前跟我讲过,说走山路时,你无论如何不要回头,不是讲有人喊你不要回头,而是你始终都不能回头,因为你头皮发麻时,有时你不晓得你后边有什么,而往往,你肩膀上很可能趴着一只狼,所以你一回头,它就把你脖子咬断了。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要你不回头,只要脖子不被狼咬断,你就还有气,还有气,你就能往埠塔寺赶。我在路上也没有给自己鼓励,但我想我小孩们都在家里,如果不是要送旗子,我至少能跟我小孩们在一块儿,即使我打他们,他们以后长大了都会晓得。但是,我现在却要往埠塔寺送旗子,我就想我是送旗子,才有了这个山路,以及我还有不能被人看见的危险。但是,是李老六让我送旗子的,我想这本来是件好事,她叫我送旗子,怎么不叫别人送呢,她也讲了,她讲在广城畈只有你看起来还像是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就是信她这个话的,加上在今个晚上,我在送旗子啊,我知道我是穷人啊,别的不讲,如果我不是穷人,恐怕我也不会送旗子,一是李老六不会叫我送,二来我不是穷人,那我也不会给穷人送。我把这个道理想通了,那些为穷人办事情的等我旗子的人,他们也是穷人,如果不是穷人,干吗要偷偷摸摸的呢,地主做事就不会偷偷摸摸的,他们做事都是正大光明的,他们都摆在明处,哪会在晚上还要送旗子呢,这所有事情都是我们穷人的。
6
我现在跟你讲吧,我天亮前是到了埠塔寺,李老六,六丫头跟我讲的是让我到油场去,油场在埠塔寺的东头,那场子也有点凹,我不晓得到油场去要讲什么话,她也没讲油场是个什么情况。她就讲反正你天亮之前到油场去,从山底下那个门进去,油场是在一道山坡上,坡上有栗树。油场我以前也没去过,但我晓得有个油场。李老六跟我讲你到那,有个人会等你。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我从底门那儿摸进油场,是个大院子,里边还有一道小门,我推门进去,发现里边很香,是堆油饼的,油饼码得都是成垛的了。我进屋后,因为很黑,只能从窗子那儿照进来一点点夜里的亮光,因为天始终没有真正黑净,所以在埠塔寺我感到比在山路上又要亮一些。
我看见从成垛的油饼堆里站出来一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这个人手里拿着麻绳,腰上也系着麻绳,我不明白他拿麻绳干什么。他见我愣在那里,就跟我打招呼,他讲你是从广城畈来的吧?我讲我是从广城畈来的。他讲你终于到了。我不晓得他这样讲干什么。他也没叫我坐到凳子上去,他就讲你路上走得还不慢。当然我也没讲我是走了一夜走到埠塔寺的。这个人腰上的麻绳跟他手上的麻绳不是连在一块的,腰上系的麻绳要粗一些,手上的要细一些,但也都不长,他靠在油饼堆上,我以为他会跟我讲旗子的事情,但他没有说,之后他就讲那你就在这等着。我不晓得等在这油场的油饼房里是干什么。但他叫我等,我就只好等。这时候,我发现穷人就是这样,你现在清楚了吧,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讲你自己,你什么也说不出,再说你还不晓得对方是什么人,但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李老六跟我安排的,是她看得上我,也看准了我,知道我这个穷人可以为另一些穷人干点事情。不过眼前这个人,我又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相像,也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甚至我都难以相信他也会是个穷人,尽管他看着也一定是一个穷人而已,否则他也不会夜里在油场等我。但他那样子,一脸的没有熟识相,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讲,他手上的麻绳也不怎么动,但他偶尔会看着那个通向外面的窗户。我闻到油饼的香味,我感觉这香味如果时间久了,会把自己熏得头昏眼花,所以我想长久地呆在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好办法。
这时我有一点难受,因为既然是叫我送旗子来,那见我的这个人却不跟我说旗子,让我呆在这个油坊里这算怎么回事呢。这个人跟我在一块儿站了大概有半个钟头,我是把他样貌给记下来了,我看他不那么像家门口人,至少我不认为他会是广城畈人。当然这是在埠塔寺,跟广城畈自然是不一样。他问我晚上吃的怎么样。我就讲我晚上吃了东西。他问我扛到晚上行不行,我就知道他是不想让我以为在即将开始的这个白天我会有饭吃。其实,穷人就是这个样子,穷人容易被人关心到是不是有饭吃了,或者说后边还有没有饭,但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我到埠塔寺有没有吃的,我饿上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倒是可以办到的。他见我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就跟我讲,你就蹲在这个油场里,要晚上才能走。因为他不提旗子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张口。他那在黑夜里拿麻绳的样子让我很是有点不舒服,但我又不敢张嘴讲。他又讲,你呆在这里不要站起来。其实他讲话时,我还是站着的,他没有叫我蹲下去,那意思我明白,就是等一会儿,他这个人恐怕要出去,那我就必须要蹲在这个油饼房里,直到晚上,我才会离开这里。
7
后来我自己也不晓得天怎么黑得那么快。我是有点饿了,但我又晓得如果你不在家里边,你就只能挨饿,只有回到家,你才能有吃的,在家里,即使没有吃的你看到你小孩在吃,或者我的小孩在我旁边站着,你就能放心,因为你反正在家里就不会有事。不过,我又想既然人已经出来了,那就把事情办完了再说。还是那个系麻绳的人来接的我,他讲现在要去的场子也不远,是一个叫孙岗的山头,就在埠塔寺界内。后生,你晓得吧,他这个人跟我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他们现在办的事情不能让人知道,如果让人知道不仅这事办不成,而且不堪设想。我是从这个系麻绳人的口气中听出来的,因为之前李老六,六丫头跟我讲话,我没有很绝对地往这方面想,但这个人讲话,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
后来,我们就到了孙岗这个山头。在北山头往北矮一点的一个竹园里,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两进房子,也就是在那里,我吃上了饭,给我吃饭的人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那个系麻绳人坐在堂屋拐角,手上没有拿麻绳,而是一把刀子,我看见他在那里磨着石头。我没多看,那个拿草帽的人,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块地方的人,跟广城畈人有那么一点像,但也像东河口,或是丰乐河南边的人。反正我吃不准。他让我吃饭时,一直看着我。他这人肯定能看出我的年岁,他比我要大,他跟我讲从广城畈走上来不容易。我倒讲走路不难,难就难在在油场里蹲了一天。他呵呵笑了起来,他讲办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感到他会要跟我讲旗子的事了。他让我吃饭不要急,我看院子里还挂了盏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神秘的,因为外边有很大的竹林,所以晚上你能听到风刮过来时,竹林的声响,还有鹊子在竹林里叫。
他见我吃上了,他就把门闩插上了,他回过头来时,我马上从他眼神里看到了跟我一样的穷人的目光,那目光很温和,很正,就好像我庄上人一样的,并且看起来就像是亲戚一样的。他伸着手到了桌角,他很想握我手的样子,但他是个穷人,跟我一样,似乎还不怎么太会跟人家握手,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即使就在今天吧,你很难看到广城畈的人互相握手,这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样子啊。但他又很急切的样子,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伸手掀着我的外褂,向内褂那边掏去。他说,拿来了?我说,拿来了。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把旗子给拿出来,因为我发现他的手已经退下去了。他就那样站在桌角,他的草帽放在桌上,我的手还在内褂那里,没能掏出来。那个系麻绳的人这时不在屋内,屋里光线柔和,点的是桐油灯。屋子的中堂上有裱得很大的画,但我没有细看。他怔在那里,我敢肯定他跟我一样,是个穷人。所以,我在想,假如李老六,六丫头真的懂我的话,她就不应该不把事情说得稍微清楚点,至少她要明明白白跟我讲,既然埠塔寺要旗子,那我该把旗子交给谁呢。我们可以说是僵持在那块儿。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坐下去,在凳子上他掏出烟末子来,放在手心上揉了揉,他又对我说,还是再吃碗饭。我心想多吃人家的不好。但他这么说后,就拿着我的碗,剥开门闩,打开大门,给我添饭去了。我是个穷人,这时我就有点难受了,我想这不对啊,人家对你不错,人家添饭,让你吃饱,不就是因为李老六交代了,是要送旗子来的吗?所以他进来时,我就把旗子从内褂的大布兜里掏出来,我是用双手捧着的。他看见了,没有和我眼睛对视,他显得非常庄重的样子,接过我这旗子,我没想他会怎么办。但他没有把它打开,可以讲动都没有动一下。这时我发现他拿着那旗子,又眼睛盯着他自己的草帽,就这样,他好像向外看了一下。
这时我也才发现大门是没有插上的。我没有吃饭,我停在那儿。我看见他,腾出一只手来,那捧旗子的手还是那样托着旗子,我看着我带来的旗子在他的手上,我感到还是很有含义的,也感到我自己像那么回事,这个人用他腾出来的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草帽,然后就走到左手的里间去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里间去,却要拿起他的草帽呢。我没有明白,我马上就吃完碗里的饭,我坐在那儿,我能听到这个人在里间屋子里的响动,不大,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坐在桐油灯下,感觉这个夏夜,已经有那么一点凉,正因为有那么一点凉,我也才又感到凉中有那么一点暖。我看到小虫子在桐油灯外边晃啊晃的,我周身都在那种又凉又暖的感觉中发抖似的,但我又有些激动,甚至可以说,我人生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没有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
8
我跟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对那个系麻绳的人印象不好,倒不是他在油场里让我困了一天。对那个拿草帽的人,我没有什么认识,可以讲他让我感到有点奇怪,不光是他把旗子拿到里屋去时,听到他那种怪里怪气的响动,还有他那样子跟我脑子里很熟的某种东西有一种相通,所以我总是在揣测,他在哪个地方。我或者见到过,又或者我们在河南沿岸的张母桥街上遇到过,这个印象一旦有了,我就难以抹去,但我晓得这个人跟我自己很像,因为即使不是广城畈人,但我们基本上有那一种差不多的感觉。因为他把旗子收去了,我想我差不多是把事情办好了,我讲过我是个穷人,穷人都是老实人吧,我送了旗子,但接旗子的是这个拿草帽的人,他没有跟我交代什么话,所以我不相信我把旗子交给这个人就算完了。老实人就是这样,我没有想到我马上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啊,不会把旗子交给这么一个拿草帽,跟我在田里头差不多一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是为我们穷人办事情的话,我想他恐怕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我就在那个孙岗山头竹园的大院子里呆了一个晚上,我就睡在堂屋的一个木架上,我听到那个拿草帽的人从里屋到外屋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家,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在夜里,我听到大门也打开过,好像有人进来,还有人低声讲话,但我都没有抬头。堂屋一直点着桐油灯。我确实是个老实人,不然我应该抬头看一看,是什么人在夜里头到孙岗山头来,这样我多少会知道一点他们要办的事情,但我躺在那里,想的倒是假如那个李老六,六丫头来,我心里就会有数,要是她来,我不用抬头,也能感觉出来。
所以我就在堂屋的木架上熬了一个晚上。天刚亮,我就起来了,那时,那个拿草帽的人已经坐在大桌旁抽烟了,是那种很呛的烟叶子。他对我轻轻地笑了笑,也许我要立刻起身告辞,或许未必不可能,但我居然发现我是不能马上走掉的,我感觉我要呆在这儿,所以我就跟拿草帽的人讲,我洗把脸。我没敢讲我要弄一点吃的,但是这个拿草帽的人这时候主动跟我讲了,他讲你饿了吧,早饭不吃了,到中午吃饭吧。我心想我们穷人一般都不会多吃别人的饭,我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媳妇,自己的小孩们,我没有在家外边随便吃过饭。但他讲了,他讲中午还有人,中午一块儿吃饭。现在天刚亮,到中午吃饭时间还早,我这个穷人就是讲不出口,自己要出去转转,或者是要干点别的什么。那个系麻绳的人在外边磨刀,磨的已经不是昨天我见到的那一把,这一把要更大,刀光也更亮。我看他那样子,好像也没有要吃早饭的意思。我听到里屋有响动,已经不是拿草帽那个人弄旗子或是别的什么响动,这是另外的响动。显然,我知道在里屋里还有人,但我一直没有看到有人从里边走出来,我自己也不敢靠近去看。
9
她大概是十点多从里屋出来的,她人很干练。她说,欢迎你加入我们。我听她讲话,虽然也是埠塔寺、阶儿岭、双河这一带的口音,跟我们广城畈差不多,但她讲话很有水平,一听就知道她这是出过门的人。我是个穷人,因为一看她不是李老六,我心里就又没底了,我盼的是李老六。但这个人这一次没有回避旗子的事情。她跟我讲,感谢你为我们做了旗子。我跟你讲,她讲话很有水平,她讲话时那个拿草帽的人坐在板凳上抽烟,那个系麻绳的人已经不磨刀了,他好像是到竹园外边去了。这个女人身边跟着一个人,我听到她喊他大铜。当然,拿草帽的人叫他铜豆。铜豆是个中等个子,很结实的人,不太像庄稼人,也许是街上人,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女人跟我讲,你既然来了,你就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我其实不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后来她就跟我讲,你放心,你是李老六叫来的,跟你讲吧,我是李老六的大表姐呢。我一直不知道她跟李老六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大表姐?李老六的情况我自然也不十分清楚,那她是李老六的大表姐,我就更加无法核定了。不过,我们穷人一般都会相信别人的话。
她在跟我讲话时,一般边上都没有什么人,拿草帽的人有时也到外边去,那个叫铜豆的街上人,有时到里屋去,有时到后边一个院落去。因为竹园很大,几乎把院子都包住了,所以这个场子很安静。中午的饭就是这个女人做的,我给她打下手,在厨房那块,她跟我讲,你要明白,你来了,这是一件大事情。反正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她又跟我讲,你可以考虑清楚,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相信李老六跟我讲的没有错,你不是一般的庄稼人,你是个有头脑的人,她不会看错的。我很想问她李老六到底是什么人?但她讲话的口气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张嘴来问她问题,因为在于她自己,她也有很多难以说清的情况,比如她就跟我讲到,人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虽然不是广城畈人,但她对广城畈也很了解,她说到了广城畈,因为是畈上,临近河冲,所以情况自然是比山里边要好一些。但即使这样,如果往实际里讲,其实还是一样的。她跟我讲,你做了旗子,你是李老六叫来的,我们也很相信你。
总之她绕了许多话,她是个很实在的人,她跟我算是推心置腹的。然后,中午我们吃饭,吃饭时大概有七八个人,我们围坐在那个大桌旁,我看出来大家很平等,但基本上人家都是听这个大表姐的。不过吃饭时,大家没有讲多余的话,我看出来,我是唯一一个到得最晚的人,甚至可以讲我是唯一一个陌生人。看别人的表情,他们互相也不会太熟。吃饭时,大表姐跟我坐在一条凳子上,她还跟我讲埠塔寺这个场子的菜做得跟别处不一样,她自然没有专门提我们广城畈。那些人吃饭都很快,就好像是完成任务似的。即使我这个穷人从来没有见过世面,但我也看得出来,这些人不是走亲戚,因为大家很明显没有亲戚关系,也没有人是互相有什么私话要讲的。我看他们的样子,他们是穷人,但他们眼睛都亮亮的,这让我有点后怕,因为我从李老六,六丫头的眼神里也看到过这种亮色。
我只要不看大表姐,我就把大表姐当成李老六一样的,但事实上大表姐比李老六要大一点,李老六也就十六七岁吧,最多十八岁吧,但大表姐应该有二十岁吧。一个二十岁的大表姐能有那样的举止,这在农村还是让人刮目相看,最重要的是,别人都拿她当回事,虽然没有什么请示,但即使是吃完了放碗退出桌子,人家也要看她一下,以表示让她知道他要出去了。大表姐没有脾气,人很和气,但大表姐不怒自威,我简直有点服她,但遗憾的是,她不是六丫头,所以我这个穷人就追不到根,我想到的就是什么人叫我干什么事,那我就跟这个人讲。但大表姐还是不那么迁就我,她没有跟别人讲我,但她一直让我坐在她边上。别人吃完都退出去之后,我还僵在那儿,我恐怕是想让大表姐给我些说法,因为我不敢张口问,又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打交道,现在我更是提不起要离开的事了,因为我从她跟我的谈话中听出来,事情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离开呢。但是,我能坚持在这儿,跟我一直在头脑中把她跟李老六混为一谈是有关系的,再说她自己也说她是李老六的大表姐,也讲了是李老六叫我来的,那她就和李老六一样了。
10
对了,后生,她就是汪孝之。我跟你讲,她就是汪孝之,你说我跟她算不算近,当然是近了,她和我一起做饭,跟我讲这个那个的,我跟她怎么可能不近呢。她一开始没有跟我讲全部实话,可以讲是在考验我,这个我后来都看出来了。她跟我讲过不少心里话,看出来我的心思跟她不大一样,她就讲因为人穷,所以有时候看事情就看不开,但看开的人未必是穷人,所以不一定谈到一块儿。那要谈到一块儿,穷人就要跟穷人谈。她跟我谈的话很多,后来我都记得住,她讲我们要改变这个样子,不是埠塔寺、九十铺要改变,东河口、范家店都要改变,广城畈也要改变。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对的。她讲,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就是要改变这个样子。当然起初她没讲怎么改变,但她讲得很细,她讲了你出门肯定也舍不下你小孩。我讲是的。她讲舍不下也要舍下,你想想为什么我们小孩是那个样子。我说,我们小孩可怜。她讲,是可怜,但你想要让以后的小孩不可怜,有学上,有钱花,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日子不是本来就这个样子的。
她在跟我讲话时,如果她不问我,我就不讲,因为我听出来她是个出过门的人,她这些话是别人讲给她听,而且她自己有体会的,所以轮不到我来讲。她讲,我们不是要好生活,我们要好生活我们就要争取。她跟我讲话不分场合,做饭时也行,坐大板凳上也行,后来她就站在堂屋的纸画前跟我讲。她讲,你可以考虑。后来我想我是听明白了,她估计到即使我明白了,我也讲不出来,所以每次讲长时间的话以后,她都嘱咐我可以考虑考虑。
这样,我就在孙岗竹园里呆了大概有五天,我真难以想象我小孩们可怜死了,他们在家里怎么办,我阿老身体不行,恐怕随时都能死掉,我媳妇表面上骨头硬,其实我不在家,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而且我已经六天没有回家了,我小孩们可怜死了,但我就是不能动。我喜欢听大表姐讲话,因为大表姐讲的有道理,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这个人悟性不好,加上我写不来字,我只认得少数些字,那我跟他们不一样,再说除了大表姐,别人不跟我讲话。但我想,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这样对待你,跟你讲这些话,而且都是推心置腹的。再说她一直叫我考虑,我想她又没有逼我表态。后来,我看到大表姐叹气,大概是她以为她这样跟我讲话,她是把我当个人物看待的,但我确实不知道讲什么。
直到有一天,大概是第六天吧,下午的时候,大表姐把我叫到里屋去了,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里屋很大,并且样子很奇怪,是山里人里屋的样式,在后墙那儿还有一道门,大概是开向山坡上的后院,从这后院又能进竹园,在那高起来的里屋的后半边有一只很大的木箱子,大表姐坐在那只木箱子边上,她边上站着拿草帽的人。而那个叫铜豆的人坐在里屋前半间的窗下。就是在这间屋子,大表姐跟我讲了她的全部事情。她是这么讲的,她讲你来了已经六天了,我一直在跟你谈,你话不多,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不错的人,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起义,我跟你讲过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讲起义,当然她的话比这个要长,可以讲她很会讲话,但意思就是这样的。她讲,我们要起义,我们要打土豪分土地,我们要革命。对,我听到她跟我讲革命。她问我,你听到没有。我说,我听到了。她又讲,我叫你考虑,其实不为别的,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穷人当家做主而努力,我们不怕死,对吧,我们就是要干这个。她讲了很多,但我听得懂,她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埠塔寺的起义据点。她拍了拍箱子,她跟我讲箱子里有枪,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枪离我这么近。她在喝水时,那个拿草帽的人到我边上对我说,汪孝之同志已经和你谈了几天,她已经考验得很完全了,知道你是个信得过的人,她跟你谈穷人,谈生活,实际上就是要一起革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筹备起义,所以如果不信任你,我们是不敢跟你讲的。我心里在想,假如革命了,我能做什么,我们穷人总是这样,我们虽然会想到自己,但想到自己时,也是在想自己对别人会有什么作用。汪孝之一直手按在那只黑色的大木箱上,她讲,我们的革命既是为自己,又不是完全为自己,我们就是要改变这可恶的旧社会。她讲话时大义凛然,虽然她没有多问我话,但我听得出来,她是对我很尽心尽意的。
11
我在孙岗山头竹园又呆了好几天,因为时间一长,我这个穷人就没有走的意思了,我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他们是为我们穷人干事情的人。直到有一天黄昏,孙岗山头黑得比山底下要迟一些,我正在跟汪孝之做饭,因为在白天,她已经反复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我参加你们的起义。她很冷静,她告诉我起义就是杀头的事情,我讲我知道起义就是杀头,她讲你晓得杀头的意思?我讲我晓得。后生,你知道吧,汪孝之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她是一个看起来冷静,但心里边一直装着别人的人。她是李老六的大表姐,她也就二十岁出头吧,但她的讲话,还有那种感觉,俨然就是个领导,当然领导这个词我也是在孙岗才听来的。后生,你不晓得汪孝之这个人有多神,反正那时我虽然眼一闭,还当她是李老六,但她跟李老六不同,她在白天跟我讲,第二天给我看枪,你晓得吧,我心情很激动啊,你想想我一个农村人,承蒙他们看得起,不仅为我们办事,还领着我一起。我想我什么也讲不出了,我激动得很。
可以讲,关于种地、生活,还有活法,汪孝之比李老六跟我讲得多,而且实在,当然我有时也听到她跟戴草帽的人讲到更大的事情,我听得不是很懂,因为我晓得她讲的根据地,就是自己有了土地啦,我不晓得她讲的是要连成一片,要跟外边连成一片,要把队伍拉出去。我在中间听到他们讲过在双河的军械库,他们要把那个军械库拿下。他们晚上在桐油灯下开会,我就坐在厨房,那时我还没有明确讲我参加起义,但那天下午,汪孝之是跟我挑明了讲,她讲你答应了参加起义,你是广城畈人,你来了也不短时间了。她总在说,你是我表妹李老六介绍来的,她果然没有看错人,你是个忠义之人,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虽然你没有张嘴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块起义的料。她的话让我沸腾,因为她是见过世面的人,我说过我是个穷人,可以讲面对汪孝之我没有什么可以张口的,她叫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但是,事情就出在那天黄昏。
12
我答应她参加起义,但那时我对起义没有什么认识,也不可能有什么认识。我心里一直想的是她答应过第二天就让我看看她讲话时压住的那只大木箱里的手枪。
但是,我前边说了,还没有等到第二天,就在那天黄昏,大概天色还不是太晚,估计山上比山下边黑得迟一点,但这时从竹园外边响起了枪声,接着就是铜豆从外边闯进来,他跟汪孝之讲,不好,山下边还有人,在山北边也有人开枪放倒了我们的人。不用讲,有人告了密,敌人已经先下手了,他们已经从山北边包抄上来,他们要把起义的人先干掉。我没有见过这些事情,但我看汪孝之这时候很冷静,我也是在那一刻感觉到她是起过义的人,不然她不可能这么冷静。当然后来也就知道她确实也在东河口霍山那边搞过起义,不过汪孝之从木箱里取出枪时,我没有看清,她也没有在那时向我下达任何命令,而是让我到院子里去。房子中的那几个人,我都晓得,我在外边能听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他们声音都很仓促,甚至有点尖细,我听得见那个拿草帽的人声音最大,他好像很愤怒,但是,我听到汪孝之训斥了他,好像他们在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的样子,就从堂屋出来了。这时候山后竹园的坡上又传来枪声,我就站在那里。
这时候,我看见那个拿草帽的人,忽然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长刀,这刀有点怪,因为刀把上拴了布条,我握在手里,他要带我从前边下山。汪孝之握着枪,已经从墙头那边翻出去。我最后看见她一眼,她没有瞅我,只是向我们往前边院门的方向指了一下,我晓得她这是在跟拿草帽的人命令让我们从那里冲出去。我这次看见她的枪,是那种乌黑的,枪筒有点长,后边的部分好像还有木头,因为她在翻墙时趴了一小会儿,好像上边的人在使劲,但她脚上踏不住墙眼,所以她就在那用枪支着墙拐,我才得以看见她那只枪,只可惜,我没能细细看。后来她翻过墙,枪声更加密集了,我们很快从前门那里往南冲,那有一个村庄,那些打枪的人,我能听得见也是冲着我们向南的方向追过来,这可能也是他们商量好的,要把敌人引到这个方向来。就这样汪孝之应该是从院墙翻到东边,她是往双河的方向撤退。
13
我们往南跑得很快,那个拿草帽的男人平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劲,他跑起来比我快多了,我这才想起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跑了,在小时候,或许在河滩上跑过,但十几岁以后就再没有跑过,对于一个穷人来讲,轻易是不会跑的,没有什么东西逼着你跑,你一个人在农村跑起来会让人笑话,所以当那个拿草帽的人在前边飞快地往山下跑时,我还有点不适应,并且我总想笑他。后生,你晓得吧,我们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总会不好意思,如果没有别人做个样子给你看,你自己是不会做的,所以我起初是落在后边的,他跑一小段,他就会回头喊我,他讲刘行远你快一点。我就赶忙往山下跑,起初我没有听到枪声,后来枪就在后边响,我晓得起先是因为有个小山头是要翻过来的,敌人在后边,他们翻那个小山头时,我们在下这个山头,再往前,我们是要上那个山头,上那个山头时,敌人在下前一个山头,虽然天刚黑,但还是能看得见,我回头看见他们有十多个人,在松树林里一隐一隐的,他们下得很快,但我们上山不可能快,这时我才感到害怕了,因为那枪声很近,我们在上这个山,他们在下那个山,其实隔着个山沟,已经很近,可以讲都能看得见对方的脸,要不是天晚了,无论如何他们能瞄准直接开枪来杀我们,但他们也不是连着放枪,大概是松树和石头老是挡着视线。最近的一次,我能听得见他们子弹打过来打在松树中间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我听得见他们在叫,你们跑不掉的。
14
我们已经往三口塘跑了,中间我是想过要调头往东头的田地里跑,即使田地绊人,但毕竟那里他们五六个人也会慢下来。但是,我没敢跟这个拿草帽的人讲。我们跑到三口塘塘口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三口塘是三大块镜子样的东西,我们是跑在中间的塘埂上,我听得到那五六个也已经冲下山来,他们隔着田,离我们没有多远。可以讲,那个拿草帽的人一直很勇敢,但他的冷静,跟汪孝之的冷静不太一样,即使他在前边跑时,他也总显得很有心事的样子,不过我也不敢问他,他有时回头让我跑快一点时,我就加力,但我始终没有跑到他前头去。我总在想,他是要我跟着他跑的,我们穷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就好像我跑在他前边就会是个错误一样。如果那时我们想个法子,比如我们不从中间塘埂跑,而是从三口塘西边那条水沟沿子跑,可能情况也不一样。
但是,很快我听到枪响了,并且声音很密集,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虽然之前他们放过枪,但那是在山上,现在是在池塘上,他们放枪,枪是平的吧,我晓得这时候枪长了眼睛了。但我没有什么反应,反正我还是在后边跑,但我突然看见我前边的拿草帽的人闪了一下,我以为他闪了腿,但他还是坚持着跳了一下,就是这一下,他把速度提起来了,他扭过脸来跟我讲,要快。也很奇怪,就是从三口塘跑过去之后,有一个涵洞,涵洞边上有两条路,他在涵洞口那跟我讲,我们向西跑。因为涵洞挡住了来路,我听见后边的人朝东岔路追过去,但东岔路有个上坡,一到坡上,那些人如果看到路上没人,他们就会返回来追西岔路。就是在那个岔路快到大槐树山脚下时,这个拿草帽的人倒下了,我看到他肚子上在淌血,血一直在往下淌,捂都捂不住,衣服上全是血。他手里拿着枪,另一只手还是拿着帽子,他坐在草堆前,他跟我讲,只要进了山,就没有事了。大槐树山大,下山路多,到了山顶就往北跑,就没有事了。
我背起他,他两只手担在我肩上,其实他并不重。我背他上山时,能听到那些人已经从西岔路那边过来了。他跟我讲不要怕,这个大槐树山山大,只要背到山顶就没有事了。我有力气,我居然还有力气,我们穷人就是有一把力气,所以我背他时并不觉得累。在山上时,虽然能听到岔路上那五六个人在叫,但我们仍在爬山,我是抓住那些枯枝子一步步往上爬。我跟他讲,你放心,我一定把你背到山上。但我心里在想,如果我们先前不是跑到三口塘,那敌人就打不中我们,因为月色大,月亮亮,借着池塘的反光,而且是夹在三个塘中间的塘埂,他们瞄准起来就容易了,幸亏没有一枪撂倒,不然就死定了。他是跑在前边的,但开枪的人没有打中我,却打中了他,也可能子弹不长眼睛吧,反正现在他受伤了,我就要把他背到山顶上。我背着这个拿草帽的人,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可能一直背着他,就是说以我那时候的见识,我没有办法做到更多的,因为是他在指挥我,所以即使是我背着他,他也是一直在跟我讲这讲那的,甚至他都知道爬的每一步离山顶那棵大槐树还有多远。他也问过我累不累。我说我不累,确实我不累,如果可能,我可以一直这样背下去,但显然这也不是办法,但首先我要把他背到山顶上。
15
当然后来我们到了山顶上,我们才发现这个大槐树山虽然讲很大很高,但爬上去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山下边是有路的,而且跟别的山之间不是连在一块儿的,可以讲它山下环着一圈都有路,别人怎么都好把你看住,你想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不过我们在山顶时间也不长,他靠在大槐树上,这个场子能把山下都看得很清楚,我看到有人在上山,顺着我们上来那个方向附近,能听到有人在叫,在山下又有人。不用讲,这个场子通东河口有路,反正敌人又来了一帮人,这个在山顶上都能看出来。他肚子上有血,他坐着,但姿势还可以,可以讲他这个人不会倒下的,他是否意识到逃到大槐树山顶是个错误我不知道,但他还是挺在那块儿。我实在太累了,但我没有讲,我讲了也没有人听。他问我,他们有多少人,我讲又来了一大帮。他讲,你不要怕,不要紧。我虽然也不怕,但我跟他看法不一样。
这时我看出这个人肯定不行了,我能看得出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手枪都耷拉在下边,但整个人就顺在那个场子,他有时也昂昂头,他跟我讲他就是要看看这个树,他这个话让我有点生气,我心想这个时候,你不能只想着自己要看看树,你就让我把你背上来,你晓得我背你上来不容易。他跟我讲,我就是要再来看看这个树,他讲他从小就上这个山,他就在这个树边上玩,他就在这个场子看四周。他讲,也能看到你们广城畈呢。现在月亮已经快要下去了,可以讲我们逃了大半夜,他力气不多了,他还在讲,但我不太想听,因为敌人正在往山上爬。如果他们上来,他们不是孬子,他们晓得我们会在大槐树下,他们那么一大帮人,你躲在哪都是躲不过的。他还讲他以前到这大树边上,跟这个大树,他讲个没完。所以我就摸摸他肚子,现在血还在淌,但只是一阵一阵的,可能没有多少血了。我一摸肚子才发现因为他坐着,所以他肠子就拖出来了,软软的就在衣拐子里头,我把它往里推了推。他笑了笑,又叹了口气,他讲,你不要怕。不过他现在这么讲,我已经听不出有什么意思了。后来,我能听到上山的人已经不远了,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估计小一会子就能到大槐树下。我想这个拿草帽的人,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拿手枪的手在地上支了一下,他动作很困难,这时我想劝他至少可以把手上的草帽拿掉吧,现在拿这草帽有什么意思啊,但我前边跟你讲过我们穷人很少敢讲跟自己无关的话,他要把草帽拿着就让他拿着吧,反正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6
当然,在那帮人没有追到大槐树跟前之前,我背着他下山了,下山的路是他给我找的,那是一条斜路,一直插到山底,是个带石头的像竖直的河道样的东西,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晓得这个下山的路的,反正绕过了几棵金树,金树中间有一个洞,我想他之所以上山,可能跟这个有关,不然他也不敢,在敌人那么近时,他还不着急。
我背着他,从这河道样的坡子往下走,因为背着他,我不敢快,不然下山走那个路会很轻松。好在,现在这夜里,天可能快亮了,月亮挡在山那边,天上有星星,我看出来这是往北,往下边去时,你能听到那群敌人在山顶开枪,不要讲,他们是发现了血迹,他们即使找不到这条往下的坡子,但他们在上边能看到山脚四周,所以一旦你跑了下去,他们还是会看见你。后生,我跟你讲我是个老实人,我即使有什么想法,我也不可能跟他有什么沟通,但我背他下山时,他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我知道他是连说话都感到费力了,所以他尽量少讲话,再说现在就这一条路,下了山再讲吧。我估计他血淌得差不多了,因为不是一直在淌,只是过一阵子,才淌那么一点,好像体内的血是挤着挤着,蓄了一点再从肚子上的那个口子淌出来。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在想即使我再听话,但我总有累倒的时候,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跑不掉了,可以讲我是在这时候才想到我们有可能是跑不掉的,我在想要是我们跑不掉,那我们也就只能被他们杀了,这个道理我是懂的。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敢跟他讲,我怎么能跟他讲呢,我现在背着他,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跟我讲话,那我就要听他的。是的,后生,我是个老实人,所以当我背着他,下到山脚时,我才发现我们已经离开那座大槐树山了,真是奇怪,我回头看在山脚下有个大土台,原来从那土台底下我们跳过河沟,然后上的大路,我们见敌人还在山上。因为他们在放枪,可以讲枪声比之前密集了,但因为月亮快要下去了,他们想射到我们也很难,但他们应该看得见我们在山脚下。我背着他往前,但我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我发现我们是在一个河坡上,刚才山上的那道坡就是连到这条河的。对,后生,这就是陈家河,我从小就晓得在我们广城畈有条丰乐河,在打山在界儿岭北有一条陈家河,两条河在双河那块就要合在一块儿,只隔着一两里路,所以那场子叫双河,但现在这场子,离广城畈很远了,我真想不到我们已经逃那么远了。
敌人正在下山,当然他们是顺着北边的山林下来的,估计没有那么快。我背着他到了一座桥头,他跟我讲上桥。我讲那边好跑吧。他见我答话,他晓得我是在问他,这也是我唯一一次问他,因为我感到他整个人都扁了,整个人轻了许多,我想这样的话,我背着他也没事,他血要是淌完了,他也就没有重量了。我上了桥,在中间时,他让我把他放下来。他讲,你把我靠在那桥边的木头上。木头很矮,可以讲下边河水不小,听不见水声。他靠在那木头上,用拿草帽的手支在地上,拿手枪的手捂着肚子,我看到他肠子都跑出来了,堆在他腿上,他这个人像个壳子一样。
现在天快要亮了,我站在他面前,我不晓得怎么办,虽然讲他轻了许多,但他仍是有重量的。我放下他,我才晓得我们穷人不容易,我已经背了他有大半夜了,我真不容易。他看了看大槐树山,他跟我讲,你不用怕。我一直听他这么讲,但我这个穷人起初是没有听懂的,我就是直来直去的人,我不懂他讲什么。后来,他把枪举起来了,他对准了我,他几乎没有什么力气,但即使这样,他就拿枪对着我,我也没有动,我也讲不出话来,我也没有问他,他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他的手在那个板机上,因为那儿有个圈子,圈里有个舌子,我看得出来,他可以扣的,他就这样指着我,他跟我讲,你不用怕。我真想哭,是啊,他拿枪指着我,我想到我小孩,我媳妇,我阿老,我想到了广城畈,他怎么拿枪指着我呢。
他没有扣板机,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讲,你站近点。于是我就靠近他一点,他拿枪仍指着我,他最后是这样讲的,他讲,刘行远,我本来是要杀你的,但我不会杀你,我们开过会,我跟铜豆讲,如果起义失败,我们要杀掉你,因为我们不了解你,但你晓得的太多。但是,汪孝之不同意,是她讲不能杀你,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杀你。她讲了,她信任你是个可靠的人,她相信你。既然她说不杀你,她就是组织,这是组织的决定,所以我不杀你,一路上你背着我,我让你背我上大槐树山顶,我本来是想在那大树下杀你,你晓得我们起义可以败,但我们不能让敌人掌握我们,这是我一直跟汪孝之讲要杀你的原因,但汪孝之不同意,她是组织,既然她这么讲,我就不杀你,可我本来是要杀你的,我自己快不行了,你看到了,我马上就要死了,可我,我听组织的,听汪孝之的,我不杀你了,你不用怕,不用怕了,我听组织的……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讲,直到他掉转枪口,对着自己的头开了枪,扑通一声,翻过木头,从桥上栽入河水中,我看见他漂在河水上,一直向下游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