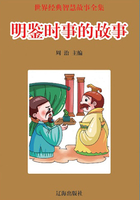翌日,孔令岳再次登门造访。他依旧穿着儒服,执着纸扇,只是手时不时地往眉角上掩,细一看,原是眉角处肿了一块。
“孔公子,您这是……”秦瑶疑惑地问。
孔令岳叹了一口气:“时运不佳,昨天夜里,书院中竟遭了贼子,我这眉角便是叫贼子打的,所幸不曾伤及性命,也不曾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此亦不幸中的万幸,孔公子莫要记怀了,好生养伤才是。”秦瑶低头略表遗憾,杏目却有意无意地瞄了殿小二一眼。
孔令岳拱手一笑:“倒叫秦掌柜为在下担忧了。”
殿小二坐在二楼的围栏上,鄙夷地低咒了一句:“虚伪!”
闲坐片刻,孔令岳又道:“听秦掌柜与小二哥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倒带着些京腔,不知两位可是来自京城?”
秦瑶道:“正是,几年前为避战乱来到此地,因贪图安逸,便也不再搬回去了。”
孔令岳点点头:“京中虽繁华,却是个是非之地,不瞒您说,在下的祖籍亦在京城,三十多年前也是因为战乱而举家搬至南方,那时在下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呢。”
“是么?”秦瑶抬头打量了他一眼,他看起来像是只有二十七八岁,不想竟三十有几。三十多年前,燕朝还不曾建立,前朝的皇帝残暴不仁,而官场腐败,以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先帝体恤百姓,毅然举兵起义,推翻前朝,灭暴君,建立了如今的燕朝。数十年来,国中亦算国泰民安,只除了几年前太子与瑞王那一场夺权之战。那时她与殿小二也陷在战乱的中心,后来,她及早抽身出来了,殿小二却没有这么幸运,虽说他如今仍安好无恙,但想必也经历过一场痛苦的挣扎。
“然而,话虽如此,若一场战乱能换几年太平,倒也值得。”孔令岳又道。
“孔公子所言有理。”
殿小二却不以为然,翘着二郎腿仰望着屋梁道:“身居庙堂之外,却妄议朝政,分明一窍不通,却道深谙其理,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呢,好生管管自己的嘴吧,省得有心人听了把你当反贼抓了去。”他这话自然有夸大之处,但他实在看不惯那两人言谈甚欢的模样,便忍不住出言讽刺。
孔令岳闻言,却笑了起来,合起扇子一垂首:“多谢小二哥良言提醒,在下不胜感激,自当铭记于心。”
秦瑶瞪了殿小二一眼,回头尴尬地看向孔令岳:“小二顽劣,望孔公子不要见怪。”
孔令岳摇摇扇子:“秦掌柜不必介怀。”
殿小二哼了一声:“我说错了么?若真有本事,何不考取功名,报效朝廷?枉你饱读圣贤之书,却待在这小城中当一个小小的教书夫子,该不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潜伏在此处忍辱负重吧?”
孔令岳微微怔了一下,一丝不自然的神色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秦瑶不曾察觉,但殿小二却看得清清楚楚。
孔令岳却道:“奈何在下确实不喜角逐权利。考取功名,入了庙堂,博了名利又如何?终日钩心斗角,时常担惊受怕,倒不如在此地当个教书夫子逍遥自在。”
“孔公子高见。”秦瑶由衷赞道,眼神中多了几分欣赏。而殿小二的目光中却多了几分怨毒,他愤恨地捏紧了拳头。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孔令岳总算起身告辞,按例又邀秦瑶一同游江。秦瑶犹豫了一阵,竟然同意了。
孔令岳喜上眉梢:“那么,三日后,在下便在渡口处静候掌柜的到来。”
孔令岳前脚才迈出栈门,殿小二便沉着脸跳到秦瑶的面前:“掌柜的,你为何要答应他?”
秦瑶白了他一眼:“人家诚意拳拳,我怎么就不能答应了?”事实上,经过数日的接触,她倒觉得这孔令岳确是个不错的人,虽说话文绉绉的,显得过于客气疏离,却很是健谈,从不摆读书人的架子,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与她趣味相投。
“掌柜的,您听我说,还是少些与这人来往吧,他懂武功,想来不是个教书的夫子这般简单。”
秦瑶轻笑:“这倒奇了,你一个店小二可以懂武,他一个教书夫子怎么就不可以了?”
“这……”
“再者,他虽说脸上的伤是贼子打的,但我猜,那贼子十有八九是你。你倒好,打了人还来告状。”
殿小二气结:“秦瑶,你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好,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去找证据!”说罢,他便如潜龙出渊般飞了出去,须臾之后,又提着一个人飞了回来。
他将脸肿得想猪头一般的杜潮守推到秦瑶面前:“看吧,把他打成这个模样的就是那个夫子,如此一个弱质纤纤的少年,却被他打成这个模样,可见他的心肠有多毒辣。”
杜潮守一个劲地点头,却哭丧着脸:“头儿,我这脸本来就无法见人了,你却还特地把我给拎出来……”
秦瑶抱着胸绕着杜潮守转了几圈:“确实惨不忍睹。姑且不论真假,就当这伤真的是他打出来的,可他平白无故地又何必要为难你?想必是你先动手的吧?弄成这般模样,也是你咎由自取。”
杜潮守扁起了嘴,泪流满面,眼里全是悲愤,不知是为自己不值,还是为了自家的头儿而感到不平。
殿小二气不打一处来,却仍不肯死心,捏着下巴踱起步来。
秦瑶慢条斯理地步向柜台,嫣然淡笑,俨然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殿小二忽地停了下来,愤恨地盯着秦瑶道:“你等着,我绝对会把那家伙的真面目揭发出来的!”
秦瑶轻轻一笑,不以为意。
未料,殿小二还当真说到做到,竟带着她去跟踪孔令岳。秦瑶本不予理会,奈何敌不过殿小二的死缠烂打,只得依了他。于是,便有了如今这一幕:她与殿小二躲在暗角处,而前方不远,孔令岳正在一笔墨铺子中挑砚台。
“店家,您这砚台是不错,但价格却不大合理。”孔令岳道。
殿小二哼唧哼唧,得意地看向秦瑶:“看吧,这么一个砚台还讨价还价,吝啬!”
秦瑶不赞同地摇摇头:“这是勤俭节约,哪像某些富家公子一般,只知道铺张浪费,须知商家无良啊,若是换了我,定会把价格压得更低。”
殿小二撇撇嘴,不再说什么。
那边孔令岳已经离开了铺子,殿小二与秦瑶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途中但见孔令岳施舍了几个小乞丐,扶起了一位跌倒的老妇人,还赶走了几个调戏少女的流氓。
殿小二的脸色越来越沉,秦瑶眼中的欣赏却越来越浓,只听她道:“助人为乐,彬彬有礼,确是一个好人。你看这人来人往,他却一枝独秀,想来必非池中之物,却淡泊名利,甘愿隐匿于市井之间,难得啊。”
殿小二咬牙切齿:“装模作样,演戏谁不会?伪善!”
秦瑶啧啧摇首:“你就是装也装不出来。”
殿小二哼了一声,只好作罢,却仍不死心,第二日又领着秦瑶去了同方书院。
同方书院是个雅致的地方,拱门背后翠竹丛丛,鹅卵石铺作的小路蜿蜒着,中间岔开两道,一道通向了一座竹亭,而另一道的尽头则是几幢小筑。此时童生们正在读书,书声朗朗,儒风盎然。
殿小二与秦瑶伏在墙头上探视着,只见孔令岳手执戒尺,正在童生间巡着,偶遇一两个童生提问,便耐心地解答。
秦瑶又赞道:“谆谆教诲,确是个好夫子,将来若是有了孩子,想必也是个好父亲。”
殿小二着急了:“难道你还想替他生孩子不成?”
秦瑶的唇角弯了起来:“ 若嫁了他,给他生孩子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殿小二一听,险些自墙头栽了下去。
却听院中地读书声突然变得整齐,竟念起了《诗经》里的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墙头上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不料竟对上了孔令岳的目光。“难得秦掌柜大驾光临,如何不走正门?”孔令岳步出庭院道。
秦瑶尴尬地笑笑,扯了扯殿小二的衣袖。殿小二极不情愿地揽起她,一同跳下了墙头。
“今日路过此处,好奇窥探了一二,望孔公子海涵。”秦瑶道。
“无妨,两位能光临敝院,在下但觉蓬荜生辉。”孔令岳道。
殿小二不说话,只在一旁闷吭清咳。
秦瑶只好陪笑:“栈中还有事,秦瑶只好先行告辞了。”
“秦掌柜慢走,但,还请掌柜勿忘了后天的共游之约。”
秦瑶施礼:“自然……”但话音未落,人便已被殿小二拉了出去。
是夜,殿小二又到杜潮守处共商“要事”。
“进退相宜,投其所好,看来此人做足了工夫,比想象中更棘手啊。”杜潮守捧着自己的肿脸道。
殿小二吭了一声,算是认同了他的话。
但是殿小二又岂肯忍气吞声?他细细思索了一阵,道:“你去找林简,务必要查出这夫子的来历。”
“是,头儿。”
殿小二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绝对要阻止秦瑶与孔令岳共游柳江,不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次日黄昏,夜幕初临,李婶慌慌张张地找到小二:“小二,不好了,不好了!方才有几个黑衣人闯了进来,掌柜的被……被……”
殿小二也着急了,却道:“李婶,您先别着急,掌柜的到底怎么了?”
李婶缓了一口气:“掌柜的,被掳走了!”
殿小二大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冲到了后院,然而院中安静悄然,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