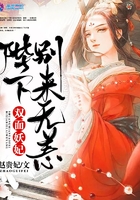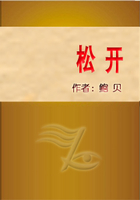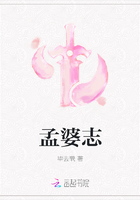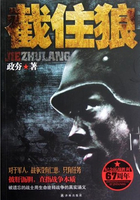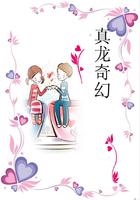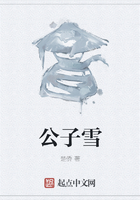置之死地而后生,逼着自己咬牙,这是芩姐的处事原则,我常常惊异她对自己的狠劲儿,她会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在对待学问上,从不偷懒,在对待错误上,从不原谅自己。我2001年到日本去看望她,她的房间门口挂着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反省中”,她说她得常常想想,每天是不是有该干的事没干,或干错了事而不觉得……五十多岁的人了,应该说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她却还不断给自己找事。她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这次回到北京,却突然向我提出要学习英语,我的丈夫是英语教授,她认为这是近水楼台,至少音标先得学会吧,其他可以自己慢慢来……我问她想干什么,她说电脑要用,交流要用,她还计划要绕地球旅行一周。这个人哪……
回首往事,虽然我们年少时家境窘迫,生活中满是酸涩,但也有我们的无穷乐趣,有我们五彩的梦。那是我们人生的起点,是我们人生的基础所在。芩姐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对文学、美术的爱好,都和她分不开。
1968年秋,芩姐分配去了西安。火车站上,和她一起走的同学几乎全家都来送行,带着大包小包,父母亲拉着孩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情景让人羡慕。而她,只有我一个人来送,小小的一件行李,连午饭也没有带,穿着一件很寒酸的半旧的衬衫。母亲在家中躺着,患了绝症,已无精力顾及离家的儿女,她是心事重重走出家门的。我们躲开喧闹的人群,她一遍一遍地嘱咐我,叫我多帮母亲干活儿,别忘了带母亲去看病,我们都知道,母亲生日无多了——重压之下,她的心在滴血,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火车向西开走了,我看见了芩姐眼里的泪水,我跟着火车跑着——后来听跟芩姐一起走的同学讲,在火车上,她坐在角落里,一直无声地流泪,从北京一直哭到保定。直至今日,我每到火车站总是心情很坏,或许是这第一次的离别和我后来插队时的来来往往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惨。
芩姐走后,我收拾她睡的床铺时,发现了一沓子纸,原来是过去我画的一组漫画,那是“文革”中在家逍遥时给芩姐贴的大字报。记得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发生了口角,芩姐出去了,我气犹未尽找来了纸、笔和墨汁,开始又写又画。第一张是“叶广芩走白专道路”,画的是她骑着一头瘸驴,左手挥舞着鞭子,右手高举着一个大三角板,嘴里高喊着“学好数理化,骑驴走天下!”第二张是“叶广芩贪图安逸享受”,画的是她舒服地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是许许多多好吃的,有话梅、咸带鱼什么的。这两样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她最爱吃的——画完后,我把这一组漫画贴在她床边的墙上,很是得意。晚上,芩姐回来发现了她床边的漫画,我等着她发火,没想到她看着看着,扑哧一下乐了,一边往下揭,一边说:“这可是有纪念意义,我得好好保存。”说着把它们压在了褥子底下。眼下,看着这一张张漫画,我的眼睛湿润了,物在,人却去了,心里空落落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离别,什么叫思念。本想把这几张画好好保存留做纪念,但后来也丢失了。
1969年1月,我插队去了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和芩姐在同一个省份。
或许是离开了家乡,彼此分离,也或许是长大了的缘故,我们学会了彼此关心,相互牵挂。
我到陕北后,芩姐因为有了工作,挣了工资,承担了我的经济费用。刚到陕北第一年,我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全是粗粮,肠胃不好,拉肚子持续了半年多。初夏的一天,芩姐突然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说:“正好有便车到延安,我来看看你。”我真是震惊了,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说是有便车,其实从西安到我们村里,足足有一千多里的路程,她到了延安后,还要换车到延长县,从县里到村里又要走五十里山路,真不知她一个人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芩姐的到来,着实让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我更是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从老乡那儿借来二十个鸡蛋,一下子都给炒了,没有油,干炒,那些鸡蛋变成了一个个硬疙瘩。下乡后,我凭着从北京带来的几本芩姐用过的医学教科书和对医学浓厚的兴趣,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芩姐在我那儿期间,刚好有几个病人,她陪着我上东坡儿下西沟地去老乡家看望,我跟她又学了不少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她耐心地给我讲在不具备化验条件情况下,怎样区分痢疾和肠炎,医疗器具怎样消毒,农村常见病的最基本处理方法——后来在芩姐的小说《醒也无聊》里边,有个在陕北插队的知青形象金瑞,她将金瑞在陕北插队的情节写得活灵活现,许多人都以为她一定有过陕北插队经历,其实那里边很多是她当年住在我们村里的观察和体会。洞察生活的细致入微,体会周围人的言语颜色,可能是来自芩姐敏感的性情和内向的性格,她常常在不动声色中,将周围的一切审视得清楚透彻,做到心中有数。那时她根本没有想过写小说,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她有当作家的梦想,但是这种从小特殊经历造成的生活态度,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成为她的本真。
芩姐从陕北回到西安。没想到等着她的是一场厄运。回去后不久,因为“诗”的问题,芩姐被上纲上线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年她二十岁,被下放到黄河滩放猪。通信地址的改变,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我再三追问下,芩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个大概。我给她回信说你不会反对毛主席,我相信你。你一定要好好的!那段时间,我很担心,害怕,怕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怕她挺不过这一关,怕我永远失去她。几十年过去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从未听她细讲过,直到她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出版后,我才清楚地知道当时她所经历的一切。她不愿意说那段日子,那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那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像当年在热孝中,躲避人们各色的目光一样,她坚守住自己的人格,将牙咬碎,咽进肚里。最终,她挺过来了。不光挺过来了,而且还利用独自一人放猪的机会自学了日语。她先是可以熟练地用日语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而后又将《汉方研究》杂志上的一些科普小文章试着翻译出来,写了厚厚的几本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把这些书稿分成两部分交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个出版社不约而同全都给出版了。大概没有谁知道,芩姐最初涉足文坛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她翻译了不少小说,那是她写作的准备阶段,也未可知。芩姐自嘲说自己是因祸得福,说这日语是“捡来的”。我不能不佩服芩姐面对逆境的奋发拼搏精神,她的永不服输的劲头。她经历了一次涅槃,得到了新生,得到了升华。
芩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年轻时的磨难是一笔财富。翻弄这些财富,是与历史相对的会意,是走过人生的豁达。不忘记过去,也不为记忆所摧残。
后来,我被招工到了陕南汉中。母亲去世了,这一打击对我是致命的,身心几乎全垮了。如果说父亲的去世是一棵大树倒了的话,那母亲的去世就是整个大厦全塌了。再回北京探亲,我去探谁?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只有哥哥嫂子。往常回去,母亲还在,北京到底还是我的家,我敢翻抽屉,敢做一切家里人能做的事情,可如今再回去,我还敢翻抽屉,能翻抽屉吗?我的心里悲凉极了,沮丧极了。是芩姐拉着我走出了那段最阴暗的日子。那时她几乎一个星期就来一封信,信中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唯独在有意识地回避着母亲去世的话题。其间她曾两次来汉中看我,每当他们单位有人来出差,一定会让他们来看看我。在我享受第一个法定探亲假时,那种悲凉几乎将我压倒,我不知道回去再探谁,母亲永远不在了,家的感觉永远没有了。探亲的第一站我到了西安,那一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西安下着少有的鹅毛大雪,当我披着满身的积雪出现在她面前时,我看到她的眼睛湿润了,说了句这么大的雪,快进来,我给你扫扫。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按捺不住,谎称要去卫生间,躲在里面一边洗脸,一边让不争气的眼泪痛快地流个够。短短几句非常普通的家常话,我又找到了家的感觉,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手足情深,这是一种永远割不断的亲情。人是需要相互搀扶、相互支撑的,亲人之间更是如此。
芩姐给家人的印象是一个倔强、刚强,甚至有点挑剔的人,有时还时不常爱调侃几句,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从她的嘴里极少说出充满柔情的话语。她的女儿,说话敢跟爸爸故意耍大舌头,却从不敢趴在她身上撒娇。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充满爱心的人。她似乎不愿意把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展示给众人,但是我感觉到了,从她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得到。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外地调进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由于彼此都在忙于工作、学习、生活及教育子女,我们的联系似乎比过去少多了,但是我每次收到芩姐的信,总是有新的信息:先是她在1983年彻底改了行,调进了《陕西工人报》任副刊部主任、记者;1990年随姐夫去日本,在此期间,她在日本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1995年她回西安后调进了西安市文联。这些年来,芩姐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走着。
1994年,芩姐的第一篇将笔端伸向家族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发表,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家族小说《祖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谁翻乐府凄凉曲》等相继而出,直至长篇小说《采桑子》的出版。那种对家、对人生的复杂情感,那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异史,那种时代风云与家事感情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绪,让我熟悉,也让我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