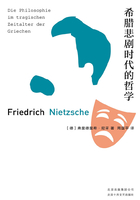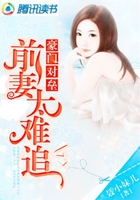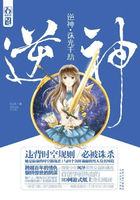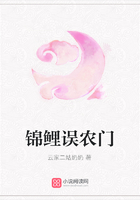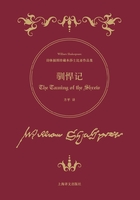陈晓平
一 引言
九十多年前(1921),二十六岁的冯友兰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杜威先生),在系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以下省略副标题),此文于次年正式发表于美国的《国际伦理学杂志》。[40]重读此文,其论证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仍然令笔者受益良多,赞叹不已。这篇文章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使人不禁想起闻名遐迩的“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该问题是由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195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中正式表述的,以后又不断地重申这一问题。
“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大量资料表明,类似的问题和讨论早已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李约瑟不过是以中国科技史的西方专家这一独特身份重提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关于该问题早已有之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爱因斯坦在李约瑟正式表述此问题之前就讨论了此问题,并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约瑟后来得知后给予反驳。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李约瑟正式提出此问题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资料表明,李约瑟读过冯友兰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诱因之一。[41]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赋予一定的新的含义。其新在哪里,是对还是错?“李约瑟问题”和先前的类似问题之间是何关系?这是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将在一定意义上保留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并比较任鸿隽、爱因斯坦、冯友兰和李约瑟本人对此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特别是对冯友兰的解答给予关注。笔者注意到,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之间的关系。例如,范岱年先生早在1997年就谈道:“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李约瑟的解答。……而1922年冯友兰的论文的思路倒是和韦伯一致的。”[42]
笔者以为,范岱年先生把“李约瑟问题”与韦伯和冯友兰的进路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可以说是独具慧眼,言简意赅。韦伯把近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而冯友兰则把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理性主义的精神,确切地说,缺少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并且冯友兰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缺少逻辑理性的深层原因。本文将对冯友兰的有关理论给以简要的评介。
二“任鸿隽问题”与“李约瑟问题”
根据范岱年先生的研究,[43]类似于“李约瑟问题”的问题早在五四前后就被中国的学者明确地提出并加以系统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他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蔽之曰,未得科学之研究方法而已。”[44]何为科学方法,对此,任鸿隽答说:“一曰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一曰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为用也。”[45]
我们知道,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逻辑学的两大分支,因此,任鸿隽对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回答可以归结为“无逻辑”或“逻辑太弱”。任鸿隽在论述中更为强调归纳法,可能是因为归纳法在近代科学中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此外,任鸿隽注意到“科学”一词的歧义性,因而在文章伊始便加以澄清。他说道:
科学者,知识而有系统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者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取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特此以与吾国古来之学术相较,而科学之有无可得而言。[46]
在这里,任鸿隽把科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凡是具有分门别类的特征的知识均属广义的科学,但是,只有那些“推理重实验”“察物有条贯”亦即由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组织起来的有系统的知识才属于狭义的科学。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只是就狭义科学而言的。
笔者以为,任鸿隽关于“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于“广义科学”的定义失之过宽,但对“狭义科学”的定义基本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对科学的理解是吻合的。以下将表明,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讨论“李约瑟问题”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混淆起来,从而使得相关争论长期陷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局面。
李约瑟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李约瑟问题”的: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47]
简言之,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但在近代中国却落后于西方呢?请注意,李约瑟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任鸿隽所说的“狭义科学”,而接近于“广义科学”,因为他把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或技术都叫作“科学”。不过,当李约瑟把古代中国的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或技术看作科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而这一弱点恰恰是任鸿隽不把它们看作“狭义科学”的原因。由此看来,只要把“科学”这个术语界定清楚,“李约瑟问题”是可以同“任鸿隽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狭义的)科学?”相容的。然而,李约瑟却对“任鸿隽问题”大为不满,他的这种不满是在冯友兰和爱因斯坦提出类似问题之后明确表达出来的。这表明,李约瑟把“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混为一谈了。
三“李约瑟问题”辨析
七年之后,李约瑟在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48]的演讲中,以有所不同的方式对“李约瑟问题”作了如下表述:
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时代悠然出于西方呢?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问题了,许多人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做出回答者却寥寥无几。然而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呢?[49]
我们注意到,李约瑟在这里已经将其原先的问题弱化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作出明确的区分,把后者与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开来,仅仅称之为“关于自然的知识”。第二,给出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别特征,即前者是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和对应用技术的推论,而后者是直接应用于有用目的的经验性知识。前两点意味着,第三,这两个问题是相对独立的,既然二者是关于两个不同对象的:一个是问基于数学和推论的近代科学为什么出现于西方而未出现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另一个是问基于实用目的和直接经验的应用技术为什么在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领先于西方。当把原先的“李约瑟问题”加以如此解析之后,其思路更为清晰了,不过其震撼力却随之减弱了。
前面谈到,任鸿隽已经区分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区别在于知识是否建立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之上;若是,则属狭义科学,亦即近代科学;若不必是,则属于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包括近代科学和一切分门别类的知识。不难看出,这一划分大致对应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分,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的特征即假设的数学化和对技术的推论分别相当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二者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并且这两个部分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与之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却使人感到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即科学。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这同一个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无解之谜,因为它近乎一个逻辑矛盾,即:甲既是A又不是A。我们不妨把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叫作“强李约瑟问题”,而“强李约瑟问题”不仅是无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
前面指出,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是弱化了的,因为它使前后两部分涉及不同的对象,即古代中国处于先进地位的是技术,而近代中国处于落后地位的是科学,把这两部分放到一起几乎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至少没有大的理解上的困难。这样表述的“李约瑟问题”是从两个并行不悖的事实中引申出来的,因而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即:(1)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2)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这第二个问题正是“任鸿隽问题”,它是基于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事实提出来的,即追问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这个事实得以出现的原因。与之不同,第一个问题所赖以产生的那个事实——即古代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在李约瑟之前并没有得到公认,至少其公认的程度是不高的,正是通过李约瑟的卓越工作才使之逐渐得到高度的公认。在笔者看来,李约瑟的主要功绩就在这里。相应地,由此事实引申出来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在技术上能够领先于西方?”才是名副其实的“李约瑟问题”。为了同上述无解的“强李约瑟问题”相区别,我们不妨称之为“弱李约瑟问题”。把上述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复合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由于“任鸿隽问题”和“弱李约瑟问题”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须指出,李约瑟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将强的和弱的两个不同的“李约瑟问题”区别开来,而是处于一种若分若合的状态。事实上,他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尽管开始时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表述“李约瑟问题”,然而他在随后的一些论述中又把古代技术与近代科学融合起来,统称为“科学”。这样一来,李约瑟就不知不觉地回到“强李约瑟问题”上。可以说,李约瑟始终在强的和弱的两种不同的“李约瑟问题”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是在爱因斯坦和冯友兰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或解答相关问题的时候,李约瑟对之持以批评的态度。
四“任鸿隽—李约瑟问题”的特殊意义
爱因斯坦曾经谈道:“一切理论的崇高目标,就在于使这些不能简化的元素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50]不妨把这两条原则称为“逻辑简单性原则”和“经验丰富性原则”。逻辑简单性原则是对应于一个科学理论系统的演绎推理而言的,即要求用以推演的公理或基本概念尽可能地少。经验丰富性原则是对应于一个科学理论系统的归纳推理而言的,即要求该理论经受经验验证的内容尽可能地多,而经验验证的过程属于归纳推理的过程。对于一个科学理论系统而言,其基于演绎推理的逻辑简单性往往体现于它的数学化,其基于归纳推理的经验丰富性往往体现于它所经受的实验检验;因此,数学化和实验性成为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
由此看来,当年任鸿隽把经由演绎法和归纳法建立或组织的系统性知识作为狭义科学的区别特征是正确的,他据此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其答案就是中国没有应用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逻辑传统。我们在前面虽然消解了“强李约瑟问题”,但却保留了“弱李约瑟问题”,进而提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从表面上看,这后一问题是“任鸿隽问题”和“弱李约瑟问题”的简单组合,并不比分别表述这两个问题增加什么含义,其实并不尽然。前面谈到,在区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的基础上可以用两种等价的方式表述“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其中一种是:“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这个表述中,“弱李约瑟问题”是前一半,“任鸿隽问题”是后一半,并且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对象都包含“科学”这个词,这样,这两个问题就不再是完全彼此独立的了。须强调,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按照任鸿隽的定义,凡分门别类的知识都属于广义科学,只有那些经由演绎法和归纳法组建的知识系统才属于狭义科学。笔者基本接受这个“狭义科学”的定义,但要对这个“广义科学”的定义加以修正,即把“分门别类的知识”改为“包含公共经验技术的知识”。通过这个修正,我们可以把那些与公共经验技术无关的学科排除在广义科学之外,如哲学、宗教等,但把服务于实用目的的经验技术包含于广义科学,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这样,古代中国的技术和近代科学同属广义科学,进而使得古代中国技术领先而近代科学落后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包含着对实验机制的设计和操作的技术,这使得现代科学与经验技术密切地关联起来,其中包括古代中国发明的技术。正如陈方正指出的:“实验科学背后的原动力,最少有相当部分是极可能也和东方传来的礼物亦即‘技术性’外部因素有关,那就是火药和火炮的广泛应用。毫无疑问,它大大地刺激了弹道学和抛物体研究。”[51]这时问题便出现了:为什么古代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未能刺激中国的弹道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陈方正和余英时的回答应该是:古代中国缺乏系统的数学思维的传统,尽管他们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任鸿隽的回答应该是:古代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包括体现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体现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相比之下,后一种回答更为准确和全面。无独有偶,爱因斯坦和冯友兰也给出类似的回答。
需要指出,李约瑟有时也从“强李约瑟问题”合理地退到“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上来。例如,他曾谈道:“对于泛希腊主义者力求保留欧洲的独一无二地位的企图来说,最大障碍就是希腊人实际上不是实验家这个事实。受控实验肯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发现,但尚未有人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此之前有某个西方民族就已完全理解了这种实验。我也并不是要声称这项荣誉属于中古时代的中国人,但他们在理论上相当接近于这一点,而在实践上则往往走在欧洲成就的前头。”[52]
在这里,李约瑟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科学的区别特征是实验方法,具体地说是可控实验。其二,把古代中国的先进技术与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李约瑟此时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强李约瑟问题”,而是包含了“弱李约瑟问题”的“任鸿隽—李约瑟问题”。
美国学者托比·胡佛(Toby E. Huff)在评论“李约瑟问题”时也间接地谈到这一点。他说:“技术本身和科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联系,假使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领先的技术没有催生出近代科学,反而在16世纪后开始停滞不前呢?”[53]看来,“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实际上被广泛地关注着,包括主张完全消解“李约瑟问题”的陈方正在内。
五 爱因斯坦命题与“李约瑟问题”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54]
译者许良英先生特别指出:“最后一句所说的‘这些发现’,显然是指开头所说的西方科学两大成就: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古希腊);发现通过系统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55]笔者接受这种解释,并对最后一句在修辞上(不是在意思上)略作修改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毕竟都被做出来了。”[56]
爱因斯坦这封信传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科学发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此方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一是体现于古希腊《几何原本》中的形式逻辑即演绎逻辑,二是应用于文艺复兴时期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即归纳逻辑。这与本文在前面所说的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学化和实验性是一致的。其二,这两个方法论发现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其三,中国人没有做出这两个发现不足为奇,而西方人做出这两个发现倒是令人惊奇的。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是陈述了两个客观事实,只有第三点表达一种主观态度,即:用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用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正因为此,中国人没有发现它们是不足为奇的。
爱因斯坦的这种主观态度蕴涵着两个更深的问题,即:(1)为什么西方人可以发现这两种令人惊奇的方法?(2)为什么中国人发现不了它们?表面上看,爱因斯坦的问题只包含前一个而不包含后一个,因为他对中国人没有发现这两种方法并不感到奇怪。但是,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由第一个问题必然会引出第二个问题。对此我们只需对爱因斯坦的那封信略作引申便可看出。
爱因斯坦关于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说法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即:中国人没有发现那两种逻辑方法是很自然的,而西方人毕竟发现了那两种方法倒是不自然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顺从自然而未发现这两种方法,而西方人对抗自然却发现了这两种方法?就笔者所知,冯友兰先生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文章中正是深入到这个层面来探讨问题的,并给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答案。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加之提出的时间早于“李约瑟问题”,不妨称之为“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之。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前面所说的“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并且对之加以深化。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是,当李约瑟看到爱因斯坦这封信之后给以强烈的反驳。他说:“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硬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价的,并有必要简单说明这是为什么。”[57]
尽管李约瑟的口气有些激烈,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对爱因斯坦的争论是学术性的,因为整个文章都是用已有的或他所发现的资料或证据来论证他的观点,即中国有科学并且比西方还要早。不过,需要指出,李约瑟在同爱因斯坦的争论中不知不觉地把“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混为一谈了。他所要论证的“中国早已有科学”是从“广义科学”方面讲的,即凡包含公共技术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但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中国没有科学”是从“狭义科学”方面讲的,即经由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因此可以说,尽管李约瑟对中国拥有广义科学给出颇具说服力的论证,但却构不成对爱因斯坦的“中国没有(狭义)科学”之命题的反驳。
爱因斯坦的这一命题其实也是冯友兰的命题。正因为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李约瑟和冯友兰之间。余英时先生回忆说:“1975年,我和他(李约瑟——引者注)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58]然而,冯友兰的问题并不错,因为他所说的“科学”就是基于逻辑方法的现代科学,只是李约瑟误解了他,正如李约瑟误解爱因斯坦一样。
还须指出,爱因斯坦对中西科学比较的关心是独立于所谓的“李约瑟问题”的,因为爱因斯坦的那封信是在“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的前一年发出的。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没有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常讨论的一个题目。对此,许良英先生的以下回忆是一个印证。
“所谓‘李约瑟难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我在大学三年级(1941)时就组织同学讨论过,并已得到解决。那时李约瑟还未到过中国,也还没有这个‘难题’的影子。1944~1946年间,浙大两位教授陈立、钱宝琮和校长竺可桢相继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专门论文。”[59]
许良英提到的这几位学者在1944~1946年间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讨论都与任鸿隽创立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有关,包括李约瑟本人在这期间发表的有关文章也是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60]可见,与其把这个问题冠以“李约瑟”的名字,不如冠以“任鸿隽”的名字。
爱因斯坦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受到“李约瑟问题”的影响。至于爱因斯坦是否受到“任鸿隽问题”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他没有直接受其影响,因为他不懂中文。然而,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冯友兰的影响。这不仅因为爱因斯坦的观点与冯友兰的观点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因为冯友兰提出问题的那篇英文文章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发表了,其《中国哲学史》上卷和下卷的英译本分别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其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发表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后两本书至少在爱因斯坦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还是唯一用英文表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国家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教材或参考书。
事实上,李约瑟本人曾经受到冯友兰上述著作的影响,“李约瑟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早已包含在“冯友兰问题”之中。我想,这也许是冯友兰未曾关注“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之一吧。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的关系。
六 冯友兰对问题的解答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对中西科学的比较最终会导致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因此,李约瑟与冯友兰关于中国有无现代科学的分歧最终归结为中国有无现代哲学的分歧。事实上,冯友兰对于“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回答是着眼于哲学层面的,因而显得比较彻底。
李约瑟曾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评论说:“冯著第二卷中关于新儒家的某些论述特别给人以白玉微瑕的感觉。在我看来,我们绝不可以说中国哲学直到20世纪初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事实上,朱熹和其他新儒固然是11世纪、12世纪的哲学家,但为了同当时的佛教宇宙观相对抗,他们与道家共同阐发的有机自然主义已极具现代气息,其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合拍之处,比冯友兰认识到的要多得多。”[61]
我们看到,李约瑟和冯友兰的分歧从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上升到中国有没有现代哲学的问题。的确,在冯友兰看来直到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现代哲学,对此李约瑟明确表示反对。笔者认为,这里同样有一个澄清概念的问题,即何为“现代哲学”。在李约瑟看来,只要中国哲学中具有较多的与现代科学合拍的观点就可称为“现代哲学”。然而,冯友兰不是这样看的,而是把哲学研究的方法看作现代哲学和古代哲学的分水岭。具体地说,现代哲学必须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尽管逻辑分析的方法不是全部。冯友兰承认并引以为豪的是中国先哲们在其观点上的深邃性,同时指出其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使之具有系统性。
冯友兰把西方现代哲学中特有的逻辑方法比作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他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62]
由此可见,李约瑟通过指出中国宋明理学和道家的有机自然观与现代科学比较合拍,以此来反驳冯友兰否认它们是现代哲学的论证是不成立的,正如他用古代中国拥有广义科学来反驳爱因斯坦关于古代中国没有狭义科学的论证。对于冯友兰的上述说法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哲学缺少逻辑分析的方法?这个问题与“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爱因斯坦命题中所蕴涵的问题。
我们在前一节将爱因斯坦的问题重新表述为:为什么中国人顺从自然而未发现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西方人对抗自然却发现了这两种方法?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以及其后的哲学论著中给出相当清晰的回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思维方法的倾向性归结为追求幸福的倾向性,又把追求幸福的不同倾向归结为不同的生存环境。
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指出,在中国周末的哲学中有三派:道家是自然派,是向内心世界追求幸福的;墨家是人为派,是向外部世界追求幸福的;儒家是中间派,不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倾向于自然派,因而倾向于向内追求幸福。这三派之间的激烈论战是以墨家的失败而告终的,致使向内寻求幸福的自然派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中国长期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中国人顺从自然而没有发现逻辑方法的原因。
冯友兰谈道:“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顺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中国思想中这条‘人为’路线,不幸被它的对手战胜了,也或许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63]
冯友兰在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回答“为什么西方拥有科学?”他谈道:“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我所说的‘人为’路线。……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不过把上帝换成‘自然’,把创世换成机械,如此而已。……他们首先力求认识它,对它熟悉了以后,就力求征服它。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64]这样,他便回答了“为什么西方人对抗自然却发现了逻辑方法”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追求幸福的倾向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对此,冯友兰的回答是他们生存的地理环境是不同的:一个是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另一个是海洋国家,以商业为主。经济基础的不同又决定了二者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他后来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论述:
农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65]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Filmer S. C. Northrop)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66]
至此,冯友兰便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认识论或思维方式上有如此大的差别,即一个长于直观或直觉,另一长于逻辑或数学;进而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而西方拥有科学的问题。不过,冯友兰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探询中西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末尾谈道:“西方是向外的,东方是向内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不过他紧接着预测道:“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67]
如果说在那篇文章中冯友兰只是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在他以后所建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中便对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并且进一步深入到方法论的中西结合问题上。
冯友兰把借助逻辑清楚地谈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叫作“正方法”,而说它不是什么甚至不说它则是“负方法”。他说:“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68]
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这是冯友兰一贯的态度。笔者对此极为认同。哲学尚且如此,科学何尝不是?事实上,李约瑟已经从冯友兰的书中读出某些真义。
李约瑟说道:“如果认真推敲冯著的字字句句及字里行间的话,中国人的永恒哲学从来不是机械论和神学,而是有机论和辩证法。”[69]他问道:“在现代科学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和被全世界普遍接受之时,是何种思想伴之而行呢?”他相信是有机自然主义,“西方的有机自然主义之花曾得到中国哲学的直接滋润”。而且“冯友兰和布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引者注)的工作加快了对中国哲学的再评价及东西方相互理解的进程”。[70]
李约瑟不仅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还对之作了高度的评价:“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尽管本书的研究方法只是诸多方法之一种,采用的材料也大多为其他中国思想史家所经常采用,但在众多的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中,冯著的确堪称翘楚之作。”[71]
七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李约瑟问题”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加以分析,把不同层次、不同意义的问题从中分解出来,然后分别对待之。对于“强李约瑟问题”笔者主张将其消解掉。[72]对于“弱李约瑟问题”和“任鸿隽问题”则应加以保留。特别是在“广义科学”的意义上把这后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而形成“任鸿隽—李约瑟问题”,这对于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凡是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深刻讨论都不可避免地把“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作为焦点之一,尽管这个术语并未出现。曾记否,开启中国现代化征程的五四运动不就是打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吗?
可以说,回答“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已经成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事实上,任鸿隽等人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就是五四运动的先声,他在其创刊号上提出并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也可看作五四运动的“先问”。在五四运动两年之后,年青的冯友兰便在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坛上再次提出并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并且将这一问题赋予更深刻的内涵,对它的讨论和回答贯穿于他以后的全部哲学思考和哲学活动之中。因为这一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焦点之一,而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则是冯友兰始终不渝地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
冯友兰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提问和解答比任鸿隽更为深刻,因为后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只限于认识论或方法论层面,而前者的论述不仅包含认识论或方法论,而且直达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人生倾向,进而达到地理环境论。笔者以为,冯友兰的这一进路是深刻的和彻底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围绕有关问题的“外史论”和“内史论”的关系略作分析。
简单地说,外史论着重于从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综合地回答问题,而内史论则着重于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方面回答问题。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著作给出内史论的解答,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外史论的解答。对于“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任鸿隽和冯友兰等人的回答主要是内史论的,而李约瑟和他以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回答则主要是外史论的。[73]
在笔者看来,外史论的最大问题是不彻底。以李约瑟的回答为例,他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主要地归结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官僚制度。那么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长期存在封建官僚制度?对此,李约瑟则语焉不详。[74]与之不同,冯友兰首先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其回答是:中国人主要是顺从自然因而向内心世界寻求幸福的,而不是对抗自然因而向外部世界寻求幸福的;相应地,中国人的思维优势在于直观的内省,其目的在于修身养性,而不是以理解外部世界进而征服外部世界为目的的逻辑思维。为什么中国人主要是向内心世界寻求幸福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求幸福?其回答是: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大陆性的,长期以来主要以农业为经济主体:农民主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培养了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需求,而这种精神需求只有在内心世界里可以实现;与此同时,建立了一种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家族制度及其伦理即儒家伦理。与此相反,根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其海洋性地理环境决定的。
我们看到,冯友兰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回答最终落到中国人的地理环境即大陆国家。笔者以为这是合理的,但这却不是外史论的,而是内史论的;内史论不是绝对不谈外部因素,而是不着重谈论外部因素。冯友兰在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着重谈的是中国人顺从自然的价值倾向和重直觉而轻逻辑的思维倾向。与之不同,外史论则着重在中国的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等外部因素中寻找答案,而少谈甚至不谈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倾向和思维倾向。冯友兰把答案最终归结为中国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其必要性在于回答得彻底。如果有人继续追问“为什么中国人生存于大陆性的地理环境?”对此我们无言以对,如果硬要说什么的话,那只能说“碰巧”,或者借用存在主义的话:中国人是别无选择地被抛在那里的。
冯友兰不仅对问题回答得比较彻底,而且对问题提出得比较准确。其实他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包含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任鸿隽—李约瑟问题”。冯友兰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75]后来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谈道:“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76]
显然,冯友兰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对古代中国的哲学和技术的充分肯定。与之相比,李约瑟只是在30年之后从科技史的角度更为充分地证实了冯友兰的这些说法,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尖锐。鉴于这一历史事实,加之冯友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深刻性与后来爱因斯坦的说法更为接近,笔者认为,在“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
(原文刊载于《中国学术论坛(网络论坛)》,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