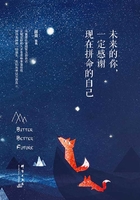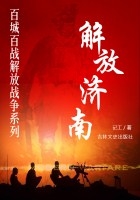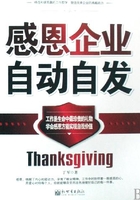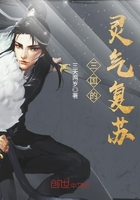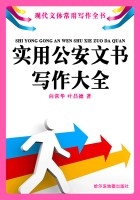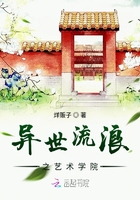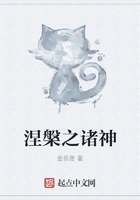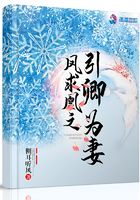我这里不是要给爱伦·坡一个公正的评价;也不是要确定他在诗人中的地位,或是指明他最重要的独创性。对于要做出判断的评论家来说,爱伦·坡确实是一块绊脚石。如果对他的作品详加考察,我们会发现似乎其中只有失之草率的写作,缺乏广泛涉猎或深厚学养支撑的幼稚想法和对各类创作体裁杂乱无章的尝试,大多迫于经济上的贫困,无法对细节精益求精。这种说法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如果不是分析地看待他的作品,而是放眼观其全貌,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和令人钦佩的规模,这些东西会让人不时回眸翻看。爱伦·坡的影响同样令人困惑。他的诗歌和诗歌理论在法国影响巨大,而在英美好像几乎微不足道。我们能证明哪位诗人的风格像是成形于对爱伦·坡作品的研读吗?唯一一个马上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名字就是——爱德华·李尔[44]。可是谁也不能确信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过爱伦·坡的影响。我可以明确地列出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影响过我;我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我确信对我没有影响;可能还有一些,他们的影响我尚未觉察,但是经提醒便会恍然大悟。然而就爱伦·坡而言,我永远无法确信。他的诗作非常少,那为数不多的诗中只有五六首获得巨大成功,但就是那为数不多的诗作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看到的任何一首诗,同样在广大的读者中享有盛名,同样被大家所熟记。此外,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对作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是在其他创作体裁方面,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我这里不是要对其不可思议之处做出解释,这顶多算是对爱伦·坡的影响的研究;从他的影响方面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个阐述,是对爱伦·坡的重要性的原因的阐述,尽管这可能有失偏颇。我通过三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尤其是保罗·瓦莱里的眼睛,尽量接近地对爱伦·坡作一会儿观察。上面这一排序很重要,因为这三位法国诗人分别代表了诗歌中某种传统的早期、中期和晚期。马拉美曾经告诉我的一个朋友,他来巴黎是因为他想要结识波德莱尔,还说他有一次在码头的一个书报亭见到波德莱尔,可是当时却没有勇气上前打招呼。关于瓦莱里,从他还不过是个大男孩时写给马拉美的第一封信中,我们知道他一直追随这位前辈诗人,我们还知道他对马拉美的热衷一直持续到后者过世。这是三代文学巨匠,他们代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法国诗歌。当然,这是相互迥异的三位诗人,当然,波德莱尔在文学上的追随者数量众多,声名显赫,而且还别有门派旁出。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三位诗人,我们可以追溯某种特殊的诗歌本质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这种理论更多来自爱伦·坡的理论学说,甚至胜过来自他的实践创作。爱伦·坡的影响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事实上马拉美,接下来是瓦莱里,不仅通过波德莱尔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他们每个人都亲身受到那种影响),而且他们还对爱伦·坡本人的理论学说和创作实践中的价值给出了有力的证明。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乐于相信,我们比任何外国人更了解我们自己的诗人;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准备接受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法国人从爱伦·坡身上看到了一些被英语读者忽视的东西。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不单单是爱伦·坡,而是他对这三位法国诗人的影响,这三位诗人代表了前后三代人;我的目的还在于对诗歌所持的独特观点,也就是这三位诗人所持的观点作进一步了解,这种观点可能是那个时代所取得的最有趣、最富有特色、当然也最具独创性的诗歌美学的成就。正如我倾向于相信的那样,如果这种对于诗歌的观点代表着一个随着瓦莱里的过世而终结的时代,那么这种观点就更值得考察。因为不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发现是什么取代了这一观点,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研究都会有助于他们的理解。
在研究这几位法国诗人眼中的爱伦·坡之前,我想还得就我自己的印象,谈谈他在英美读者和批评家眼中的地位;因为,如果我错了,你们可能就会用我想法上的错误来批评我说的关于他在法国的影响。爱伦·坡曾被看作浪漫主义运动中次要的或是二流水平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小说上,他是所谓“哥特式”小说家的继承人,而诗歌上,他是拜伦和雪莱的追随者。可是,这种说法是把他放在英国传统中,而那里无疑并不是他的归属。英国读者又把爱伦·坡作品中游离于英国传统之外的东西说成美国的东西,可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我们考察了他同代以及前一代的其他美国作家之后更是如此。他的作品中有某种乡土的地方风情,而这种意义上的乡土气息,惠特曼则是一点儿也没有。这是一个既不属于自己的家乡又无处可去的人的乡土特点。爱伦·坡有点儿像个流落异国的欧洲人,他为巴黎所吸引,为意大利和西班牙所吸引,为那些他认为有着浪漫的忧郁和辉煌的地方所吸引。虽然他活动范围南北方向不超过里士满和波士顿,东西方向也不超过这几个中心城市,但是他却像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者。这样名声显赫的作家很少有从自己的根基中获取得这么少的,很少有这样脱离自己的周围事物的。
我相信一位有修养的普通英国或美国读者对爱伦·坡的看法是这样的:爱伦·坡是一位写了为数不多的几首短诗的作家,而这几首短诗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就令他着迷了一段时间,并且不知怎么竟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我想如果不是在一本诗集中翻阅到它们,他是不会重读这些诗歌的,这些诗歌给他的乐趣,倒像一种可以让他片刻重温的愉快回忆。在他看来,这些诗歌属于一个特定时期,那时他对诗歌的兴趣刚刚觉醒。某些意象,更多的是某些韵律留在了他记忆之中。这位读者还会记得爱伦·坡的某些故事——不是很多——并认为虽然《金甲虫》在那个时代极为盛行,但此后侦探小说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他有时或许会将爱伦·坡与惠特曼进行比较,经常重读惠特曼,而不是爱伦·坡。
至于散文小说,人们认为爱伦·坡的故事对某些类型的通俗小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就侦探小说而言,几乎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两位作家:爱伦·坡和威尔基·柯林斯。虽然两者的影响力有时并行不悖,但是也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侦探形象。干练高效的职业警察出自柯林斯,精明古怪的业余侦探则来自爱伦·坡。柯南·道尔得益于爱伦·坡之处甚多,不仅仅是得益于《摩格街谋杀案》中的侦探杜宾。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他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是在托特纳姆宫廷路上的一家旧货店里花几个先令买来的,他是在哄骗华生。他是在厄舍府[45]的废墟中找到那把小提琴的。福尔摩斯和罗德里克·厄舍的音乐练习之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那些混乱无序的即兴演奏虽然有一次将华生送入了梦乡,但是肯定会让任何受过音乐训练的人痛苦不堪。我认为赖德·哈格德[46]那些奇异美妙的探险小说极有可能是从爱伦·坡那里获得灵感的——并且哈格德本人也有够多的模仿者。我认为在赫·乔·威尔斯[47]早期的科学探险发明小说中,他得益于爱伦·坡某些故事的启发的地方可能也有很多——比如说《戈登·皮姆》、《大漩涡底余生记》,或者《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我把证据的收集留给那些有兴趣致力于此问题的人。但是恐怕现在极少有读者会翻开《她》、《星际战争》或者《时间机器》,更少有人会为它们的前驱而兴奋不已。
上述几位法国诗人和有着同等权威的英美批评家在看待爱伦·坡的方法上有着普遍的差异,我先是认识到前者看到的是爱伦·坡的“全貌”,是将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英美批评家,我认为更倾向于对作家作品的不同部分各自做出评价。我们把爱伦·坡看作一个涉猎诗歌及各类小说的人,未能静下心来把任何一种文学体裁运用到极致。法国读者对表达形式的多样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发现了,或是自以为发现了一种本质上的统一。尽管必要时他们承认由于贫困、意志薄弱和遭际变迁,爱伦·坡的许多作品缺乏连贯或是应时而作,但他们仍把他当作一位极重要的严肃作家,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他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种批评思想的差异;但是必须说明,我们的观点是来源于对爱伦·坡实际创作中的缺陷和不足的了解。有必要举例说明这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给英语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爱伦·坡对诗歌中的重叠[48]要素有着一种特别罕见的鉴赏力,对这种从本义上可以称作“诗的魔法”的要素极有感觉。他的作诗法不同于最伟大的格律大师的作诗法,不是那种学习或积习而成的作诗法,不是那种一味追求较丰富的韵律,以迎合一生中不时重温他的逐渐成熟的读者的鉴赏力。爱伦·坡的作诗法的效果直接且无延展,对于感情敏锐的学童和睿智文雅之士来说几乎别无二致。在这种不变的直接性中,这种诗体可能更具有几分优秀韵文的特点,而不是诗歌——但是在此,我并不想讨论这个与主题无关引人争议的问题,因为我确信这是“诗歌”而非“韵文”。这种诗体有一种重叠的效果,由于完全未加掩饰,能够激起内心深处几近原始的情感。但是,在爱伦·坡为恰当的声音挑选词语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该词也应该有恰当的意义。我将就爱伦·坡和丁尼生对同一个词的用法做一个比较——丁尼生可能是继弥尔顿之后所有英国诗人中,对音节上的声音有着最为准确和最为挑剔的欣赏力的诗人。在爱伦·坡的《尤娜路姆》一诗中——我认为这是他最成功,也是最典型的诗作之一——我们发现以下诗句:
It was night, in the lonesome October
Of my most immemorial year.
这是我最难追忆的一年,
一个荒凉的十月的夜里。[49]
根据《牛津大词典》的解释,immemorial的意思是:“无法追忆的;古老的;远古的”。这些解释好像都不适合爱伦·坡对该词的用法。那一年并非无法追忆——说话者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年的一件事;结尾处他甚至记得恰好一年前、同一个地方的一场葬礼。丁尼生的诗句,同样有名且令人赞叹,其诗中的声音与作者所希望唤起的声音产生很好的呼应,这首诗可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
The moan of doves in immemorial elms.
古老的榆树林中鸽子的呢喃。
这里immemorial除了有着最恰当的音效,还精准地描绘出树木古老得让人都不知道到底有多老。
诗歌,种类各不相同,可以说有让读者关注声音的诗歌,也有让读者关注意义的诗歌。对于前一种诗歌,其意义的理解几乎未曾让人意识到;对于后一种诗歌——在这两种极端上——恰恰是声音的运用让人不曾察觉。但是不论哪一种,声音和意义都得相互配合;即使在最纯粹的叠句诗歌中,词语的词典意义也不能够被心安理得地忽视掉。
词意上的轻率对爱伦·坡而言是很常见的。我认为,《乌鸦》远非爱伦·坡最好的诗;尽管它最为著名(部分原因是作者在《创作哲学》中对该诗进行了分析)。
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
一只神圣往昔的乌鸦庄重地走进我房间,[50]
由于乌鸦没有什么特别神圣之处,就算这不祥的鸟不是完全地不神圣,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来自一个神圣的时代,即使假定有这样一个时代存在过。我们刚刚听到乌鸦被描述为“庄重的”,但是不久又被告知他是“丑陋的”,这种特性没有得到详细的解释,很难与“庄重”的说法一致。诗中的一些词,插进来好像要么只是为了填充诗行,使之符合规定的音步,要么是为了押韵。乌鸦被称作“不是懦夫”是完全没必要的,只是为了满足与“乌鸦”押韵的迫切需要[51]——这是对押韵的急切需要作出的让步,这种做法,我相信马莱伯[52]一定不能容忍。甚至很少会有这般如同小学生似的辩解:说灯光“凝视”沙发坐垫[53]是奇异的幻想,即使有那么一点合乎逻辑,也会显得牵强。
《乌鸦》中诸如此类的不足——你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创作哲学》,这篇爱伦·坡声称披露了《乌鸦》创作方法的文论,在英美不像在法国那样受人重视。读那篇文论时,我们很难不去想,假如爱伦·坡如此精心地构思他的诗歌,那么他写诗时可能颇费苦心——但是写出来的诗却和创作方法很不相称。因此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过分析自己的诗歌,爱伦·坡要么是在制造一个恶作剧,要么就是写一篇自欺欺人的文章,以记录下他所自认为的创作方法。因此,这篇文论就未得到其应有的重视。
爱伦·坡其他的诗歌美学文论也值得研究。没有哪个诗人在论述自己的“诗艺”时,除了为自己的实践——即他个人类型的诗歌创作,进行解释、辩解、辩护或是做准备之外,还能期望再多做些什么。他也许认为他是在为所有诗歌订立法则,但是他那些值得一说的必说之事,与他自己的或是他想使用的创作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这种方法对于嫡传后学很可能同样有效,并且帮助甚大。我们只有用他写的诗歌来核对他所说的,才能有把握在他的诗歌论著中找出对任何诗歌都适用的原则。关于长诗创作的不可能性,爱伦·坡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因为一首长诗,他认为,充其量只是一系列串联起来的短诗。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那就是爱伦·坡自己未能写过一首长诗。他只能构思出某种具有单一的简单效果的诗歌,对他而言,整首诗必须保持一种情绪。然而,只有在一首相当长的诗中,多种情绪才能得到表达。因为多种情绪需要多种不同的主旨或主题,它们要么自身相互联系,要么在诗人的心中相互联系。这些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且大于各部分之和,我们从阅读这样一个整体的各部分所获得的愉悦,会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而得到增强。由此,在长诗中,一些部分可能会被故意设计得比其他部分缺少“诗性”。这些诗段,假如单独选取出来可能会黯然无光,但相对照而言,可能会引出其他部分的重要意义,并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比任何部分都更具意义的整体。艺术激情尽可能广泛的变化可以使长诗增色。但是爱伦·坡却想让最初的艺术激情贯穿全诗,这实在令人怀疑他是否欣赏过但丁《炼狱篇》中更富哲理的篇章。结果爱伦·坡说过的话成了昔时同样未能写出长诗的其他诗人的莫大慰藉,并且我们必须承认创作长诗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实力和持久力的问题,还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爱伦·坡在这个话题上的论述很有启发性,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认为长诗创作是不可能的诗人的观点。
事实上,爱伦·坡认为诗歌必须是单一情绪的表达—若要在此证明《钟》,这首有意尝试多种情绪的习作,其实像爱伦·坡所有的诗歌一样只有一种情绪,就会变得太过离题—最好把这个事实理解为一个更根本的弱点的表现。在此,我只是试探性地提出我的说法,但这是一个我提出来想看看会有什么结果的观点。我的说法也许还能解释为什么有很多读者在他们成长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在他们刚刚度过童年的人生阶段中,会对爱伦·坡的作品感兴趣。爱伦·坡才华出众,这无可否认,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天赋极高、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的才华。他强烈好奇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只是那些懵懂孩童的心中乐事:自然、力学和超自然的奇迹,密文和暗号,谜语和迷宫,机械操作棋手以及迸发出的各种奇思妙想。他好奇心的多样性和强烈感令人快乐,叫人惊叹;可他趣味上的怪异离奇和杂乱无章最后却令人疲倦。他所缺乏的正是那种赋予成人庄重感的始终如一的人生观。某种态度可以是成熟并且始终如一的,也可以是让人极度怀疑的,但爱伦·坡不是怀疑论者。他似乎完全听任瞬间的想法,结果他所有的想法看起来不像是要让人相信的,而像是拿来消遣的。他缺少的不是智能,而是心智的成熟,这种成熟只有随着人整体上的成熟、各种情感的发展和协调才能获得。对于任何心理学或病理学上的可能性的解释我都不感兴趣。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那就是发现爱伦·坡的作品正是那种我可以期望从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才智和感情的人那里得到的,发现此人的情感发展在某一方面仍停留在年少时期。他最生动的想象力的实现都只是一个梦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他诗中和故事中的少女总是已故的,或是还未得入怀便已消逝了的。即使在《闹鬼的宫殿》这首主题似乎是要表现他自己酗酒嗜好的诗中,灾难也不具有道德意义,而是被当作一个孤立现象来冷淡对待,当他说起自己的堕落状况时,诗行背后不像弗朗索瓦·维永[54]的那样有种恐怖的力量。
关于爱伦·坡,我已说了这么多,现在得继续探究在他的作品中,让这三位伟大的法国诗人赞赏钦佩的到底是什么,而这点我们尚未发现。首先,我们得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三位诗人都并非熟谙英语。波德莱尔肯定读过不少英美诗歌,毫无疑问他借鉴过格雷,很明显他也仿效过爱默生。他根本就不熟悉英国,要让人相信他英语说得相当之好也根本不可能。至于马拉美,他教授英语,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只是一知半解。他曾致力于撰写某一英语使用手册。但是仔细查看这篇奇特的论著和他凭着印象列举出的古怪日常谚语,马拉美英语学识渊博的说法便会不攻自破。至于瓦莱里,即使是在英国,我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英语。我也不知道他以我们的母语读过什么:瓦莱里的第二语言是意大利语,在他的某些诗歌中可以看出这一语言的影响。
当读者用一种他不太通晓的语言去阅读作品时,他很有可能发现作品中没有的东西;如果这个读者本身是个天才,这种外国诗歌的阅读或许会在偶然的妙想中,诱发出他心灵深处某种重要的东西,他也将此归功于他所读的文字。事实也是,在把爱伦·坡的小说译成法语时,波德莱尔做了明显的改进。他把随意粗劣的英语变成了令人赞叹的法语。将爱伦·坡的许多诗歌译成法语散文的马拉美也做了类似改进。但另一方面,诗的韵律,也是爱伦·坡独创性中最显著的地方,却丧失了。但因此要证明法国人高估爱伦·坡是由于他们的英语太蹩脚,就完全不对了。我们不可过多揣度,他们并未受到语言劣势所扰,而我们却对此太过在意。这不是他们高度评价爱伦·坡思想的原因,也不是他们重视他哲学和评论方面文章的原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得把眼光放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避免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以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对爱伦·坡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伟大的诗人,各自又大不相同。而且,我已经说过,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三代人。这里,只有瓦莱里才是我主要关注的。因此,关于波德莱尔,我只想说从他写的爱伦·坡故事和文论的译序来看,他最关注的是此人的个性。他描述的准确性我并不关心,关键是在爱伦·坡身上,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茕茕独立和世俗意义的失败中,波德莱尔发现了le poète maudit[55]的原型,即诗人是社会的弃儿——正是这种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在魏尔伦和兰波身上变成了现实,正是在这种类型中波德莱尔视自己为一个杰出的典范。这种十九世纪的范型,le poète maudit,社会和中产阶级道德观的反抗者(当然是源自欧洲大陆拜伦式神话的反抗者)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符的。但波德莱尔在撰写一篇主要概述爱伦·坡这个人及其生平的序言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引出了瓦莱里的美学观:
他认为(波德莱尔说道),他是个真真正正的诗人,诗歌目的及其准则一样有着相同的性质,诗歌除了其本身应当什么都不考虑。
“诗不在说理——它本身就是理。”这一信条近来已得到了认同。
马拉美的兴趣则是在诗歌技巧上,尽管他认识到爱伦·坡的诗歌技巧是一种法语无法借鉴的作诗法。但说到瓦莱里,吸引他注意的既不是爱伦·坡这个人,也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诗歌理论。很早以前,当瓦莱里还年纪轻轻时,他曾给马拉美写过一封信,向这位前辈诗人介绍自己,信中说:“我珍视爱伦·坡的理论,它那么深邃,潜藏着那么多广博的学识;我信仰韵律全能,尤其是暗示性短语的韵律。”但是,我的观点并不是主要根据这个年轻后生的信条,而是根据瓦莱里后来的理论和实践。正如瓦莱里的诗歌和他诗艺方面的文章,是他思想上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同样地,对于瓦莱里来说,爱伦·坡的诗歌和理论是不可分割的。
这又让我思考起la poésie pure[56]这个术语的意思:这个法文短语内涵丰富,引人讨论与争议,并不能完全译为“纯粹的诗歌”。
可以说所有的诗歌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他人、神明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情感经历。因此,诗歌也与思想和行动有关,它们源于情感,又孕育着情感。但是,不论人类所处的表达和欣赏阶段是多么的原始,诗歌的功能绝不是要简单地唤起听者心中相同的情感。诸位应该记得德莱顿著名颂诗[57]中对亚历山大的盛宴的描述。据说吟游诗人提谟修斯[58]乐技高超,变化多端,唤起了这位亚洲征服者心中的强烈情感。若说他真是因此而变得激动万分,莫如说那时的亚历山大大帝正因酒精中毒遭受着自动症的折磨,根本就不可能欣赏音乐或诗歌艺术。在最早的诗歌中,或是在最初的诗歌乐趣中,听者关注的是诗歌主题。他能感受到诗歌技巧的效果,但还未完全意识到这种技巧。随着语言意识的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听者,那时或许已变成了读者,意识到了故事本身及其叙述方法的双重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开始意识到了文体风格。接着我们便颇有兴致地区分起不同诗人处理相同主题的方法的异同,这不仅仅是优劣的鉴别,还是各种同样令人赞叹的风格间差异的欣赏。在发展的第三阶段,主题退居幕后,它不再是诗歌的目的,只是实现诗歌的必要手段。在这一阶段上,读者或是听者对主题变得漠不关心,几乎如同初期听者对风格漠不关心一样。这种毫无意识和漠不关心,无论是开始对风格的,还是后来对主题的,都会完全使我们脱离诗歌。只注重主题而完全忽视其他,对听者来说意味着诗歌还未出现;只注重风格而完全忽视其他,则意味着诗歌已经消逝。
这种自我意识的增强过程——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语言意识的增强过程——有着我们称之为“纯诗”的理论目标。我相信这将是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我认为诗仅仅是诗,只要它在下面意义中保存一些“不纯”,就是说,只要其主题本身受到重视。布雷蒙神父[59],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坚信尽管“纯诗”要素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必要因素,但是诗歌不可能完全由“纯诗”组成。然而瓦莱里的出现使我们对诗歌主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们必须谨小慎微,避免说出主题变得“不那么重要”。它反倒是有着另一种重要性,作为手段它是重要的,但其终极目的是诗歌。主题为诗歌而存在,而不是诗歌为主题而存在。一首诗可以运用几个主题,并以特定的方式将它们连接起来,要询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几个主题组合后所产生的,不是另一个主题,而是诗。
这里我想指出美学学者提出的诗歌理论和诗人所持的同一诗歌理论的相异之处。一个是对诗人无意识写作方法的描述,一个是诗人本人有意识地根据理论写作,这完全是两码事。在感动人心的写作中,诗歌理论变得有所不同,不再只是诗人写作方法的解释说明。而瓦莱里确实是个写作时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诗人,也许,在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并没有完全遵从理论的指导,但是他理论上的阐述无疑影响了他写作的诗歌类型。他是所有诗人当中自我意识最强的。
除了极度的自我意识,还需给瓦莱里加上另一个特点:他的极度怀疑。也许大家会认为,这样一个不相信任何事物能成为诗歌主题的人,大概会在“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中寻求庇护。但瓦莱里实在是太过怀疑,就连艺术也不相信。值得注意的是,他多次把自己写的东西称为ébauche——草稿。他不再信赖诗歌目标,只对创作过程感兴趣。很多时候,他不断地写诗,好像仅仅是因为他对写作中自己的内省式观察感兴趣。你只需读读他的几篇文论——有时确实比他的诗歌更激动人心,因为你能察觉到他在写这些文章时会更兴奋些——就可看到他的观察记录。在《杂文集·卷五》(他文选集中的最后一卷)中有这么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至于我自己,我承认,相比作品本身而言,我更关注(艺术)作品的形成和构建”,并且,该书下文说道:“在我看来,最本真的哲理更多的不是在深思的对象中,而是在思考行为及其处理的本身。”
现在,通过瓦莱里,两个可以追溯到爱伦·坡的观点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第一个观点由波德莱尔从爱伦·坡那里得出,我也已引述过:“诗歌除了其本身应当什么都不考虑”。第二个观点是创作诗歌时应当尽可能地深思熟虑、字斟句酌,诗人应当在创作中观察自己——而这点,在如瓦莱里般多疑的脑子里,得出了一个与另一观点极为矛盾的结论,那就是创作行为本身比其结果也就是诗歌要有意思得多。
首先,要说的是爱伦·坡诗歌的“纯粹”。从“语言纯粹”这个意义上来说,爱伦·坡的诗歌远远谈不上纯粹,我已经对爱伦·坡遣词造句时的粗心大意和肆无忌惮做过评论了。但是在“纯诗”这个意义上,那样的纯粹对爱伦·坡来说就轻而易举了。主题无关紧要,技巧举足轻重。他不需要通过净化过程来达到纯粹,因为他的素材已经够空洞稀薄了。其次,爱伦·坡有那么一个缺点,在说到他对理论显得并不相信而是拿来消遣时我曾提到过。这里,爱伦·坡和瓦莱里的思想,两个极端再次相遇,一个是不够成熟的思想在玩思想游戏,因为它还未发展到令人信服的程度,一个是过度成熟的思想在玩思想游戏,因为它太过多疑而无法让人相信。通过这一对比,我想,正好可以解释瓦莱里对《我发现了》的崇敬之情——那个宇宙幻想并未给我们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在哲学、神学或是自然科学上爱伦·坡知识有限,但是瓦莱里,继波德莱尔之后,却把它作为“散文诗”推崇备至。最后,爱伦·坡对《乌鸦》的创作分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创作哲学》是不是恶作剧,是不是自欺欺人,是不是爱伦·坡写这首诗时谋篇布局的大致准确记录,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瓦莱里提供了一种方法和一项工作——观察他自己的写作。当然,一个比爱伦·坡更伟大的诗人已经研究过作诗过程。在《文学传记》中,柯勒律治主要关注的当然是华兹华斯的诗歌。但他并没有联系自己的诗歌写作来进行哲学探索,可他确实是先提出了这个让瓦莱里着迷不已问题:“写诗的时候,我在做什么?”爱伦·坡的《创作哲学》恰好“聚焦”这个问题,并对这个最后终结于瓦莱里的关于作诗过程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瓦莱里通过内省性批评活动,已经将诗学的深层研究推到了一个极点,在这点上前者开始破坏后者。路易·博勒先生在对瓦莱里的出色研究中,中肯地评述道:“这种精神自恋与这位诗人并不陌生,尽管他没有解释他作品的全部:‘为什么不能把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作艺术作品呢?’”
现在,我想我也已经暗示过了,我相信这种萌芽于爱伦·坡而成熟于瓦莱里的“诗艺”,已经尽其可能得到了发展。我想这种美学对后来的诗人不会再有任何帮助。拿什么来取代它的位置,我并不知道。但仅仅是否认前者的美学是不可能取而代之的。坚持主题的极大重要性,坚持认为诗人作诗应该自然而然、不经思索,应该依靠灵感,忽视技巧,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都只是从高度文明到野蛮的退化。必须有这样一种美学,不管怎么样,它应既能包容也能超越爱伦·坡和瓦莱里的思想。我并不十分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诗人的理论必须来源于他的实践,而不是实践来源于理论。但我承认,首先,在从爱伦·坡到瓦莱里承袭下来的诗学传统中,涌现了一些让我极为赞赏和喜欢的现代诗歌。其次,我认为这种传统本身就代表那百年中、在任何地方都最引人关注的诗歌意识的发展。最后,就某些诗歌发展前途的探索而言,我对这种探索行为本身就很重视,因为我们相信应该去探究所有的发展前途。而且,我发现,在尝试通过波德莱尔、马拉美,尤其是通过瓦莱里的眼光来观察爱伦·坡后,我更彻底地确信他的重要性和他的作品作为整体的重要性。至于未来,一种合理的假设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进步,这种在瓦莱里身上发现的对语言的过度警觉和过分关注,会因重荷的不断增加而使人类大脑和神经变得不堪忍受,最终必将土崩瓦解。同样地,它也可能会被保留下来,科学发现发明无穷尽地深精细究,政治社会机器无止境地细化发展,也许会将我们带到那样一个阶段,那时,人们对人性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厌恶,乐意接受最原始简单的磨难,却不愿再背负现代文明的重担。对此我并无定论:我留给你们思考。
朱振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