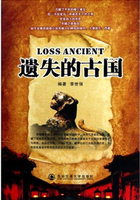邓友梅
老朽八十有二,脑细胞退化,近老年痴呆,为少闹笑话,少说错话,正自令封笔,落得个自在,好友周明突然来电,要我写篇稿子谈谈“走过的路”。我说我已作了封笔决定,他说决定很好,但要写完这篇再执行。友命难违,可是走八十二年的漫漫长路,回头望去曲折遥远,都找不出路口来了。从哪儿说起呢?
我祖籍是山东省平原县,就是当年刘备当县长时,发现有人刺杀他,吓得从城墙下水道爬出去的那个平原县。虽然刘备当了皇帝以后,在下水道口上雕了“龙门”两字。可当地人民的生活难度一点也没改变,闯关东成了改变生活唯一出路。我父亲十一二岁时就随着乡亲下了关东,在东北拉洋车时,被一个奉军军官叫去给他拉包年,给予士兵待遇,从此当上了东北军。直奉战争随奉军进关,到了天津,在天津结了婚。奉军返出关外时他开了小差,留在天津打工,所以我1931年出生于天津。在天津长到十二岁,上高小一年级时,我爹和日本工头打架遭到追捕,全家就逃回了山东老家,我从这里走上“人生之路”。
在老家要继续上学,我村没学校,姑姑村里有所小学。我就住到姑姑家上学。姑姑那村较大,东头有汉奸据点,驻着伪军和“区公所”,姑姑家和学校都在西头,夜里有穿便衣的八路军和侦查人员来去。村人都热情接待。但学校却只有初小一二三年级。老师听说我已上五年级,在课堂上没什么可学的,就叫我帮着写黑板报,看学生作业,他们从中辅导我。这些事都是在教师工作室做,我也就知道了他们在课堂外的活动。
我只读过4年小学,我读小说是从看张恨水、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和《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开始的。我11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后,由于故乡是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我12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我家40斤小米几丈粗布,令我复员,并要我尽快离开老家,怕鬼子扫荡抓住我。既是为了我的安全,也是怕我经不住考验。我就到天津投亲,从此流浪在天津街头。碰上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我见机会难得,求着人家把我收下,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干了一年多。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我们送回中国,打算叫我们再在他们在中国的矿山上劳动。中国人回到中国后就有办法了,我在几个大工人带领下就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我在天津流浪时,街头有出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才收几分钱。我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只有租书还租得起,就读起了小说。为消遣读书,又没人指导,唯一的选择就是好看。《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碰上什么看什么。看着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换一本。就这样开始养成了读书报的习惯。
在日本当牛马,见不到中文书报。回国参加新四军后,一开始在连部当通信员,见到书报真是如饥似渴。我当通信员,营长见我爱读书挺高兴,不光表扬我,到团里开会时还专门上宣传科替我找书,日本投降后部队要把一些没机会上学的小同志送进学校去补习文化,营长抢先要了个名额,把我送进了根据地一所中学脱产学习。可我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缺少个演小孩的演员,找了几个孩子面试,人们见我会说国语,脸皮又厚,而且是部队送来代培的,没有军籍问题,一张调令我就成了文工团员。
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我管小道具——点汽灯,最多的是爬在幕后小声念剧本给台上提词。这样人家演一个戏我等于念了一个剧本,念多了无意中受到了编故事、写对话的熏陶。那时演的戏多半是小歌剧和秧歌戏,于是也学会合仄押韵。解放战争打起来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作即兴演出。行军时部队走路我们就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要现编现演。我们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我就靠我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看见从路上走过来的是炊事班,我就打着板儿说:“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同志们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缴枪。”团长一看我比上海来的大演员还编得流利,以后除了点汽灯,还叫我参加编写小节目。有回我数快板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我说:“我会数,但有的字我还写不出来。我说你记行吗?”这样我说他用文字记,他拿回去过两天在报纸上印出来了。那位编辑又拿着花生、柿子来找我说:“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费。不过这稿子是我替你写成文字的,还给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们俩一块吃!”这就是发表的处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1951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这才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陈登科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错,可他那笔字比天书还难认。不光写得草,还自己创造字。稿子里有好几处的“马”字下边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稿子发愁地吸了半盒烟都猜不出念什么,念“马”吧,没有四个点,前后句子也连接不上,不念“马”应该念什么呢?恰好康濯从他身边经过。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说:“我猜念‘趴’,马看不见腿不是趴下了吗?”写信问陈登科,他说他创造的这个字就是“趴”。当时文学研究所收的就是这类人。
进了文学讲习所后,我认真读书,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我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所里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如讲屈原,主要就请游国恩讲,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讲。听曹禺先生讲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但听完回去自己写起作品来,他讲的学问却一点也用不上。当时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儿,吃饭在一个食堂。有次回家,在吃早饭时我和他坐在一起。他问我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反应?我说:“你讲课大家很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说:“小邓,我写了一辈子,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我说:“您的秘诀不告诉别人,总可以传授给我吧!”曹禺笑笑说:“说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写上,真要讲,一个钟头就说完了,你们规定一课讲两个半小时,只好一多半时间讲废话!”我又问:“那一个小时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时也没有,也就有15分钟。其实15分钟都用不上,就一句话:你想学着写剧本,就背上三个剧本,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别的没窍门。”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学写作其实跟学骑自行车一样,看人家怎么骑你就怎么骑,骑不好就挨摔,摔着摔着就会了。想学写小说,就读好小说,读通了再写,就跟不读的时候不一样。
文学作品有没有客观标准?当然有,有历史和社会评价问题。我们提倡读名著,读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但作为一般的读者,有权利选择自己较为喜欢并与自己阅读水平接近的书籍来读,个人喜欢看的书读来就印象深。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也正是自己曾喜欢读的书籍,对自己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读的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作家是名人,翻译家也是名人,但我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什么也记不住。如果只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写诗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学习歌德的阶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没人时打开抽屉看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来了,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所长召开座谈会,了解学员读书情况,有人已给她汇报,说邓友梅从不认真看课程内的书,却偷着看武侠小说。丁玲很开通,她说,没关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就多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经过一些年的创作实践,我的体会是:读书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接受的频道,不是这个频道就不能接受。读得进去的作品写作时有意无意会去模仿它。没有一个人开始写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学习水平与接受水平是会不断提高的。后来我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巴尔扎克的著作也读了不少。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张天翼同志。我问他,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技能。他说,记日记。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当时在鼓楼,宿舍与课堂隔着一条马路),一个月要走几十趟。你给自己提个要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过去没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另外,在记的时候,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而设法让人看了得出你的结论。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说漂亮两字,你只写她的形象出来,让别人读后感觉真是漂亮。你想骂一个人,也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读后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记生活手记的习惯。对社会、对人生总想多看多了解。天翼同志说,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这样才接近真实,并能引起别人同感。当了“右派”以后,不敢再往本上写笔记了,怕被拿出来歪曲解释,作为抗拒改造的罪证。就每天睡觉前把看到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重新思维一成。经过两年多,没有记录,好多事都忘了。但没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记忆的。
我从文学讲习所出来以后,写了一篇小说《在悬崖上》(1956年秋)发表在《处女地》,接着在《文艺学习》转载。当时红了一阵,我也有点晕乎,觉得这回真是要当作家了。1957年赵丹来找我,约我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他先付1000块钱订金。我正闷头改写剧本,全国作协叫我去开会。一共通知了四个人,我、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作协两位领导跟我们四位年轻人谈话,内容就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响应号召参加“大鸣大放”。作为青年人,作为共产党员,你们不带头谁带头?什么时候不能写作,非这几天写?什么时候不能下乡呢?非现在下乡?当时刘绍棠正准备第二天下乡去,票都买好了。只好把票退了。我也把正写的剧本停下了。按党的号召参加“大鸣大放”。
到5月16日那天,报纸上登出《这是为什么》。“反右”正式开始了,紧接着报纸上批判刘绍棠。有一天我在南河沿碰见王蒙同志。他对我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我比较谨慎。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了。这时领导又来找我说话,说你当不当“右派”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现在要批评刘绍棠,这是党对你的考验。看你是什么表现。我很想借着批判刘绍棠摆脱我自己,于是准备了一个发言。我对刘绍棠“反党言行”不知道,只知道他下乡时,要让家里人蒸点馒头带着去,乡下饭难吃,到老百姓家吃饭也麻烦,所以下乡去总带着几斤馒头。我批判他时就给他上纲说:刘绍棠,你深入到农村生活,还带着馒头!你还能像农民的儿子吗?底下听众一听就鼓掌。正在鼓掌时,走上来一位领导宣布说:“大家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早被定成“右派”了。要是早知道就不来开会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到1976年对我宽大了一点,摘掉“右派”帽子,便让我提前退休。退休后我回到北京,这时已妻离子散。家中只有我一个人。派出所还老让我汇报跟什么人有接触。又有什么运动思想。我只好每天到“陶然亭”躲着。“陶然亭”有一批划到另册的人天天一块打拳。那里有大喇叭可以天天听广播,所以没事就爱上那儿去。陈毅同志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从小在新四军军部,认识陈毅同志,当了“右派”以后,无处可诉,就给陈毅同志写了一封信。没过一个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陈毅同志回信并说只要有政策给“右派”摘帽子,第一个就给我摘。这使我非常感激。听到他去世,我心中非常难过。但又无人可倾诉,我就断断续续把回想起他的一些小事记了下来。没有题目,只是些片断,写了一些陈毅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来看我。在给她做饭时,为了叫她能安稳地坐着,没别的事好叫她干,就找出这几篇乱写的东西给她看。谁知她看完后竟说:“你把它改成小说好不好?”我说:“改小说干什么?没有人会发表我的东西。”她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表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了。”我考虑没必要叫她替我冒险,她说:“你才40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说大有来头。局势也许会好转……”我照她说的改了篇小说。
小说改了两遍,她认为可以发表了,给我劳动改造时的工厂写信,请保卫科替我写了一个证明“此人劳动改造期间没发现新的罪行”。既然没有新罪行,茹志鹃就给我在《上海文学》发了,起名叫《我们的军长》。没想到“四人帮”刚打倒后第一次全国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被评了个一等奖。
接着,刘绍棠、从维熙、王蒙等陆续回到了北京,重新动笔写作了。一下子引起极大轰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景。
这时我已经40多岁,好容易从被群众专政状态中解脱出来,又拿起笔来冒险值不值得?我要认真考虑,要写就得写出点模样来。若只是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一下,没多大特色,就犯不上花这工夫了。写作好比跑马拉松,起跑的时候有上万人,跑到一半连5000人也剩不下了。到最后5公里坚持下来的人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到冲刺阶段只有三五个人了。若不跑到冲刺就不要跑。文学的冲刺是怎样冲法呢?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得也有点模样,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有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要有自己所长胜别人之所短,经过衡量比较,我终于琢磨出自己的强项。王蒙是北京清华园长大的,他父亲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他生活在知识区,对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没我了解地道。刘绍棠也是北京人,但他是通县农村人。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来北京很早,一进北京就参加安排旧皇亲贵族生活的工作,熟识了一部分八旗子弟。小时从大人嘴里听说旗人都是又爱吃,又爱吹,讲求面子却没本事挣钱的一族。我们参加安排八旗子弟的工作后,发现以前对他们的看法不全面,甚至有成见。旗人平均的文化艺术修养比我们汉族人高。再进一步细了解,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消闲美食文化等方面,学问很深。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群体怎么垮到这么穷困的地步呢?原来清朝一入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满洲统一了中国,全民族成员都有功,从此旗人男子一出生就有一份俸禄。从今后旗人不许做生意,不许学手艺,不许种田。学文要当文官学武要做武将,起码也在旗里吃一份钱粮!这是胜利者的特权。恰恰是这特权带来了悲惨后果。一旦清朝帝制倒台,没有了政权撑腰,他们的后代连混饭的本事都没有了。要饭都赶不上汉人,因为他们拉不下脸来。“文革”中我被定为“反革命”,在工厂劳动改造,气温零下40度,没有住处。花140块买了个地震棚居住。有一个京剧团的朋友竟要求和我来同住,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他是大清国驻欧洲某国钦差大臣的女婿,是大清国内务府大臣的嫡孙。他没地方住,溥仪被赶出宫就在他爷爷任上。他连买地震棚的能力都没有,只好找我搭伙。我们在一个炕上住了四五年,我从他那里感受到不少旗人贵族的特色。文学是语言艺术,光熟悉生活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打成“右派”后,好几年我在北京劳动。家在右安门,在德胜门外工作,每天下公路过天桥,我都到茶馆听说书。故事我都知道,就是为了听艺人用北京土话述说故事的功夫。因此我比王蒙、绍棠更能使用北京市民口语。和他们比,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表后反响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同时也没有放弃写其他熟悉的生活,只是写别的用另一套语言,只有写北京人的生活我才用北京土语。其实我写战争花的工夫最大,我认为那才是主旋律,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写革命历史,但除了《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两篇作品得了奖,其他都没有什么反响。说实话,我写北京题材的作品时最省劲儿。写京味作品,我只注重有趣和有味,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时代,消失的历史。写《烟壶》时并没有想写爱国主义。后来觉得只写艺人的生活经历分量不大,就加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内容。但只是着眼于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北京从元朝起作为国都几百年,任何一家老百姓的起落兴衰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认真地反映了一家百姓的命运,就能把那一时代的整个历史背景折射出来。过去学了文艺理论,总想用小说去套理论,所以写不好小说。只有当你的小说无意去套理论,而所表现的生活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时,这才是小说真正起的作用。
我写京味儿作品,也写战争历史作品,为什么花费力气大的一些作品反而不一定好?我想,读者读书首先要选有趣的,有趣才好看,我写京味小说,首先是想怎样把它写得好看。看来要把小说写好看,就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与你的性格最易呼应又是你最易于表现的生活素材。生活内容复杂多样,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写成小说。最体现本质意义的才是最值得写作的。但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人眼里看来感觉却未必一样。同样一座山,画家感觉很美,很有价值入画;而地质学家就可能觉得它不含矿产因而没有开采价值;交通工程师则从修路的难度上考虑它的地位。作家深入生活,就要找有美学价值的东西观察,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写出来都好看。作家要善于发现有艺术含量的生活素材。张天翼同志让我养成随时观察有趣事物的习惯。第一是有趣,但光有趣也不行,还要有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看了我的小说,总要起到愿意当好人不愿当坏人作用才好。在我的所有小说中,90%数大路货,只有10%是我特有的产品。我的体会是,哪篇小说写得特别顺,哪怕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写出来,这篇小说故事的结构、情节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写得顺说明酝酿得成熟。但在语言上要想写出特点就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这是苦功夫。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要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真正讲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说,有一句废话都很刺眼。长篇就比较松弛点,长篇小说没有废话的很少,也很难。中短篇小说可以做到像鲁迅先生所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和标点符号。
20世纪50年代看苏联小说很多,我的《在悬崖上》就受其影响。一次我问老舍先生,为什么我的小说进步不大?老舍先生说:“是你在语言上没下工夫。瞧这段话:(从远处慢慢走来一个飘摇着两条腿甩着手上挎着一个包的眼睛发亮的女士),你念着顺嘴吗?你自己念着都打奔儿,别人看着能顺溜吗?以后你写完稿子自己先出声地念两遍。你自己念着不打奔儿了,别人就看着顺溜了。”这以后我写完小说就大声念,念着绕嘴的地方就必定改顺它。这些都是技术问题。技术功夫是较容易练的。心里感受的功夫难练。要发现自己最善于感受的场景,要研究哪种生活境界对你最敏感。在文学界哪种题材的作品一走红,许多人都跟着写,这是笨办法。人家能写好的你不一定能。我的小说很少写景,因我写不出像样的风景来,这可能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时候到日本去当苦力,日本河山很美但没有心情欣赏,关心的是少挨点打。后来到新四军当兵,成天行军打仗,最关心的是路好不好走。我写不出风景,写小说时就尽量避着。但我比较敏感人情世故,就特别注意观察这些方面,发挥自己的长处。我比刘绍棠大5岁,70岁的老人和6岁的老人看来差别不大。可是6岁的小孩子和1岁的孩子看到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我6岁上小学时绍棠还不会说话。从7岁到14岁我还看到了旧中国什么样,1949年一进北京,我看到了老北京的模样。描写起旧北京来我就比绍棠有更多的直接感受。发掘自己的宝藏很重要。每个人如果认真审视门己,都会有自己特有经历、特有感受和生活积蓄,要静下来寻找自己的长处,谁先认识这一点谁就先走一步。
还有一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外国文学新的写作思维方式要不要学?要学,但不要死学。学习写作,首先要模仿。什么样叫模仿好了,即叫人看不出你在模仿别人就是好了。学习别人写作,要学得让人看不出来。让人家觉得你是自成一派。工业生产要标准化,文学千万不要标准化。文学没有绝对的标准。诺贝尔奖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谈西方文化,他们外国人是权威,谈中国文化,我们是权威。有西方学者曾经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金?我回答:“有两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第一我们要写得更好。第二你们各位的东方文化水平要提高一点。”我们要有自信。你越去迎合他们,他们越看不起你。在文学上我们也要向西方学习,学习新的创作思维观点,但在小说的写法上,还要坚定按照自己的写法写。
日本出樱花,中国也要种樱花,种得再好也不是你的特点。可是中国有菊花,有牡丹,这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个人与整个文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也是这么一种关系。搞文学,必须发挥自己所长,要发挥自己所特有的审美的和表现美的观念与手法。
原载《艺术评论》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