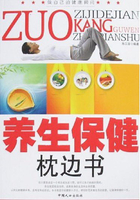皇帝颔首,收敛了面上的惶惑不安,正襟危坐,肃容道:“今日孙儿来,还有一事和皇太太商议。孙儿想立皇嫡子保成为皇太子。”
太皇太后微怔,荧荧烛火之中,她发间的银丝华光微闪,发间的点翠珠饰映着烛光,宛若水色,“保成还小,过早地立为太子,就是过早地成为靶子,更何况你如何知道来日保成能是个明君?若他德不符位,你又将如何处置太子?废黜他,有害父子之情;留下他,有损社稷万民。”
皇帝正色道:“孙儿既然下此决心,就一定会好生教导太子,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请太皇太后放心。”
太皇太后定定看着皇帝,半晌才道:“事关国本,不可轻动立储之念,我好好想想,皇帝,你也再考虑考虑。”
“皇太太……”
“好了,”太皇太后挥手制止了他,“我累了,皇帝跪安吧。”
皇帝只得讷讷不言,苏麻喇姑送他出门,皇帝低声道:“苏麻,你帮帮朕。”
苏麻喇姑莞尔,“太皇太后的性子,皇上自然是知道的,这事您不让她想清楚了,她不可能应下来,您现在强逼着,反而惹得太皇太后越发不高兴,您且耐心等等。”
送走了皇帝,苏麻喇姑接了宫女递来的奶茶,亲自送到太皇太后手边,太皇太后眯眼看她又端了热水盆来,“你很少这么伺候我了。”
苏麻喇姑蹲下身,褪去了太皇太后的鞋袜,将她的双足泡入温水之中,“奴才服侍您多年,也是看着皇上长大的,皇上性格坚毅沉稳,自小就是帝王之才,立太子一事,您何不就交给他自己决定呢?”
太皇太后望向桌上跃动的烛火,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只蛾子撞上那温暖喜人的火苗,嗤的一声便被烧作一块焦炭,太皇太后伸手碾碎了,低声道:“苏麻,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为了皇位,兄弟阋墙,你死我活的事,你见了不少,皇帝立保成为太子,若保成能弹压住他的兄弟们也就罢了,可一旦不能,那就是夺嫡争位的又一场血腥之战,皇后的嫡长子没有保住,连皇后都因生嫡次子而薨了,我心中愧疚难当,实在是不想保成过早地卷入储位之争中!”
苏麻喇姑笑道:“有您在,有万岁爷在,太子必定是一代英主,您不看自己把万岁爷教得多好。”
“我教得,当真好吗?”
太皇太后不禁质疑,顺治时的那些荒唐事一件件地浮现眼前,顺治帝福临、孝献皇后董鄂氏、静妃……一个接着一个地在她眼前晃荡,“先帝也是我亲自教导,怎么他就处处不如皇帝呢?”
“这……”苏麻也不敢擅言,“奴才别的不敢说,在孝献皇后过世前,先帝确实是一位好皇帝,许是四阿哥和孝献皇后的先后离世逼得先帝成了那副模样,常人言道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想来就是这个道理。”
太皇太后冷笑一声,支着额角看苏麻喇姑,讥诮道:“你说,福临心里真的有董鄂氏吗?董鄂氏疾革之时,他召寝不断,皇子公主越发多,若真的伤心,还能顾念到旁的女子?与其说董鄂氏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被他活活逼死的。福临,哼,他从来不懂爱,不会爱,他的爱是一把剔骨的钢刀,伤己伤人!”
苏麻道:“那当今的皇上呢?”
太皇太后趿上元宝鞋,苏麻喇姑忙上前搀扶,“玄烨,他还没有遇到一个真心喜爱的人。你看皇帝登基这十三年,对待朝臣,铁血手腕;对待后宫,有宠无爱。你若问他,那些给他生过皇嗣的,他能认出几个,皇帝必然无法回答,可若你问他,后宫之中重臣的女儿有哪些,他必定知道得一清二楚。这虽然是一个好皇帝必要的条件,但于玄烨而言,心中无一人,太过孤清,再好的帝王,也不过是一个处理国家大事的木头人。”
苏麻喇姑伺候着她歇下,自己坐在脚榻上,“奴才总觉得,咱们皇上心思沉稳,纵然有真心恋慕一人的那天,也绝不会如先帝那般。”
太皇太后被她逗笑了,“我总说你偏疼玄烨,你还不信,如今果然自己说出来了吧?”
苏麻喇姑莞尔,“莫说奴才,便是主子您不也心疼万岁爷吗?这人心啊,都是偏的。”
十月,简亲王喇布和安亲王岳乐的军队先后出发,赶赴战场。皇帝协同太皇太后及后宫众人往南苑行猎。
太皇太后道:“从前在盛京时,太宗皇帝时常带着众人围猎,那时太宗的儿子们都是一把好手啊,可惜皇帝的儿子们还小,不能一试身手了。”
皇帝拿起猎弓,跨上骏马,道:“孙儿的皇子们虽小,可是兄弟们却都是个顶个的好手,绝不失我满族男儿豪情!”
恭亲王常宁四下看看,“隆禧那小子呢?”
皇帝试了试弓弦,笑道:“太妃病了,昨日他向朕请旨,入寿康宫看望太妃去了。”
裕亲王福全道:“那小子看太妃是一个缘故,臣弟看来,他是最懒的,躲开今日的围猎才是要紧。”
太皇太后闻言,看向皇太后,“钮祜禄氏病了?”
皇太后颔首,“一入冬就有些发热,昨儿夜里喝了凉茶,今儿便起不得身了。”
贵妃亦道:“昨儿奴才打发喜哥去送了些补品过去,今儿早起也问过太医了,太医说太妃是贪凉,吃坏了胃肠,才引起发热,清淡两日就好。”
皇太后笑着握住贵妃的手,向太皇太后道:“东珠这孩子实在是个细心妥帖的,这才入了冬,她就亲自带人将各处的吉祥缸查看了一遍,又将各宫有疏漏的地方合计一处,向内务府报备,往年因为冬日烛火用度增加之故,总有走水,这一回可让人放心多了。”
贵妃端庄浅笑着,敛衽起身,八团花缎绣四君子石青便服盈盈而动,“这原是奴才分内之事,当不起太后娘娘如此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