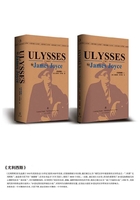我在小说中说:此一刻,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在搂着自己的老婆或别人的老婆睡觉,慈禧太后正在西逃的途中,天高皇帝远,有谁会注意到边界上此一刻发生的事情呢!
我的马挖起了蹦子顺额尔齐斯河直下。记得我说过我骑的是一匹好马。
一边是河水,一边是茂密的森林。灌木丛里有着许多的明堡暗堡,明堡暗堡里有着许多的窗口,这些窗口随时有理由射出子弹,因为这是在苏联领土上。
头顶上则是一座黄土山。黄土山上并排排列着八个雷达,这些雷达据说可以监测到中国内地兰州军用机场的飞机起落。雷达发出“咔咔咔咔”的声音,令人心悸。
我飞奔过去,拦住跑在最前面的那头牛,并且用马靴照它的大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这是一头大驮牛。牛是一种聪明的动物。这头大驮牛早就知道自己闯祸了,正在等待着这一脚,现在这一脚踢下来,牛立即折回头了。
所有的牛都折回头了。现在我赶着这些牛往回走。
后来我突然看见我的左手,树林子遮掩处,有五个打马草的人。他们挥动着大刈镰,一下一下地打着。他们把外衣脱掉了,挂在树骑兵术语。马的高速运动姿势。前蹄悬空,猛往前纵,像蚂蚱一样,一点一点地飞跃。
上,那外衣是苏军的军装。他们现在穿着的,是一种斜开领的恤衫,这种衣服,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肖洛霍夫的小说中都见过。
这五个打草人是苏联兵。
他们也在我发现他们的同一刻发现了我。
那天我穿着衬衣,光着头。瞅见我骑着马走来,他们最初以为我是苏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为他们送午饭的,于是停止割草,拄着镰刀,向我喊叫。
接着他们看清了我的眉目。
他们一个就地卧倒,卧倒之后,见我只是一人,又没有武器,于是又爬起来,到树下去取他们的枪。
我吓坏了。
我再也顾忌不了这些该死的牛了。我一叩马刺,马飞奔起来。而那些该死的牛,也像受了惊吓,争先恐后地跑开了。
我的耳后传来拉动枪栓的声音,但是没有开枪。
我的马是一匹好马。它载着我越过二分之一界河,越过绿茵草地,越过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越过一号口的密林,一直冲进白房子边防站的黑色碱土围墙,才停下。
牛也一个不剩地跟着我回来了。
气喘吁吁的我走进连部,指导员正在值班。看见我惊魂未定的样子,他左半边脸的肌肉嘟嘟地抖动起来。
我叙述了我越境的经过。在叙述中不停地看着门口,生怕那五个打马草的苏联兵再闯进来。
在叙述完以后,也许是鬼迷心窍了,我说,要不要将那块绿茵草点。我说,按照边防政策,边界上地形地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要向上级报告,何况现在,是界河在这里分岔,形成一块绿茵草地。
后来我停止了说话,因为指导员一直沉默不语。
他显然在紧张地思考着。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能看见他的半边脸在猛烈地抖动。
后来是他打破了沉默。他装着漫不经心地问:“真的有这么一块--孤岛一样的地方吗?珍宝岛战役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说确实有这么一块地方,这是我的目击!
“那么,有必要将它向上级汇报吗?”他有些鄙夷地问我。
我说按照边防政策,咱们得汇报的。
指导员沉吟了半晌,显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做出决定的他,半边脸不再抖动,而是显得异样的平静。而他对我,也显得突然地亲昵起来。他说,这事他知道了,报不报是他的事,这你就不用问了,以后这孤岛的事,也就不要再去说它了。
指导员后来大约并没有向上汇报,因为白房子依然相安无事。
白房子边防站没有向上汇报,而对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大约也并没有向上汇报。包括这块孤岛,包括我的越境,便成为一桩永久的秘密。
这真是一种伟大的默契。
我常常想方边防站的管事的,也一定是一老谋深算的家伙。
直到我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刻,摸摸自己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我才明白了指导员那个决定的重要的意义。他令这白房子的几十名可怜的士兵免去了一场杀戮之灾。
如果汇报上去的话,那么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之后,中苏边界冲突也许会出现第三个地名:白房子!
我在后边将要讲铁列克提事件。铁列克提事件就是由于决策部门懵懂无知形成的。当边防站将电话打到新疆军区,询问能不能到那块争议地区巡逻时,接电话的是一个参谋。他问:“那块领土是我们的吗?”边防站回答说:“是我们的。在中国版图之中,况且,我们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那里放牧。”参谋一听勃然大怒,说道:“那还请示什么!既然是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去那里巡逻!”这样,铁列克提三十一名官兵踏上死亡的征途。
铁列克提的故事放在以后再说。
在告别指导员的时候,我说我到白房子以后,一定要到河口去看看那个孤岛。
兵团人
18日下午我去了兵团。《兵团日报》和《绿洲》的朋友们约我吃饭。
他们告诉我19日出发。老杜已经给我把日程排满,到北屯呆两天,到哈纳斯湖呆两天,到185团呆两天,到186团呆两天。
我同意他们的安排。但是我说,一定要我到边防站呆两天,看看碉堡,看看战壕,看看了望台,看看一号口、二号口、三号口,看看我当年扛过的那个六九四〇火箭筒,现在是谁在扛着,看看我当年骑的那个额上有一点白的马,现在是谁在骑着。
饭局上,看着兵团人那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我想,我也许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克服障碍,将今天的兵团人和二十几年前的兵团人联系起来。
正如我费了许多的努力,才将今天的指导员和二十几年前的指导员联系起来一样。
我记得他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的军装,破烂不堪。这军装有土黄色的,像电影上的国民党溃兵穿的道具服装。有绿色的将校呢,那服饰的肩头还有挂肩章的两条带儿,记得185团五连的连长,一个山东老兵就穿这样的服装,不过这服装已经十分的陈旧,满是尘土,太阳又晒得它发灰发白,那连长穿在身上,一副怪模怪样的样子。还有人字呢的军装,人字呢如果洗得发白,会很好看的,但是,服饰的主人根本没有心情洗它,于是这人字呢又黑又脏,像挂在人身上的一堆活动的抹布。
在那个险恶的年代里,兵团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漫长的边界上堆起一座肉体的长城。
我永远忘不了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入我境那一次,我看到的兵团人的情景。
胡子拉碴的男人扛着老式的步枪,骑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老马(光背马),纷纷地走向边界。女人们将家里的一点破烂,用床单打成一个包揪,然后坐在包揪上,手里拖着孩子,准备撤退两厢。
勇敢而苦难的人们哪!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炎热的中午,中亚细亚的太阳猛烈地炙烤着,我扛着铁锨,到兵团的条田里去为边防站的菜地要水。
一个面孔黝黑的女人站在春小麦地里,扛着圆锹,穿着长统雨靴。她那件褪了色的花格子衬衣才叫我看出她是一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边防站种菜班的班长,想给菜地里要一点水。她听了,默默地用铁锹戳了一阵,于是,水汩汩地流向了菜地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陕西兵。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的家在遥远的天津,她是1965年来支边的,邢燕子那一拨。“你们知道邢燕子吗?”她问。
我现在记起来了,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写过有一次边防站放电影,兵团用马车拉来一些人来看。我将一位大嫂让进班里,让她坐在铺边喝水,大嫂的孩子,则在床上乱滚。突然,孩子望着白色床单上那一团一团的东西,问妈妈这是什么。孩子说:“这一个像中国地图,那一个像世界地图。”妈妈脸红了,她训斥了孩子一顿,恰好这时电影开演了,这个尴尬的话题才算结束,女人领着孩子看电影去了。
我小说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
我这里说的是185团的兵团人。我那时候只能看到他们。
在兵团司令部,我还得到一个惊人的史料。
这史料是,我居住过的那遥远的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在1962年修的。
哦,我的白房子!哦,我的兵团人!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兵团人有着如此深沉的一种情愫。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个妈蚱,我们是难兄难弟,我们共同支撑了那一块白房子天空。而这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建起来的!
兵团农十师从各连中抽调了出身好,身体强壮,打过仗的农工,组成三个连队,给每人发了一枝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条干粮袋,然后说,要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得半个月时间,结果,将三个连队拉到了这里,占领和驻守在这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这三个连队后来又带来家属,组成185团。
185团在给自己盖房子的同时,给这块争议地区盖起两座边防站,它就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和白房子边防站。
这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的事。1963年5月,两个边防站开始驻军。
在兵团,接待我的兵团文联的曹主席感慨万端地说,这些事情总有一天要有人将它写出的。我说,这一天已经到了,而写出的人就是我。
随着我的向白房子的走近,我还将要写许多的事情。而185团进驻白房子争议地区的事情,我也许还将要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