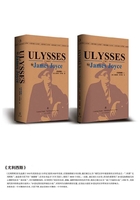“红玲去后岔沟摘山芋肉。”七爷的这句话,像一根棒子,在我心里横着拌一下,后就突然翘起,一下打在了我心上。我的心一哆嗦,身子跟着一阵颤抖,接下慢慢平静,如同开了一道门。那门是我从一道关了我很久的黑屋中找到的,先缓缓地打开一条门缝,露出一道清亮清亮湖水一般的光,后来我突然哗一声把门敞开,太阳就又圆又大地挂在中天,到处铺着金银混合的光色,河流、房子、土道、山坡、沟壑、林地,七七八八的景和物,全都明亮地映在我眼前。
我终于看到了另外一方天地。
我感激七爷。我想给七爷一眼感激时,七爷已经走进了那将倒未倒的场房屋。
半晌时分,家里的酒桌散了。
娘和姐在收拾碗筷。
爹坐在屋门口悠然地抽烟。
我悠然地回到了家,立在爹面前。
“咋说?”
“倒是你八爷想了个法儿:让你七爷出山。”
“七爷?”
“你不知道吧?你七爷他爹原来是咱瑶沟村的老郎中。你七爷自小就跟着他爹学医。你七爷这辈子在外闯荡就靠是半个野医混饭吃。听说前几个月你七爷还在乡下治好了几个哑病娃。队长说支书家哑媳妇不是天生的,是害过一场病,病好了喉咙就哑了。只要你七爷把支书家哑媳妇的病治好,支书和他媳妇不会不感激,不会不把红玲嫁到瑶沟村。”
我很想笑爹,很想笑队长三叔和八爷们。可他们是我的长辈,是瑶沟村的头头脑脑,瑶沟村的事情都靠着他们去主持,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不敬。
“哑媳妇的病……能治好?”
“队长去问你七爷了。”
“治好了要支书和他媳妇同意,红玲不同意咋办?”
“哑媳妇是她嫂子,红玲总得有点良心吧。”
我笑了,终于轻轻淡淡地笑了一下。那笑的模样我看不见,但我知道我的嘴角挂满了一串一串对爹和队长三叔们的瞧不起,挂满了一串一串对他们的嘲弄。
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想。
在来日罢了早饭时候,我说爹我下地了,就扛着铁锨上了耙耧山。我家在山上的地是在东梁。上山后我径直朝西梁走过去。
过去西梁就是七爷说的后岔沟。后岔沟中有很多野生的山芋肉树,浅紫浅红的小果子,如野酸枣似的零零星星挂在枝条上,摘下来一晒一制作,就是上好的补养中药。
红玲就是去那儿采药的,我也要到那儿去做我要做的情事。待我的情事一做完,娶红玲那些使村人想过朝朝暮暮的东西,就会如秋果一样挂在秋天的树上,伸手一摘就到手了,就成为实在了。
爬上耙耧山,太阳很清丽地在远方悬着,光线柔韧地射过来,像一条条绷直的丝线。不消说,天气很好,天空上白云淡淡,仿佛如透明细纱张在高远的头顶,水蓝色的天底,把那纱似的白云浮起来,又像飘着丝丝连连的羊毛。我爬上山坡的时候,景景物物都在白云、柔日下显得十分雅静,十分幽妙,十分动人。出沟的老鸹一群一群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影子凉阴阴的井水般从我脸上滑动着,“呱呱”的叫声哗哗啦啦从半空中雨一样落在山坡上。眼下,收过的秋地都已耕犁锨翻过了,新土被湿夜潮了一遍,显得被洗过一般洁净,远远看着,一块一块,如同飘落在荒坡上的崭新的红布。
我观赏着这些景物,心事歪歪地到了西山梁上,坐在了山脊的顶端,后岔沟就全裸进了我眼里。这天的后岔沟,在日光中是一种紫黄色。沟中的稀落树木和崖头的荆荆条条,在那紫黄中微微地摆动,晃得我眼睛发光。
红玲还没有来。
我把目光从后沟移开去,扭过头,就看见田湖镇五颜六色地坐落在山脚下,绿的树木,灰的房屋,红的学校和小工厂,青的河流,黑的沥青公路,把田湖镇错落涂抹成搅混了的色盘儿。就在这色盘儿中间,支书家的三层小楼直直地戳在中央,显得各家房屋、各条街道和街道上的大小摊点,都趴在地面被吓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在山顶,能看见大街上动着的人群,如雨前搬家的蚂蚁,一群一股地移动。在那移动的人群中,我依稀看清了支书缓缓地朝我走来,又缓缓地离我走去……
十二年前我八岁,那当儿我是个贼,黄瓜、番茄、豆子、小麦、红薯、柿子,七七八八的熟了我就偷。一季不偷,一季的日日夜夜心里不牢稳,总悬着如学业一样神圣的那么一件事。夏天的时候,西瓜熟了。一个镇就那么一块瓜地,在伊河边的沙地上,像蓝天碎下一块落在了那里一模样。我脱光衣服,从上游伊河进水,游到瓜地边,盯着瓜棚望一阵,就爬进了瓜地里。那天的沙地烫得我肚子起泡,为了不把肚子贴在沙地上,我就把屁股举起来,像举着两个又白又虚的大蒸馍。太阳火一般在我的屁股上烧着,西瓜如太阳般在我眼前照着。我朝最大的西瓜爬过去,身子一动一动,像一条饿瘪的小虫在瓜秧中穿来穿去。
我把最大的、边上插有记号做种子的西瓜摘掉了。我推着西瓜像推着一个车轮朝着伊河边上爬,可当我爬出瓜田的时候,我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块还没吃完的西瓜,像拿着一牙红色的月亮。
“哪个队的?”
“十八队的。”
“娘的,又是你们十八队!”那个人骂着,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我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往沙滩上飘落,他就举着我摘的那个西瓜去瓜棚了。
那人就是支书。
支书那时候每天都到伊河中洗个澡,吃个瓜,坐到天黑凉快时,从各队田头视察着回到镇子上。支书走到瓜田埂儿上,肩膀像一块门板一开一合,闪闪烁烁。我望着支书的肩膀,就像望着一座快要倒压在我身上的绝崖石壁,于是,我忙不迭儿把目光朝下移了移,看见了支书的鞋。
支书穿的是一双新做千层硬底儿布鞋,我就如记住了我的年龄样记住了那双鞋。
到田头当中时,支书又回头盯着我,“你说你们瑶沟村为啥尽出贼,不会出一个让人瞧起的人物来?”
我没有回支书啥话儿。支书也不等我回话就又朝瓜棚里走去了。我始终盯着支书的鞋。
回到家,我的肚子上有一个千层底的鞋印儿,青青的,像一片大极的椿树叶。全村的人都围着我的鞋印儿看。娘和姐在看着我的鞋印儿哭,爹在一边抽闷烟。
有人说:“奶奶的,找他去!”
队长三叔说:“是支书踢的,你找谁去?”
至今儿,支书踢的那一脚仍然有些疼。虽然过去了十二年。
红玲终于被我等来了,好像来晚了羞愧似的慌匆匆的。
她骑个自行车,车后夹个篮子,沿着沟底的土道,把车子骑到后岔沟口,一扎,拿着篮子朝后沟的土崖上爬过去。我在山梁上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只绵羊在崖壁上小心地一脚一脚移,到崖壁的半腰,那儿有了一片坦处,坦处上有几棵小树,她就在那树下不动了,把篮子挂在树枝上,双手在枝间抓来揪去。
我盯着红玲不动,心里火急火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只要那个时刻一来,我就可以朝我发现的大门走过去,把门闩打开,敞开门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太阳、村落、河流、山坡、镇子、街道啥儿的,就会朝我走近。红玲会哭着嫁给我。踢过我一脚的支书会成为我岳父。大队改为村了,支书退下了,我会成为村里的一个人物。全村四千二百多口人,大事小事都将去找问我咋办,而不是去问今天的支书。而这些,还刚刚是我的开始,我才二十岁,我不可能在田湖大队——田湖村干一辈子,我不可能在瑶沟村日日夜夜过光景,直到了死!往年,有多少乡干部都是从各大队干部中选拔的。我会在田湖村干得不错,会成为全县极出色的最年轻的村干部。然后,我会被选拔到公社去,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再也不是农业户口了。也许,我会首先当两年公社团委书记,或是公社抓某一项工作的党委委员,再或是一上来就被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分工我具体抓工业或农业;一半年后,公社书记或乡长突然因某次车祸或啥儿案子,死了或被免掉了,我就成了乡长或书记,那时候,我二十五岁,最大二十七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长或乡党委书记,被送到啥儿党校学习两年,回来就留在县委了,日后就从县政府或者县委一级一级干上去,干上去……我不知道我到底会干到哪个位置上。七年前听说一个工人初中文化,三年之内从车间主任干到了副省长的位置上。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儿,我没有那样的命,但我准定会给瑶沟村争得荣耀,整个儿田湖镇祖辈世代没出个如我一般的人物。我在田湖镇、我在田湖公社、我在瑶沟村……独一无二。也许还会留下一块纪念碑……
我的头有些儿晕。
太阳温温暖暖抚摸着我,山梁上开始散发出被太阳照热的甜腻腻的土气。白云一片片在日光下游动。麻雀的叫声,在我身后啁啾成潺响不断的溪水。对面的沟崖上,红玲已从一棵树下移到了另一棵树下。
我静静地等待着,像我在镇子车站上等着一辆客车的到来;像我儿时过了新年,过了正月十五等待着下一个新年和十五的到来。不消说,那时间流得如冬天凝着的河水。麻雀的叫声把我弄得心烦意乱,仿佛我在等着的不是客车或新年或十五,而是等着一口去运棺材的牛车。我坐过运棺材的牛车,那车走得和我眼下的时间一样的慢。我真想对着红玲叫两声:
你快滚下土崖吧!
你快些滚下土崖吧……
红玲采山芋肉果的那面土崖真是很缠缓,是一道偏陡的坡地,只中间坡腰上有段险处,离沟底约有丈余深浅。再往上走,那陡坡就突然后退,留下一片很平的崖地来。这崖地上有七株山芋肉果树,像七株枣树错落在崖地上,组成一小片儿芋肉小果林。我很惊奇这儿有片小林我为啥从未发现过,几年前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割牛草。
红玲是邻近午时骑车走了的。
红玲走后,我就立时下了梁子,爬到后岔沟这面坡上,到红玲采过中药的地方看了一遍。她采过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凌乱的洋布胶底鞋的鞋印儿,印儿上星星般布落着饱满的紫红色的小果子。我捡了颗小果在嘴中咬破了,极苦!我嚼着那苦味在坡地走了几遭,那七棵药树,红玲采了六棵,还有一棵未采。不消说,她准定还要来把这棵树给采掉。每一棵树上的山芋肉,在药店都可以卖上百十块。也许,她今儿后晌就来采。
都是天造地设的事情。真幸运她还有一棵没采的树。
我看了各处的地势,就慢慢沿着来路往回走,当下到那段陡坡时,我抓住一根荆枝吊着身子登在一个石头上,然后,用尽平生的力气往外拉。荆条的蔓根在板结的崖土上,嘶叫着被我拖出来,像拽一根被啥儿压着的绳子。那黄根从粗到细,越拽越长,当到了一拉即断时,我又把拽出的黄根塞回原处,用虚土掩了我拖根留下的土崖裂痕。接下,我把身子朝东靠了靠,抓一块石头猛砸我脚蹬过的那块凸石。“砰砰”的声响,在后岔沟里单调回响,崖壁上的斑鸠、麻雀和卧在崖壁窝中的黑老鸹,被这声音惊得一团一团飞向天空,为了望我似的盘旋一圈儿,才朝对面梁子飞过去。
那灰色的凸石松动了,松动得一蹬即落。
我从崖壁上爬下来,抬头望着那松动的石头和就要断了的荆根,像观赏我二十岁往后漫长的人生图景。我的一切辉煌的想法都要从这石头和荆条真正开始,从这儿仔仔细细地迈出第一步,走向那遥远、艰难的以后。
我该走了。太阳已没了那温顺柔软的亮光,变得火毒起来,似乎是正夏一般。
走了几步,我心里动一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有角有棱的尖石头看了看,犹豫着回来放到了那崖壁的下面。
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走了。
我操他祖宗八辈子,后晌,我在对面梁上等到天黑,红玲没来采果树……
来日,我又在对面梁上等了一天,红玲依旧没有来采那棵树。
太阳西沉时,山梁上下空无一人。天离我又高又远。土梁的红色如血般浸泡着我。我对着后岔沟那七棵山芋肉果树,撕着嗓子叫了一声:
“红玲——该死的红玲——你赶快死掉吧红玲——”我走了。
七爷说支书家哑媳妇的病不难治。三叔说你一定要把那哑媳妇医成能说话的人。七爷想了想,说瑶沟到了出人物的时候,别说是让我医个哑媳妇,让我死了我也不能不死。
月亮升上来的时候,队长三叔让我和他去支书家。我去了。我要看看红玲为啥这两天没去后岔沟。那棵山芋肉果树还等着她去采。那松动的石头和将断的荆根也还在等着她。
在支书家小楼的正间屋里,支书坐在一张椅子上抠着脚趾缝的泥,看着当天送来的两天前的《人民日报》。我和三叔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条凳上。
三叔说:“都不在家?”
支书没抬头,“都串门去了。”
三叔说:“来给你说个事……”
支书没抬头,“孩娃们的婚事以后再说吧。”
三叔说:“不是。是你家……儿媳妇的病……”
支书没抬头,“咋?”
三叔说:“能治。”
支书突然坐直身子,手从脚趾缝里抽出来,硬硬地看着三叔,“谁能治?”
三叔说:“我们村的七爷。”
支书默了一阵,“笑话……她这病连省城大医院我都托人问了,说是死哑。”
三叔说:“七爷在乡下治好了几个死哑,现在人家连歌都能唱。”
支书又抠着脚缝,“真的?”
三叔说:“真的,偏方治大病,又不花钱,不妨让七爷试试。”
支书拿起了《人民日报》,“治好了当然好,花多少钱都可以。”
三叔说:“明儿天我把七爷带来?”
支书翻着报纸,好像寻一篇啥样的文章,眼却瞟着门外,“别急,红玲这两天去县里进货刚回来,她娘明天想走娘家……忙过去这几天,我去请七爷。”
队长三叔不再说啥,拿眼瞟着我。我说我们走吧。三叔说走吧。支书说你们走?我送送你们。我们就一线儿出了支书的楼屋。院里月光如水,哑媳妇端个盛有猪食的盆子站在门口的黑影里,我们一出来,她就匆匆端着猪食往支书家后院猪圈去了。
支书说送我们,却站在门口盯着匆匆走了的哑媳妇不动。
回家路上,队长没说一句话。
我也没说一句话。
我们默默地走着,月光在路上被我们踩成了碎片儿,到村口分手时,队长三叔说,“我日他奶奶……你回家睡吧连科。”
我又在山梁上静等了两天。
爹说:“山地上那点活还没干完?”
我说:“没完。”
爹说:“别去了,先把下边地的小麦播上。”
我说:“你别管我!”
爹惊疑地盯着我。
我在爹的惊疑中,早早就爬上了耙耧山,蹲在后岔沟对面的山梁上。我像一个守家狗样凝视着梁下那条土道。太阳在我的凝视中变动着各种颜色,静默悄息地朝着山顶爬。日光中的土沟里,盛满了躁人的暖气和浅红色的尘土及浅红色的尘土气息。在那暖气和气息中,土道舒展地从沟口进来,朝沟底伸去,如同一条没有拉紧的丈量沟长的皮尺。最后,红玲就是从这皮尺上骑车过来的。那时候,我在山梁上等得就要瞌睡,忽然看见有道光在眼前一闪,仿佛雨前的雷电在眼前划过了似的,浑身一震,就看见红玲来了。和几天前一样,她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自行车在太阳下闪着热辣辣的亮光,不慌不忙地从土道上朝后岔沟口靠近。我的心开始萎缩起来,激动和快乐如手锤般砸着我的心,仿佛是砸一个牛皮战鼓。她车后的篮子里,盛满了堆起来的阳光,在车上起落颠动。她不知道后岔沟等着她的是啥儿,车子骑得悠悠然然,在土道上起起落落,好像是站在一条船上在湖中随风飘荡。我死眼盯着她朝后岔沟靠近,每近我一车轮子,激动和快活的手锤就在我心上密集一阵,仿佛要把我的心敲碎,把我的胸膛敲炸开一般……
终于,她到了沟口,扣下了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