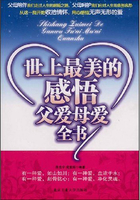塞拉的《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是那种能引起你各种情感及生理反应的小说,它是如此强烈,以至阅读这本书时会感到非常新奇和刺激,常常会处在震惊、悲悯、叹息、宿命等等诸种情感的旋涡中。这个小说世界离“人”很远,小说中的人似乎更多地拥有一种类似动物的本能,人物的心理完全偏离正常的轨道。就像小说中杜阿尔特这一家处在城市边缘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处在文明没有覆盖的地方,他们过着赤裸裸的兽性生活。
小说中,关于父亲得狂犬病的描述,是这个骇人世界的最好的象征。父亲是个粗暴的家伙,动不动就要揍母亲和孩子。但一次父亲被一只狂犬咬了,这个可怜虫无可救药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我们”将父亲关进了壁柜。父亲“像雄狮一样乱蹬乱踢,并发誓要将我们全都杀死”。两天后,父亲死了。“我们发现他俯伏在地,脸部表情就像恶魔一样叫人害怕”。这似乎是一个被某种病菌侵害的、疯狂被无限放大的世界。
塞拉在这部小说里表现了他对暴力的迷恋及对某种丑陋事物的奇怪的偏好。在叙述者“我”的生活中,父母的棍棒对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父母经常相互挑衅,母亲总在找机会辱骂父亲,父亲则“好像是正在等她骂出这些话来好打她似的,立即抽出皮带,边追边打,一直到累了才停止”。暴力像种子一样落在“我”的身体里,以致“我”成年以后的第一次性事就是用暴力的方式完成的。这里,爱情(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变异为施虐和受虐。
第一次性事出现在“我”弟弟的葬礼上,出现在“我”弟弟的坟墓边。女的先骂“我”像死去的弟弟……接着就是一阵残酷的搏斗。“我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按倒在地上……我咬她,把她咬出血来,弄得她筋疲力尽,驯服得就像一匹小母马”。完事后,女方露出微笑,夸“我”是一个男子汉。“她的话像雷一般在双唇中轰鸣。”她说:“我爱你。”
小说中对丑陋事物的描述非常逼真精细。小说这样描述“我”弟弟:“这可怜虫只能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像老鼠一样在喉咙和鼻腔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吱吱声,这是他学会的唯一本领”。他身上长满了疹子。“小屁股两边的好肉与小便和水疱上的脓血混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给剥去了一层皮一样”。他四岁时被一只猪猡咬掉了耳朵。这之后他一见到猪就两眼露出恐怖,赶紧躲起来。这个可怜的弟弟后来淹死在油缸里了。“我们将他捞起来时,从嘴里流出的油就像金丝一样连续不断,一直流到肚子上”。小说充满了这种可怖的描述。小说中的比喻更加深了这种丑陋和暴力导致的灼痛感。“他给我的肋部留下了一块好像用烙铁烙过一般的伤疤”。
小说还充满了无论从道德还是伦理上来说都极为反常的情感反应。小说中的笑声,往往是在人物处在最悲惨的时候发生的,因此,这笑就像一道咒语,就像撕裂这个世界的一道闪电。比如,在父亲得狂犬病死后,面对父亲可怖的惨状,“母亲不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啼哭,反而笑了”。又比如,“我”弟弟咬了拉斐尔先生(弟弟的出生是拉斐尔同母亲通奸的结果)一口,拉斐尔就使劲地踢弟弟,直踢得弟弟鲜血直流,“血都快要流尽了”,这时,拉斐尔“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笑得合不拢嘴”。母亲竟也同拉斐尔先生一起同声大笑。在小说的安静时刻,小说让弟弟体验了一种令人“辛酸”的幸福感:在母亲对弟弟“像产了崽的母狗一样”的轻轻的抚摸中,我看到“弟弟一生中第一次微笑”。
塞拉宣称他探索的是“人类的责任、悲剧性的体验及揭示我们的困惑的那些境遇”。因此,塞拉写下这些暴力事件,是因为“文学的界限恰好就是人性的边界,它标明了神和魔鬼之外的天地”。塞拉在诺贝尔奖的答谢辞中,提出了写作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在这个很大一部分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虚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决定性工具:它能够在通向自由的无尽的征途上为人们指引方向。”
五、炸成两截的桥
安德里奇那部用平实的编年体大纪事式的笔法写就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命运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了维舍格列城人四百年间的日常生活。在长长的时间的轴线上,南斯拉夫民族的命运呈现令人难以捉摸的诡秘。这部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小说的真正主角是一座桥。这座桥的象征性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一座联结着历史和现实的桥,也是时间的河流上一个演示命运轨迹的舞台(每一桩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是历史深处最惊心的一幕:杀戮、死亡、血痕、横征暴敛、飞来的横祸以及自相残杀。这块被土耳其人统治了三百年,后又被奥匈帝国占领了一百年的土地,有着无比复杂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因此桥也成了渴望民族和宗教之间相互沟通的象征。最后,这座有四百年历史的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成两截,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依旧悬而未决。
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我看过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地下》。这是一部有着奇幻想象力的超现实风格的电影,这部电影表面上讲述两个游击队员不同命运的故事,但实际上真正的主角依旧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这个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五十年后因南斯拉夫爆发内战而分裂作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象征和隐喻。我之所以在此谈到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发现了南斯拉夫艺术家共同的特点和精神气质:对苦难的关注、深刻的反省、真切的悲悯以及含着泪水的宁静和博大。我想这一切肯定是由这块土地的多灾多难和历史的戏剧性决定的。
安德里奇的另一篇小说《卖柴》也有着足够长的时间。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依布罗·梭拉从富家子弟沦为孤苦伶仃的卖柴老头的漫长一生的故事。小说在一声叫卖声中开始,然后安德里奇向读者描述了卖柴的依布罗的肖像:身材瘦小,眼中布满血丝,卑微,麻木,是一个靠卖柴挣几个小钱的酒鬼。安德里奇非常冷静非常残忍地让这个人物的一生处在动荡而苦难的生活之中。小说的前半篇,安德里奇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性格的悲剧,但后半篇,小说指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悲剧。他的家产被挥霍完了,他的老婆死了,他被市政厅开除了,他成了一个酒鬼。这时,安德里奇让老人得到了短暂的也是最后的安慰:老人的女儿和女婿常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帮助。“他简直觉得她(女儿)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于是对人夸耀女儿和女婿成了他酒醒时最大的乐趣。但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老头很快失去了他唯一的安慰:他的女儿被捕后被穆斯林卫兵打死了,他的女婿参加了游击队最后战死在战场,做了一个伟大的英雄。这时即使最麻木的人也会被小说所透出的难言的酸楚所打动。老头知道这些消息后向人们喊:“我那女儿和女婿可真了不得啊!听哪,你们大家都听哪!他们……啊,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是老头最绝望的时候,也是老头最骄傲的时刻,小说此刻喜剧性地设置了让老头拒绝了别人买柴这一情节。“我不能替任何人把柴送到楼上去……懂吗?如果你要买柴,你自己下楼来拿。”老头说完就在别人的恶毒的叫骂声中远去了。在这篇小说里,依布罗的回忆被一声声的叫卖声打断,因此这叫卖声就有了逸出其声音的意义,这成了这个孤独的人和世界的唯一的联系。最后,小说理所当然地在叫卖声中结束,所有的声音消失在无边的寂静里,消失在我们满眼的泪光之中。
安德里奇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命运让他处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最为中心的旋涡之中。那个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杀奥国皇储事件同他还有点关系,因为他和那个杀手普林西是同一个组织“青年波斯尼亚”的成员,他因此进了监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好是驻德国大使,他是在德国人攻占贝尔格莱德后才离开柏林的。他回到南斯拉夫,又被德国人软禁。在二次大战隆隆的炮声中,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
六、跳蚤的方式
萨拉马戈在《修道院纪事》中设计了一只有趣的狡猾的跳蚤。先让我们看这只跳蚤如何在皇宫的威仪前长驱直入的。
说的是王后久未怀孕,国王很着急。他向上帝承诺若王后怀孕,就造一座修道院。承诺完后,国王想试一试。国王和王后同房有一套庄严的仪式,一本正经。跳蚤就躲在王后的床垫底下,它一般不轻易出动。当国王在动的时候,它安静着。当国王不动的时候,它开始动了。萨拉马戈说,对跳蚤来说,“国王高贵的血液和城里其他普通人的血液没有好坏之分”。这时,跳蚤咬中了王后,但王后怕国王的圣液流出体外,不敢动。她只能忍受跳蚤的胡作非为。这天,国王做了个梦。国王先梦见一棵树,然后又梦见树上长出了一座修道院。这说明,王后怀孕了。
显然,这是一只有立场有原则的跳蚤,它有“平等意识”,并且看起来它还颇有点儿不畏权贵劲儿,其姿态是挑战性的。这只跳蚤只在本书的第一节出现,但事实上,这只跳蚤迅速繁殖,已经扩散、隐藏在本书的每一页。这是萨拉马戈写作中一条强烈的讽刺脉络,萨拉马戈喜欢挑衅,尤其是在涉及权力和宗教的时候。小说在描述王公贵族出场时,没有像古典小说家那样在此会情不自禁地炫耀自己的博学,萨拉马戈用简洁的口吻说:他们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但他们的区别我们也看出来了,那些珠宝多的地位高,珠宝少的地位低。萨拉马戈没有说出的话显然是:地位的高低并不取决于生命质量的高低而仅仅是因为珠宝的多少。萨拉马戈总能这样看穿那种严肃的形式的本质。当然萨拉马戈也会讽刺普通人,但萨拉马戈给了民间社会更多的越轨机会。比如在四旬斋期间,妇女们可以不负家庭职责,“家庭之中会增加一些戴绿帽子的丈夫”。萨拉马戈接着说:复活节后妇女们都说累死了,但灵魂得到了安慰。可见,这只跳蚤在咬普通人时,显然温和得多。因此,这只跳蚤具有“民间立场”,虽然也喜欢咬普通人,并把他们咬得发痒,但它更多地是针对现存秩序的。就是妇女们给丈夫戴绿帽子一事,针对的也还是宗教的清规戒律。
这就是萨拉马戈的一贯方式,即“反讽”。在谈到反讽时,萨拉马戈说:“反讽有点像你晚上走路穿过墓场时吹口哨,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那么一点儿人类的声音,拙劣地掩饰恐惧,就可以忽视死亡。反过来说也没错,如果我们连反讽的能力也没有,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小说中有一个缺席的、不偏不倚的客观叙述者,似乎可以对自己所叙述的东西不作任何反应。其实“站在什么地方说话”应该是小说基本的道德。我就喜欢这只跳蚤的立场,尖利得能够刺痛我们,但不至于使我们受不了。我也喜欢这只不那么一本正经的跳蚤,见有油水可捞,就不会放过图个快活的机会。我还喜欢萨拉马戈印在封面上的照片。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但这皱纹向我们展示的不是沧桑,而是孩子气。他好像在同我们玩一桩有趣的游戏,他仿佛在那里说:你们抓不住我。
《修道院纪事》是一部关于人类意志力的小说。小说由两个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国王劳师动众建造修道院,即国王的意志;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发明“大鸟”这种飞行器,即人类联合的意志。国王的意志是以人民的血汗和牺牲为代价,使人类相互对抗,而如果人类的意志联合起来并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不但能对国王的意志提出挑战,而且最终能实现人类的梦想。
但这不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这部小说应该是想象的产物,小说赋予“历史”以超现实的夸张和变形,使历史看上去像一个神话。小说描述了许多奇迹。比如,在修道院停放的尸体不腐烂也不僵硬,四肢还像活着时那样任人轻轻挪动。这尸体放在那里,能使盲人复明,能使跛子走路,后来人们埋了尸体,奇迹不再。比如,书中的女人布里蒙达在早饭前具有超人视力。更大的奇迹应该是“大鸟”飞升的叙述:一块块琥珀吸引垂死者的意志,从而使“大鸟”靠众多意志的力量升上天空。什么是奇迹?奇迹即是超越我们自身限度的事物,但它应该蕴藏在人类内心的深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景观。人类通过梦想抵达令人激情澎湃的神秘区域。
我猜想萨拉马戈的小说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我指的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可能是萨拉马戈灵感的源泉。比如,修道院和飞行器,在《百年孤独》中就有一个用钟摆机器制造一个飞行器的故事,还有一个飞行员飞过修道院因为爱上一个人而一头扎了下来的故事。比如萨拉马戈的另一部小说《失明症漫记》显然受到《百年孤独》中“文明失忆症”的启发。又比如,他们的叙事同样具有巴罗克风格。但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区别相当大。马尔克斯更原始,更感性。马尔克斯的世界具有人类原初的单纯力量,但又有一种庞大的多种成分混合的喧嚣。而萨拉马戈是个理性的世界,他的创作方式需要想得更清楚,需要更强的逻辑能力。
七、污秽尘世中的女性光芒
试图用一个词概括一位作家是不可能的,但词语有这样一种功能,写在哪里,哪一部分就会裸露,当然相应地,其他的侧面就可能被遮蔽。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写文章的很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我发明的,这套我是向评论家们学来的。评论家总喜欢用一个旗号来概括数量惊人的小说。
因此,我有理由不去谈马哈福兹这位笨重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其他好的或不好的方面,只谈谈他笔下的女性。他笔下的女性确实写得好,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充满了尊敬和爱怜,同时似乎怀着某种深远的内疚和忏悔。马哈福兹喜欢关注那些风尘歌妓,在他的笔下,这些女性似乎是另一种类,她们饱满、健康、敢作敢为,与一般的良家妇女比,她们显得更为光彩照人。这大概是因为她们活得更真实、更本性的缘故。考虑到马哈福兹生活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考虑到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比较严厉的禁忌,马哈福兹这样写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马哈福兹说,“这些堕入风尘的女子比身上贴着虚假光圈的政治人物要高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