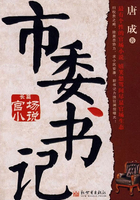“跟我来,我现在带你去见老板,否则只有等到晚上七点了。”
他们走过候客厅,原先等在那里的人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弗雷斯蒂埃一出现,那位年轻的女士和很像过气演员的老妇人立即站起身朝他走过去。
弗雷斯蒂埃把她们带到窗边,尽管他们说话时尽量压低嗓音,但杜洛瓦依然听到他们之间以“你”相称。
然后,弗雷斯蒂埃和杜洛瓦穿过两道包着软垫的门,来到经理办公室。
杜洛瓦进门后才发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原来只是经理和几位戴着平顶帽的先生在玩纸牌。其中有几位,杜洛瓦前晚已经在弗雷斯蒂埃家里见过。
瓦尔特先生拿着纸牌,聚精会神地玩着,动作老练。他的对手也不赖,出牌起牌,手法熟练,一张张花花绿绿的薄纸片被他们玩得得心应手。诺贝尔·德·瓦伦坐在经理椅上埋头写作,雅克·里瓦尔则叼着雪茄,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房门一直关着,里面空气浑浊,还掺杂了一些家具散发出的皮革味、陈年烟草味和印刷品的油墨味。在所有报馆的编辑室里,我们都能闻到这股气味。
在一张镶铜红木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种纸张和印刷品:信件、明信片、报纸、杂志以及供货商发票。
弗雷斯蒂埃和站在玩牌人身后的几位先生握了握手,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他们身边看牌。瓦尔特老头拿下一局后,他趁机说道:
“我朋友杜洛瓦来了。”
经理的目光突然从镜片上方射过来,打量着这位年轻人,然后说道:
“我要的那篇文章,您带来了吗?关于莫雷尔质疑的讨论已经展开,如果这篇文章今天可以见报的话,效果一定非同凡响。”
杜洛瓦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折成四叠的纸片,说道:
“在这儿,先生。”
经理满心欢喜地接过去,微笑着说道:“很好,很好,您果然言而有信。弗雷斯蒂埃,要不你帮我看看?”
弗雷斯蒂埃连忙回答道:
“不用了,瓦尔特先生。为了教他入行,我和他一起完成了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
这时,轮到身材瘦长的众议员出牌,此人的观点属于中间偏左。瓦尔特先生一边接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既然这样,就听你的。”
没等瓦尔特先生开始新一轮牌局,弗雷斯蒂埃便俯下身来,凑到他的耳边说道:“您曾经答应过我让杜洛瓦接替马郎博,那么,是不是给他同样的待遇?”
“行,就这样。”
说着,瓦尔特先生又兴致勃勃地投入新一轮牌局。弗雷斯蒂埃赶紧拉着杜洛瓦离开了。
诺贝尔·德·瓦伦始终没有抬头,他好像没有留意甚至根本没有认出杜洛瓦。雅克·里瓦尔则走上来紧紧握住杜洛瓦的手,显得格外的热情。
当弗雷斯蒂埃和杜洛瓦再次穿过候客厅时,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看他们。弗雷斯蒂埃对其中那位最年轻的女士打了声招呼,声音特别响亮,好像要让在场的人都听到:
“经理马上要见您。他现在正在和预算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开会。”
说完弗雷斯蒂埃便急匆匆地走了,一副身居要职、公务繁忙的样子,好像正要赶去写一篇十分紧急的稿子。
一回到编辑室,弗雷斯蒂埃便从抽屉里拿出比尔包开,继续他的抛球游戏。他一边接球,一边计数,然后利用间歇向杜洛瓦交代工作:
“这样吧,你每天下午三点钟来找我。我会告诉你该去哪些地方,采访哪些人,是白天去,晚上去,还是第二天早上去·,·首先,我会给你一封介绍信,你拿着它去找警察局一处处长。二,他会安排一名下属和你联系,此人将为你提供所有重要的新闻。三,当然,这些新闻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消息。有关工作细节,你可以请教圣一波坦,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四,你可以马上去找他,也可以明天再去。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想方设法从被采访人的嘴里套出我们需要的信息。五,不管门禁多么森严,你都得想办法进去。……六,你每个月的底薪是两百法郎,如果能写出点有趣的采访花絮,并被选中刊登,将以每行两个苏计酬。七,如果报馆向你约稿,也按这个价计酬。……八,”
然后,他开始全神贯注地玩游戏,口里慢慢数着:“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但他没能接住第十四个,他抱怨道:
“该死的十三!这个数字总是给我带来霉运,我将来的死一定与十三有关。”
这时,一位编辑忙完手头的工作,也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球。这位三十五岁的编辑身材矮小,看上去就像个小孩。不一会儿,又有几位记者走进来。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到柜子前拿出自己的球。很快就有六个人了,他们并肩站着,背靠着墙,一次次地把球抛向天空。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手中的球却因为木质的缘故颜色各异,有红的,黄的,还有黑的。一场内部的比赛就这样展开了,还在工作的两位编辑这时也站起身来给他们做裁判。
弗雷斯蒂埃接了十一个。那个像小孩的矮个子男人输了,他按了按铃,对听差说道:“去拿九杯啤酒来。”他们趁机又玩了起来。
杜洛瓦和他的新同事一起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对弗雷斯蒂埃说道:
“我该做些什么?”
他的朋友回答道:“今天没什么要做的。如果你想走,现在就可以走。”
“那……我们……我们那篇文章……今天晚上付印吗?”
“当然。不过,这不需要你操心,我会帮你再改改。回去接着往下写,明天下午三点准时过来。”
杜洛瓦和在场的同事一一道别,尽管他现在还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然后,他兴高采烈地从楼梯走了下去。
乔治·杜洛瓦一晚上都没睡好。一想到那篇即将见报的文章,他就激动得辗转难眠。天一亮,他就起了床,到街上晃悠。这时候,给各报亭发送报纸的搬运工都还没来。
杜洛瓦来到圣拉扎尔车站,因为他知道《法兰西生活报》每天都是先送到这里,然后再分发到自己所在的街区报亭。由于时间还早,他只得在人行道上溜达。
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位女店主走到铺子前,把玻璃店门打开。接着,一个男人头顶一摞折成对折的报纸走过来。杜洛瓦连忙迎上去,却发现里面只有《费加罗报》、《吉尔?布拉斯报》、《高卢人报》、《要闻报》以及另外两三种晨报,就是没有《法兰西生活报》。
他不禁担心起来:“是不是他们决定明天再登《非洲服役散记》?或者,瓦尔特老头对文章不满意,最后决定把我的文章撤下来?”
他再次来到报亭,发现那里正在出售《法兰西生活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送来的。他丢下三个苏,拿起一份报纸迫不及待地打开,迅速浏览了一遍头版的标题,始终找不到他的文章。他的心枰枰直跳,急忙翻开另一页,紧张地搜寻着,终于在一篇文章的末尾看见“乔治?杜洛瓦”几个黑字。成功啦!杜洛瓦顿时感到兴奋不已。
他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往前走着,帽子歪向一边,脑袋里一片空白。此刻,他很想拦住每位行人,然后对他们说:“快来买呀,快来买呀,这上面有我写的文章。”他还想像那些夜间在街头叫卖的人那样,扯开嗓门,大声吆喝:“请看《法兰西生活报》,请看乔治?杜洛瓦的文章《非洲服役散记》。”突然间他有一种冲动,想到公共场所朗读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比如咖啡馆,总之是那种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于是,他开始搜寻已经有人光临的咖啡馆,他找了很久,最后在一家小酒馆坐了下来。这里已经坐了几位早起的客人。杜洛瓦叫了一声:“罗姆酒。”完全没有想到现在根本不是喝这种酒的时候,应该叫苦艾酒才合适。接着,他又喊了一声:“伙计,拿份《法兰西生活报》。”
一位穿着白色围裙的侍应生跑过来说道:
“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法兰西生活报》,只有《回声报》、《世纪报》、《灯笼报》和《小巴黎人报》。”
杜洛瓦一听,火冒三丈:“真是个小酒馆,还不快去给我买一份。”
侍应生赶紧出去给杜洛瓦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杜洛瓦开始津津有味地读起自己的那篇文章,还不时地大声叫道:“太妙了,太妙了!”希望能够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让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这张报纸究竟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然后,他放下报纸,起身离开。老板见状大声叫住他:
“先生,先生,您忘了拿您的报纸!”
杜洛瓦回答道:
“留给你们吧,我已经看过了。今天的报纸上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并没有指出具体内容,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看见刚才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先生拿起了那份放在桌上《法兰西生活报》。
杜洛瓦心想:“现在该做些什么呢?”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去办公室把这个月的薪水领了,顺便辞职。一想到科长和同事目瞪口呆的神情,他就激动得浑身颤抖,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可以看到科长一脸震惊的表情。
杜洛瓦走得很慢,以便在九点半左右到达,因为财务科十点才开门。
他的办公室很大,但是光线暗淡,冬天的时候,几乎一整天都得开着煤气灯。窗外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对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八位职员,还有一个副科长坐在角落里,用一扇屏风挡着。
杜洛瓦先到财务科把一百八十法郎二十五生丁的薪水领了,出纳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装钱的蓝色信封,交给了他。薪水到手后,杜洛瓦便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走进已经工作了一些时日的宽敞办公室。
杜洛瓦一走进办公室,便听到副科长波特尔先生的呵斥声:
“是您啊,杜洛瓦先生!科长已经问起您好几次了。您知道,他是不允许任何人在不出示医生证明的情况下请两天病假的。”
杜洛瓦站在房间中央,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大声回答道:
“我才不在乎这些规定呢。”
他的话在同事中间引起一阵骚动。大家都非常惊讶,波特尔先生也慌忙从那间小办公室的屏风上方探出头来,露出一张吃惊的面孔。
波特尔先生之所以坐在屏风后面,是因为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害怕吹风。为了监视下属的一举一动,他还在屏风上面挖了两个洞。
屋里静得连苍蝇拍打翅膀的声音都听得见。过了一会儿,波特尔先生终于半信半疑地问道:
“您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在乎这些规定呢。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被《法兰西生活报》聘为编辑,月薪五百法郎,稿酬除外。今天早上我已经开始上班啦。”
杜洛瓦原本不想这么快就把整件事说出来,而是想慢慢地戏弄一下他们,但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一口气说出来。
他的话果然取得了预期效果,同事们个个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
杜洛瓦接着说道:“我马上就去向佩蒂伊先生辞职,然后再回来和你们道别。”说完,他径直走到科长办公室。后者一见到他便大发雷霆:
“啊!您来了。您知道,我不能……”
杜洛瓦打断他的话:
“请不要这么激动……”
佩蒂伊先生身材肥胖,头发红得像鸡冠。他没想到会被下属顶撞,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说道:“我受够这鬼地方啦。今天早上我已经开始在一家报馆上班,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我现在是专门来向您辞行的。”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积蓄多时的怨恨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发泄。
杜洛瓦回到办公室,和旧同事们一一握手道别。但是他们都不敢和他说话,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前途。科长办公室的门一直开着,刚才科长和杜洛瓦的谈话,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
怀揣着刚领的工资,杜洛瓦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他先到一家经常光顾,口味不错,价格又公道的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除此之外,他还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并特意把它留在了餐桌上。然后,他又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的东西。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拿走这些东西,而是要售货员将东西送到他家。他告诉他们他叫“乔治?杜洛瓦”,并补充说道:“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然后,他留下自己的地址,并对他们强调道:“你们把东西交给门房就行了。”
因为时间尚早,他走进一家专门制作名片、快速领取的小店,让人给他印了一百张名片,当然他没有忘记在自己的名字下方印上了自己的新职务。
最后,他来到《法兰西生活报》报馆。
弗雷斯蒂埃见到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说道:“啊!你来了,很好。我正有些事情要你去办。等我一会儿,我先把手头的事做完。”说完便继续埋头写信。
桌子的另一头,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胖男人,面色苍白,脸有些浮肿,光秃秃的脑袋油光发亮。由于高度近视,他写东西的时候,鼻尖几乎贴在纸上。
弗雷斯蒂埃对那人说道:
“圣一波坦,你准备几点去采访那些人?”
“四点。”
“那你把这位新来的同事杜洛瓦也带去吧,让他领教一下这份工作的窍门。”“没问题。”
接着,弗雷斯蒂埃转身对杜洛瓦说道:
“你把第二篇文章带来了吗?今天早上发表的那篇反响还不错。”
杜洛瓦一时间哑口无言,结结巴巴地说道:“没带……我原以为今天下午可以写……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做……我没有……”
弗雷斯蒂埃显得有些不悦。他耸了耸肩,说道:
“如果你以后再不按时交稿,小心你的饭碗。瓦尔特老头现在正等着你的第二篇稿子呢。我只好告诉他,文章必须等到明天。如果你想只拿钱不做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啦。”
沉默片刻,他又说道:
“做事必须趁热打铁,像你这样怎么行!”
圣一波坦这时站起来,说道:
“我要走了。”
弗雷斯蒂埃往椅背上一靠,拿出一副训斥人的架势,神情严肃地对杜洛瓦说道“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两位贵客:一位是中国将军李登发,住在大陆酒店;一位是印度王公塔波撒依·哈马得赫·巴利,住在布里斯通酒店。你们马上就要去采访这两个人。”
接着,他转身对圣一波坦说道:
“别忘了我给你提过的采访要点。记得问问将军和王公,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活动有什么看法,怎么看待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否希望欧洲,尤其是法国介入他们的事务。”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道:
“如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报道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必定能吸引大批读者。”
他对杜洛瓦说道:
“留意圣一波坦的一言一行,他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勤记者。好好学习他是如何在五分钟之内让被采访人说出真心话的。”
说完,他继续低头写信,表情是如此严肃认真,显然是为了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让杜洛瓦这个昔日战友、今日下属清楚自己的位置。
一出门,圣一波坦便哈哈大笑起来。他对杜洛瓦说道:
“瞧,真是个装腔作势的家伙!居然对我们指手画脚,好像我们是他的读者似的。”
他们走下楼,来到大街上。圣一波坦问道:
“想喝点东西吗?”
“当然,天气真热。”
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圣一波坦一坐下,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把报馆里的每个人都从头到脚数落了一番。
“要说老板,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您知道,犹太人从来不会改变,都是一路货色!”然后,他还给杜洛瓦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事实,以此证明那些以色列后裔到底是如何吝啬小气。比如,节省区区十个生丁;像家庭主妇那样和商贩讨价还价,直到自己如愿;充当高利贷放贷人;做典当买卖等等。
“不仅如此,这家伙从不相信任何人,自己却什么人都骗。他的报纸,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自由派、共和派、奥尔良党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简直像个杂货店。其实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支持他的股票交易以及他开办的各种企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的实力日益强大,仅靠几家注册资本为四个苏的公司,就赚到了数百万……”
圣一波坦兴致勃勃地讲着,还不时亲昵地称杜洛瓦为“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