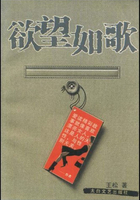马吕斯把所有的衣袋翻遍了,一共才凑起5法郎16个苏。这是他眼下的全部财富。他留下16个苏,把5个法郎递给了那姑娘。“这16个苏已够我今天吃晚饭的了,”他心里想,“明天再想法子。”
她飞快地抓过钱,说道:
“好极了,我看见了太阳。”
这是融化她脑子里积雪的太阳,她的话也像雪崩似的被引了出来:
“5法郎!个头儿大!亮晶晶!真棒极了!您是个好孩子。我把我的心交给您了!我们有好戏上演了!喝两天的酒!吃两天的肉!杀牛羊,炖鸡鸭,吃大锅的肉!放开肚皮,汤喝个够!”
她把衬衣提到肩头上,向马吕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摆出一副亲昵的样子,转身出门,边走边说道:
“谢您了,先生。没有关系。我去见我们的老头子。”
走过斗柜,她看见那上面有一块干面包壳,尽管上面满是尘土并且发了霉,她还是扑了上去,抓起来一面啃,一面嘟囔:
“真香!不过够硬的,牙要硌断了!”
说着,她出了门。
五天然的窥视孔
五年来,马吕斯一直生活在穷困之中,生活在匮乏之中,甚至可以说生活在悲痛之中,但是,他现在才发现,他领受的一切还远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悲惨。真正的悲惨,他刚刚看了一下。他从刚刚从他眼皮下走过的那个幼虫身上看到了它。事实说明,只看到男人的悲惨那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悲惨,如果你没有看到妇女的悲惨的话;而只看到妇女的悲惨那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悲惨,如果你没有看到孩子的悲惨的话。
一个男子,走到绝境之时,便是无可救药地陷入深渊之日。一切不幸统统向他的头上压下来。工作、工资、面包、燃料、勇气、毅力,一下子全都没有了。阳光在他体外熄灭,精神之光在他体内熄灭,四周漆黑一团。他碰到了妇女和孩子的软弱,便残暴地迫使他们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因此,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发生。绝望的周围围着的只是一层脆薄的隔板,这些隔板,每一片都紧紧地挨着邪恶和罪行。
健康,青春,体面,圣洁的、怯怯的新生体肤的柔性,温情,童贞,清白,灵魂的这些保护膜,都一齐遭受了一只手的穷凶极恶的蹂躏,这是一只在摸索出路时碰上污秽自己也甘于污秽的手。父母、儿女、兄弟、姊妹、男人、妇人和女孩,像矿物质,互相掺杂,彼此,粘附,不分性别、血统、年龄、丑行、清白。命运使他们背靠背地蹲在一间又脏又乱的小屋子里,凄惶而又酸楚地互相看着。他们是多么不幸呀!他们的脸色是多么苍白呀!他们是多么冷呀!他们似乎是生活在远离太阳的星球上。
马吕斯看来,这个姑娘似乎来自鬼蜮,因为她那种种丑态,只有黑暗世界才会有。
马吕斯几乎谴责起自己来,他觉得自己不该那样终日神魂颠倒,陷入儿女痴情不能自拔,对于自己的邻居,直到今天,并没有看过他们一眼,虽然替他付过房租,那不过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是人人都可能做到的。他马吕斯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好些。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自己和几个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只有一墙之隔,他们与世隔绝,摸着黑过活,如果拿人类的链条来比喻,自己与他们是挨得最近的一环,他感觉到他们在他身边生活着、喘息着,但却熟视无睹!每天,他无时无刻不听着他们走动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可他竟充耳不闻!在听到他们说话声的时候,还听到过他们的呻吟声,而他竟无动于衷!他的思想在别的地方,在幻境之中,在不可能实现的美梦之中,在虚无缥缈的爱情之中,在痴心妄想之中。在此情况下,对于一伙人,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说,和他是同父弟兄;从人民的角度来说,和他是同胞弟兄;而这些人却在他的身旁濒于死亡!徒然地濒于死亡!他本人甚至可以构成他们苦难的因素,他本人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因为,假使他们有另外一个邻居,不是有一个他这样愚痴的邻居,而是一个较为关切人的、一个乐于为善的邻居,那么,他们的穷困状况、苦痛的状况会被注意到,那样,他们也许早已得到照顾,早已脱离困境了!当然,看上去他们异常堕落、异常卑鄙,甚至异常可憎,但是,摔倒而不堕落的人有多少呢?况且“不幸的人”和“无耻的人”本来就是一个词,它们本就混淆不清的。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我们是不是在别人陷得越深时援助越应该有力呢?
马吕斯一面责备着自己——因为马吕斯和所有心地正直的人一样,时常以教育家自居,对自己有过分的要求——一面望着把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隔开的那堵墙壁,仿佛他那双充满怜悯的眼睛会穿透那隔墙,给那些穷苦人送去温暖似的。那堵墙很薄,是在窄木条和小木柱上敷了一层石灰。我们刚才还提到过,这隔墙挡不住声音,隔壁每个人的说话声,各个不同的嗓声,可以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只有马吕斯这样的睁着眼睛做梦的人对这一切才会长久不加注意。那墙,无论容德雷特那一面,还是马吕斯这一面,都没有裱纸,粗糙的白灰暴露着。马吕斯,几乎是无意识地在捉摸这层隔断。有时,梦幻也能和思想那样,能够进行研究、观察、忖度。他忽然站了起来。他发现,在那上面,在那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洞眼。那是一个由三根木条形成的空隙。堵塞空隙的石灰剥落了。人站在斗柜上,从那空隙中便能看清楚容德雷特破屋里的一切。怜悯有,而且应当有自己的好奇心。这洞正是一个窥视孔。为了帮助他而窥察他,这是许可的。马吕斯想:我一定看个明白,看看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究竟如何。
他跳上斗柜,凑近那个窟窿,向隔壁张望。
六兽窟
城市,和森林一样,各有各的恶毒、可怕生物的洞穴。不同的是,藏于森林中的生物是凶残而猛烈的、壮伟的,也就是说,是美的;而藏于城市中的生物则是凶残而污浊的、卑微的,也就是说,是丑的。同样是洞穴,兽洞胜似人洞好。野洞优于穷窟。
马吕斯所看见的便是这样一个穷窟。
马吕斯很穷,他的房子里几乎是一无所有,但他穷得高尚,他的房子也就干净。而马吕斯眼前所看到的邻居则穷得卑劣、肮脏、恶臭、令人厌恶、污秽不堪。一把麦秆椅、一张破桌子、一堆破瓶烂罐,角落里,两张破得不能再破的床,这便是全部家具。所有的光线都来自那个破天窗——上面有4块方玻璃,挂满了蜘蛛网。这光线不明不暗,刚好把人脸照成鬼脸。墙皮全都脱落了,满墙都是补缝和疤痕,那样子,会让人想到一张被恶疾破了相的脸。墙很潮湿,从内里渗出眼屎那样的黏着物。墙上有不少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地上还铺了一层砖,尽管铺得不大整齐;这里却既不见砖,也不见地板;陈旧的石灰地面已经被人踩得乌黑;地面高低不平,满是尘土,但仍不失为一块处女地——扫帚从来不曾碰过它;各式各样的破布鞋、烂拖鞋、破布,满天星斗似的一堆又一堆;奇怪的是,屋子里有个壁炉,为这壁炉每年也得付40法郎;还有一个炉子,炉子上有一口锅,炉边有些劈好了的木柴,一些炉灰,居然还生了火。两根焦柴正冒着烟。墙上挂了些破布片,还有一个鸟笼。
使这破屋显得格外丑陋的一个因素是它的面积大。它不但有凸角和凹角,有黑洞和斜面,还有一些“港湾”和“地岬”。这使它拥有不少的无法测探的吓人的旮旯,在那里仿佛藏着许多手掌一般大的蜘蛛和脚掌一般宽的土鳖,甚至哪个角落里还藏着什么牛鬼蛇神。
壁炉的每一边,都抵着一张破床,一张伸向门口,一张伸向窗口,它们与马吕斯正对着。
在邻近马吕斯借以窥视的那个洞的一个墙角上,放着一幅嵌在木框里的彩色版画,画的下方有两个大字:梦境。画面上是一个熟睡了的妇人和一个熟睡了的孩子,孩子枕在那妇人的膝上。那妇人正在做梦,梦中,她用手挡住从云里飞来的一只老鹰,那老鹰衔着一个花环,显然,那妇女是不让那花环戴在孩子的头上;远处是拿破仑,他靠在一根深蓝色的圆柱上,头上顶着一个光轮,柱顶有个黄色的斗拱,上面写着:
马伦哥
奥斯特里茨
耶拿
瓦格拉姆
艾劳这些地名都是拿破仑打胜仗的地方。
那画框下面,有块长方形的木牌子似的东西,斜靠着墙,竖在地面上,像是一幅反放的画,那也可能是一块油画布,背面画坏了;也是一幅什么壁炉挂画。
那张桌子旁,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坐着,面前摊着鹅翎笔、墨水和一些纸张;那人身材瘦小,脸色死灰,神色惊恐,模样狡猾,一种冷酷而不安分的样子,一见便知是个坏透了的家伙。
拉华退尔拉华退尔(1741-1801),瑞士人,相面者,认为从人的面部结构能识别人的性格。如果对这张脸进行了研究,就会在那上面发现秃鹫和诉讼代理人的混合形象;在这张脸上,猛禽和讼棍在彼此丑化,相互补充——讼棍因猛禽而卑鄙,猛禽因讼棍而狰狞。
那人长着长长的灰色络腮胡子,穿的是一件女人的内衣,棕毛满布的胸脯和灰毛耸立的臂膀都在外面露着,下身是一条满是污垢的裤子,脚上有一双破靴子,张着大嘴,脚趾全部露了出来。
他嘴里叼着烟斗,正在吸烟。说也奇怪,穷得没有面包,但却有烟。
他正在写着什么,也许写的就是马吕斯看到的那类东西。
桌子的一角,放着一本旧书——它已不能成套,红色封面,那是昔日租书铺出租的一种12开版本的书,可能是一本小说。封面上有大字书名:《上帝,国王,荣誉和贵妇人》,杜克雷·杜米尼尔著。1814年。
那男子一面写什么,一面大声自言自语:
“我说,人即使死了也还是无平等可言!看一眼拉雪兹神甫公墓便可知晓!那些有钱的老爷们葬在高处,路的两边种有槐树,路面则铺了石块。人们驾着车可以直达。小户人家,穷人,不幸的人又会如何?他们被扔在低洼的烂污泥浆齐膝的泥坑里,水坑里。扔他们在那里,目的是让他们赶快烂掉!如果不想陷在地底下去,就别动去看看他们的念头!”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向桌上猛击一拳,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
“啊!我恨不得一口把这世界吞下去!”
一个胖女人,也许是40岁,也许是100岁,正在壁炉边,蹲在自己的光脚跟上面。
她也只穿了一件衬衫、一条针织的裙子。裙子上有多块旧呢布补丁,腰里一条粗布围裙遮去了裙子的一半。这妇人,虽然眼下叠成了一堆,但仍可以看出,她的块头儿很大。和她丈夫一比,那简直是个丈六金身。她的头发原是淡赭色,现已经半白了,显得怪且丑。即使这样,她仍时不时地伸出她那一只长着扁平指甲的大油手去梳理它。
在她身边的地上也有一本打开的书,它和桌子上那一本同样大小,也许是同一部小说的另一册。
床上坐着一个脸色灰白、又瘦又高的姑娘,几乎是赤着身子。她垂下两只脚,似乎是不在听、不在看,甚至也不在活。
马吕斯想,这可能就是刚才到他屋里来的那个姑娘的妹妹。
乍看上去,她也就是十一二岁。但仔细观察后,又觉得她足有15岁了。不错,这是昨天晚上在大路上喊“快逃,快逃,快逃”的那个姑娘。
她是那种长时间不见长,某年陡然猛长的病态孩子。这可悲的人类植物是穷困的产物。这些生物没有童年期,也没有少年期。15岁时样子像是只有12岁,16岁时又一下子像有了20岁。今天还是个小姑娘,明天却成了个妇人。那光景,是她们在超越年龄,以便生命早日结束。
这时的小生命还是一副孩子的模样。
另外,这家人没有任何劳动的迹象,没有织机,没有纺车,也没有其他任何工具。眼下,在房间的一角上倒堆放着几根废铁钎。它们的存在令人不解。总之,这个家全然是一派绝望之后和死亡之前束手待毙的惨相。
马吕斯看了一会儿,觉得这里的阴气比坟墓更为可怖,因为这里仍然有灵魂在游荡,仍然有生命在活动。
陋室,地窟,阴沟,这些穷苦人在社会建筑最低层爬行的地方,还不能完全称为坟墓,它们只能称为坟墓的前厅。富人总是把自己最最华贵的东西摆在宫室的入口处,同样,死人便把自己最最破烂的东西置于他的前厅。
那男子住了嘴,那妇人没有吭声,那姑娘像是也不再呼吸,屋子里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
那男子仍在写着什么。他一边写,一边嘟囔:
“混蛋!混蛋!统统都是混蛋!”
这倒成了所罗门警句所罗门说过:“虚荣,虚荣,统统都是虚荣。”的变体。那妇人听了叹息道:
“得了,得了,安静点吧,”她说,“别把身子气坏了,亲爱的。你给这些家伙写了信,就已很对得起他们了,我的当家的。”
穷苦,犹如严寒,它使人们身子紧靠着身子,心却离得很远。这个妇人,看样子,似乎曾经以她心中仅有的那一点情感爱过眼前的这个男子;但是,很有可能,在悲惨压得全家透不过气来的情况下,由于日常互相埋怨,结果,那种感情也就在心里熄灭了。在她心里,只剩下了一点对丈夫柔情的死灰。甜蜜的称呼还挂在嘴上:“亲爱的”、“我的当家的”,等等,但是,嘴上叫着,心里却不起什么波澜了。
七战略和战术
马吕斯感到窒息,正打算结束观察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声音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坚持下来。
原来,他听到那破屋子的门突然打开了。
大女儿进得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