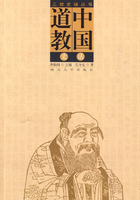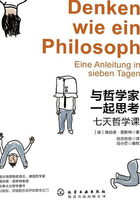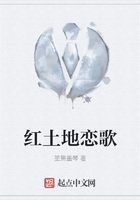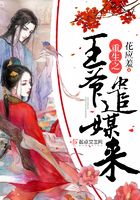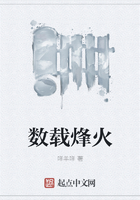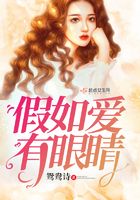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而称帝建立汉朝,公元前196年,刘邦先是消灭了异姓封王中实力最大的韩信、彭越等;公元前180年,在吕后临朝用事8年去世之后,刘邦宗族和其旧功臣,又联合剿灭了外戚封王的诸吕;到了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又平定了同姓封王的吴楚七国之乱。至此,汉朝的国家应该说是相当稳定了,度过了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在前三四十年最容易遇到的存亡瓶颈。除了上述这些相对短暂的局部战争(有的还只能说是宫廷政变),到汉武登基,国家已大致享受了一个甲子的和平。而在文景之治,尤其是清明仁厚的汉文帝在位23年(公元前180—公元前157)期间,国家基本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自奉也甚俭的黄老哲学,薄徭赋,轻刑罚,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长。
当汉武帝于16岁在公元前141年登基,此时的汉帝国已经建立近62年,从版图和国力都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到那时为止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与此前同样中央集权和强大的秦帝国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优势。秦立朝甚短,尚未形成稳定的,也能加强其合法性的“传统”,其政策又比较专持个人独裁和严酷暴力,不要说整个统治阶级的再生产,甚至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接班人也还缺少教养和章法,秦始皇本人虽然梦想着“万世一系”,但个人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长生不老”,其强大统治的根基下面其实埋伏着极大的隐忧,最后以至于“二世而亡”。
而据《汉书·食货志》,汉帝国在汉武登基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程度。汉朝建国时,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即便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所以,汉初一度实行了重农抑商,限制奢侈消费的政策,后来虽然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中都官府使用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文帝、景帝治理国家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最后以至于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乃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常被视为财富象征的马匹过去多是达官贵人之家才能拥有,而现在连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过去只有上层才能经常吃到肉,所以说国家大事是“肉食者谋”,现在连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也都是白米好肉(见《汉书·食货志》,参用《通鉴》卷16,柏杨译文)。其时世界尚未连为一体,各大文明之间基本不通消息,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和那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罗马相比也绝不逊色。这也说明即便在低技术的情况下,历代政府也都曾不仅多次解决过温饱问题,甚至达到过相当可观的社会繁荣。
但是,汉兴数十年之后也不是没有隐忧,尤其是要再往前走,还需要探出一条新路。有些问题,原来不突出的,到那时也就突出了。比如说打江山的老一代,到了那时就基本上都已去世了,这时就面临一个是任用功臣子弟补充统治阶层,即由打江山的后代一代代继续坐江山,即走向某种世袭制;还是另谋他法,实行制度创新,不论出身,务使有德有才的贤者在位的问题。还有像过去的年月,大家都比较穷,甚至连官员天子也不豪富或不怎么摆阔。社会上还没有多少财富,而现在财富急剧地增多了,就有一个相对比较和分配公平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否要无限制地追逐财富,或者采取一种完全自由放任主义的问题。尤其是讲究礼义的“周文”衰败,战国至秦一味追求功利、富强和战胜之后,官场和社会上的风俗也是功利滔滔,物欲流行,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言:“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暴秦更是使此风甚嚣尘上。直到汉兴六十余年,此风依然不衰。虽然经济大大发展了,但道德却没有振兴。比如说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通鉴》卷17,柏杨译文)
应该说,汉初一段采取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还是相当有效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传统的黄老哲学和今天现代社会的主流自由主义还颇有相通之处,但是,传统社会毕竟不同于现代社会,在传统等级制度和政教合一的社会里,黄老哲学似乎是一种过于消极无为的哲学,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治民化民。另外,再考虑到上述自“周文”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解体,战国到秦朝一直是崇尚暴力、欺诈和成功的时代,不仅上层阶级的风气,社会风俗也大大地衰败了。虽然有些风气在汉初已经有所矫正,但总的来说,由于风俗的败坏容易短期内就造成,而风俗的提升则需长期努力方能见效,通过诈力追求成功和利益的风气还是相当程度地存在。所以,从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上来说,都不能不谋求积极主动、放眼长远的重本之策。
对以上种种问题,如能清醒认识,又借助于已有的有利条件,总是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但面对成绩,人却可能容易得意和张扬,从而缺乏一种反省和正视问题的精神。我们在较早贾谊公元前173年上文帝书中已经看到这样的批评。他说,其时进言者已经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而他以为,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特别指出商鞅变法所造成的秦俗之弊害,而这种秦俗又由于秦得天下而传播开去,流风所及也一直影响到汉俗:“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汉书·贾谊传》)。在上层崇尚诈力以求最大功利,而下层也被影响而崇尚功利的情况下,过去那种“周文”影响下的亲亲和重德之风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贾谊其时已有返本开新、寻求长治久安之意,他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通鉴》卷14)。但当时紧迫的问题还是如何节制诸藩王而使中央国家政权强大而稳定。所以贾谊的上疏主要还是提出了从客观形势上弱藩的建议,而即便在这方面,最后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在这些问题严重暴露之后,在汉景帝时候晁错倡导的大力削藩。这些举措都指向了对宗族王后世袭制度的限制,但是,当时虽然有不定期的特举贤良文学,也有治一、二经的博士,官员阶层如何走出一条稳定的非世袭的制度新路还有待摸索,至于社会风俗的改良也还没有全面的举措。故此,贾谊的政治主张还只能说是“更化”的一种先声。
汉武帝登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十月,即汉立六十二年,他下诏各地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出题“问以古今治道”,对者有一百多人。其中广川儒者董仲舒后以“天人三策”著称的连续三篇对策,可以说是汉兴六十余岁“更化”之基本纲领性文献。其中第一篇主要讲秦之后的社会流弊,讲为什么必须“更化”;第二篇主要是提出了改制的两条重要举措,一是兴办太学,一是定期察举孝廉,从而使统治阶层的再生产不再世袭化,为后世两千多年的选举制度开辟了道路。第三篇主要是讲在政治统治的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价值,并限制统治阶层孜孜谋利。或者我们可以简略地说,第一篇主要讲“更化”之“因”,第二篇主要讲“更化”之“制”,第三篇主要讲“更化”之“的”,即主导的价值目标。
所谓“更化”,主要是指对秦以后制度风俗的“改弦更张”、更除秦法秦俗而化上化民。董仲舒在其第一策中,像贾谊一样,首先指斥了崇尚功利以致诈力的秦制所导致的社会风俗的败坏,这也是必须“更化”的主要原因,他说:“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董仲舒言论的引文无另注者均出此传中的“天人三策”)。而像社会不重教化,政治统治者私心独断、唯我独尊,不畏天悯人,不重视教育子弟,甚至于不重视教育太子,以及不仅民间孜孜求利,社会上层和官员也常常无视正义而求权谋利,这些也都和秦俗在社会上还有很大的影响有关。
“更化”的“更”即“更改”,尤其是指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创新;而“化”则主要指“化民”,即移风易俗。合起来或可说,即通过改制来达到“善治”,通过“善治”来达到“化民”,从而实现一个好的共同体社会。为此,政治家就不能像“俗吏”一样斤斤于琐务,只是穷于应付,而是要有长远眼光,适时提出大经大法。而又由于古人常常把这一好的社会理想置于远古,认为“三代”是理想,所以,这一“更化”又常常采取以“复古”“返本”的形式来“开新”,或者用董仲舒的话来说是“退而更化”。这不仅是大政治家需要有的从容气象和镇定开局的魄力,也是和现代“进化”大异其趣的路径。
又次,这一旨在全体的“好的社会”虽然是最终目的,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着力点却在政治、在制度,其主要的原动力也是来自少数有能力居于社会上层、掌握政治和教化的权力、引领民众的人。“化民”要靠圣人明王,但如果“化民”成功,则即便“圣王已没”,其子孙也可“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董仲舒特重圣人和圣王,以及社会上层,尤其官员和君主对民众的示范和领导作用,主张“化民”先要“化上”,这也是与他对政治的功能和对人性的看法相合的。他说:“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故君主必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董仲舒又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政府不能任由物欲和“功利滔滔”,且必须从自身做起。同时,政府也不能专任刑法,“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
强调君主的作用并不是说现在的君主就是“圣王”“明主”,下臣就只能“颂圣”。相反,这是对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而天人感应、灾异天谴的学说也主要是为了感悟甚至威慑君主,给君主的权力加上一种更高的制裁力。“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当然,“更化”并不是“革命”,不要说当时的汉朝社会还相当繁荣,政治也还算清明,就是碰到犯有严重错误以致罪行的王朝,也还不能轻言改朝换代,因为这毕竟是伤筋动骨的大事,不知要造成多少人流血丧生。如此也是知国大体,甚至也是“生生”之天心天意。所以说“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同样,强调官员的作用也并不就指要依靠现成的官员。当时的官员还多是昔日的功臣及其子弟,又有一些是靠财富入官。而对打天下的一代来说,功劳多是军功,所以,汉政一度也是“军人政治”,战争习气占主流;以财富入官者则还带来了一些“富人政治”的市井习气。然而,“马上得之焉能以马上治之”,前鉴不远,秦的速亡就是一个明显的教训。而董仲舒的理想是儒家的“士人政治”,是不拘出身贵贱、贫富而使“贤者居上位”。在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非世袭还不大可能,远古的禅让更像是对酋长部落的理想传说,而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伪“禅让”则因其虚伪之至而变得臭名昭著。但诸侯封建制的遗波经过汉初五十年的激荡则基本成为绝响。不过,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官员阶层——或者说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构成却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建立一套稳定的制度。究竟是走世袭的老路还是走非世袭的新路?直到武帝登基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根本解决。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看到了董仲舒在其第二个对策中提出的两条制度建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的第一个建议是:“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他的第二个建议是:“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这两条建议可以说是相互配合的。它们既有选才,又有育才。它们也既是政治制度、选官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化民制度。而且在推荐中又含有考试,像博士员子弟或者说以后的太学生通过考试“甲科补郎,乙科补吏”。经过坚持不懈的制度化、常规化,就慢慢改变了官员队伍的社会构成,使之许多是来自社会下层。
这两条相互配合的制度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意义的重大,在我看来,此前一直是低估了的,尤其是长期被现代学者所低估。而我认为它们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不仅本身延续了两千多年,并使中国的古代选举制度(先是推荐的察举,后是考试的科举)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制度,而且逐渐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使中国终于从一个“周文”的封建世袭社会逐渐走向了一个“汉制”的传统选举社会[6]。它们最后的确使官员世袭制成为历史的陈迹,使下层的有才华者能够和“官后代”“富后代”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上竞争,正大光明地跻身上层,源源不断地成为官员的主体。
董仲舒还在第三策中提出了“更化”之主导价值观的问题。他认为存在一种普遍和永久的天道价值,“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是垂之永久的。但是,由于时势的不同,在那些不是最基本的价值层次,又还是会有损益和改变。故视作理想的“三代”也还是有同有异,且往往是“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而汉承秦之大乱之后,就还是要有所改变,有所“更化”。为此,他在政治上主张“独尊儒术”,在社会上,他主张限制物欲利求。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种颇有“政教合一”色彩的主张的确和现代社会的主流倾向不合,但我以为这里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要是从政治统治的层面说的,即除了六艺、儒术,不让其他的学说“并进”至政治上的统治思想。而在民间社会,其他思想并不遭禁,这和秦代除了种树农艺之书一概焚毁大不同。儒术虽然后来成为政治上统治的意识形态,但它本身的性质并不是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而还是相当宽容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在政治统治的最高层,其实也是常常吸纳法家、道家的思想,杂用王霸、黄老之道的。
董仲舒第三策中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重要思想,那就是“国不专利”,官员士大夫“不与民争利”。这不仅是为了以身作则,端正统治者的道德形象,也是为了予民以利,富民生计,同时也有助于改造民众和社会的价值观,亦即如果说要淡化和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那也应当首先从上层和官员做起。他所说的“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主要是对士大夫说的,而不是对所有人说的。在国家统治者“不与民争利”方面,古人也已有所论列,而董仲舒的比较特异之处是与天人之道的相连,即他还是从天人关系方面开始论说,他说,天对各种动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而人也是这样,“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所以,他主张“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换言之,亦即你作为统治者不能什么都得,一切通吃。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力和名位,如果说还要与民争利,贪求无已,要巨富暴富,那也是太不像话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其实已含有一种让“权钱名”相对分流的价值多元论思想。
董仲舒又曾在社会经济方面建议“限民名田”,[7]防止两极分化,“以塞兼并之路”。他还是从批评秦制开始,说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又公元前131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火灾,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主父偃窃之以上奏天子。记中推说灾异天意,暗示应诛淮南王刘安及田蚡,后淮南王果反,但当时董却陷狱,后不复言灾异,一直家居,据说在公元前106年九十余岁去世。
董仲舒可以说是汉武时期“更化”的主要理论家和倡导者。《汉书·董仲舒传》言:“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发”这里应该是指“发端”,或也可以指“阐发”。从后一种意义来说,董仲舒无疑是“更化”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从前一种意义来说,或还有争议,有董仲舒之对策在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五年之说。但从其对策中的语气看,尤其是两条制度建议,说“愿”,说“使”,明显是建议的口气,也就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我想即便从制度“发端”的意义上来说,也应当主要是董仲舒之议起了主要作用。当然,当时应该说已经在朝野形成了相当的共识要推崇儒家,包括推崇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特举贤良时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此奏并得到了批准。此即在政治上去除法家、纵横家之言,但尚未涉及黄老之言。而后来代卫绾为相的魏其侯、武安侯则更为“隆儒”。
当然,关键的还是要看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态度。汉武帝为什么会重用儒家,接受董仲舒的制度建议?这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政治理念的吸引,也有实际的考虑甚至个性的原因。汉武帝自小的老师是儒家学者,是“儒门子弟中尉卫绾、王臧为太子太傅、少傅”。故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政治理念的充分熏陶,而他也喜欢文学礼仪,这也是儒家所擅长。儒家的许多礼仪如建明堂朝觐之制,也有助于加强王者之尊。而他登基之后,夹在几方面的外戚如作为太皇太后的窦氏亲戚,作为皇太后的王氏亲戚,以及旧日功臣的各种势力的争斗之间,他也希望打破世袭,引入和加强自己新进的力量。而他的确也具有雄才大略,善于识人用人(虽然也用之严苛),他也想大有作为,开创新局,包括想比较彻底解决匈奴威胁的问题。这样,过去消极无为的黄老哲学自然不能满足他的政治抱负,于是,重用儒家,主要以其思想治国也就成为他的选择。
当然,即便最高统治者支持,这一政治变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一时大有重用儒家、大兴新政之势,但在第二年,就遭到好黄老之言的太皇窦太后的力阻,“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通鉴》卷17)。当然,随着后来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渐渐长成收权,政治经验丰富而又有魄力,这些阻力也就慢慢消除了。而除了朝廷最高层,来自下面的消极怠工的阻力也多有存在。比如察举孝廉,就也遇到过整郡无人被察的情况,所以,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11月诏议二千石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举,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不过,总的说,“更化”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甚至可以说“其发端也微”,开始的一些举措并不是很引人注意,似乎只是一些原有制度的增益和补充:例如将特举变为岁举;将原有的一、二经博士正式定为五经博士并补子弟;然而,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制度,使之成为常规并不断完善,竟渐渐使整个统治阶层改变了面貌。儒学终于成为不可撼动的主导思想,选举也成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制度。所以,又可以说“其收功也巨”。虽然说任何改革其实都不会完全按照改革者的意愿进行和实现,尤其会和其理论的倡导者的理想较远。上面已经谈到汉武尊儒的“更化”的改革在建元二年就遭受挫折。但其实更大的改革变形还是来自统治者自己,即来自汉武自己,汉武曾被自己的老师汲黯直责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后来耗费民力也甚多,很能识才用才但却不怎么惜才,对其属下相当严酷,担任其宰相的官员多不能善终。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要说还是有一些制度却还是在汉武时期巩固住了,例如太学和察举。它们甚至成为基本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打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分配形式和教化的主要形式,为中国政治相当程度上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顺便谈一下观念的精英与行动的精英的不同特点和作用。董仲舒基本上还是一个学者、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却并非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他和作为政治行动领袖的汉武帝自然相当不同,和弥合政治行动与政治思想的丞相公孙弘也有所不同。我们看董仲舒早先在孝景为博士时“三年不窥于园”,晚年也“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即可得知他是一个比较精纯、能够耐得住寂寞,不受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诱惑的学者。董仲舒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对策中说自己:“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至于“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董仲舒认为自己并不能够胜任。故而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并不太被人认可。而向子歆以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则被后来笃论君子甚以为然。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精英与行动的精英之别,作为观念的精英,重要的是他要系统地形成,如果有可能,还鲜明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理论。而董仲舒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他的“天人三策”是他近六十岁时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其思想含量与公孙弘的对策一比较就可察知其要丰富深刻得多。而他这一政治对策之后还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他还有《春秋繁露》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天人之道、天人感应、天命性理的学说。所以,董仲舒仕途不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主张被相当全面和彻底地采纳和实现了。政治统治者“用其言而不用其人”这是常态,不仅董仲舒与汉武帝是如此,前面的贾谊与文帝,甚至更早的韩非与秦王的关系也是如此。思想能有这样的命运也就是幸运了。而董仲舒寿终于家,据说享年九十,不像贾谊英年早逝,更不像韩非死于秦王的狱中,就还有个人命运的幸运了。
而在中国思想理论的历史谱系中,董仲舒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学的制度一系在后世的主要发展者。孔子的儒学到战国时已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孟子,更重内圣;一支是荀子,更重外王。秦之后,开始的一千年(从汉至唐),先是制度儒学、政治儒学、外王儒学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后来的一千年(主要是宋、明),则是心性儒学、修身儒学、内圣儒学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而在前一个千年的发展中,董仲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外王制度儒学做出了最大的理论贡献。“更化”是真正的制度创新,但同时又是“返本开新”。董仲舒因此成为孔子之后制度儒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和实现者。
董仲舒的“更化”主张,在汉武帝时期基本得到了实现。自武帝以后到宣帝,一时从各种途径人才辈出,堪称“得人”。[8]这种政治及社会风俗的“更化”——首先是权力的“更化”——走向了一条反世袭的新路,这固然有思想理论的引导作用,也有社会形势的呼应。走向这样一条新路主要是来自下层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也需要有可能世袭的上层出于公心,不将用暴力夺来的权力永远视作自己的,他人不得染指,只有自己的子弟掌握才能放心的禁脔。结果也反而是这种公心和公平延续了汉祚。西汉在延续了两百多年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但最后还是由刘姓的光武帝刘秀重新执鼎,结果又有了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这长达四百多年的一姓王朝的统治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再也未曾有过,在世界上大概也是惟此一家。
而从国家的角度观察,社会统治阶层从世袭到非世袭,或许还可以说是从小国到大国、弱国到强国,甚至是从古代国家到现代国家的一个明显标志。至少,一般来说,统治阶层非世袭,是国家能力稳定持久地强大的一个要件。因为官员世袭就会有他们自己的家族利益,而不只是国家利益。这两种利益就很可能发生冲突。家族利益就可能冲击、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最后甚至颠覆国家。的确,这一对世袭制度的批评主要是从国家主义或国家能力的观点观察的,而如果从其他方面观察,比如从某些优秀文化成就、从防范极权主义的角度观察,封建世袭又不是全然负面的。甚至从政治能力的养成来说,世袭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这里更重要的还是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尤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权力世袭无疑将压制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才,引发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福山在其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中,[9]重申了这样一个不断有人指出的事实: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能力和世袭制群体之间是负相关的。世界各地的统治者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与阻碍他们的世袭倾向做斗争。因为偏爱自己家人的本能其实在人性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一有机会,世袭制度就会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复辟。[10]福山指出,为了创造一个忠实的管理阶层,有些国家甚至采取了各种破坏家庭的极端措施。像中国的一些皇帝重用宦官,因为他们不会有后人,所以常常比普通官员更受皇帝信任。还有像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发展出一种军事奴隶制,奥斯曼帝国皇帝的禁卫军士兵不许结婚,等等,甚至教会不让教士结婚也有防止世袭的倾向。福山认为,统一了中国的秦王朝显然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但它妄图建立一套近似极权主义的残暴独裁统治而终归失败。而汉朝和贵族精英之间实现了合作,并通过复兴儒家思想建立了统治的合法性。[11]
我曾尝试用“周文”与“汉制”来概括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文化传统。“周文”是封建世袭社会的制度风俗,而“汉制”则是中央集权的选举社会的制度风俗。在“周文”之后,经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激荡的过渡时期(战国至秦),在暴秦之后的汉朝,又经过了数十年的制度摸索和建设,方才真正建立了“汉制”。当然,作为后来的社会,“汉制”也继承了“周文”的一些价值理想和文化理念,同时也继承了“秦制”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但是,社会主要资源如何分配和统治阶级如何不断再生产这样一些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长久之道的主要问题,却是在汉代解决的,所以,说后世基本遵循的制度是“汉制”而非“秦制”,我想是有道理的。而我们还看到,真正具有创新意义,成为后世两千年制度的基本典范的“汉制”的建立,恰恰是在“更化”的过程,亦即更新秦制秦俗的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