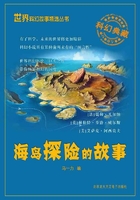下面是瑞蓓卡小姐寄往伦敦拉塞尔广场给爱米莉亚·塞德立小姐的信,由国会议员皮特·克劳利作为免资邮件发出。
我最最亲爱的爱米莉亚:
当我拿起笔来给我最好的朋友写信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同时又是多么悲哀!哦,今天和昨天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今天我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昨天我还在家里,和情胜同胞的妹妹朝夕相伴,我要永远永远在心中珍爱我的妹妹!
我不想告诉你,在和你分别后的那个悲凉之夜,我是何等伤心,流了多少眼泪。星期二你快乐逍遥去了,和你的母亲在一起,还有倾心爱你的青年军官在你身边。晚上我一直惦记着你在珀金斯家跳舞,我敢说舞会上所有的姑娘中一定数你最最漂亮。车夫约翰用一辆旧车把我拉到了皮特·克劳利爵士在伦敦的宅子,那车夫对我粗鲁至极,无礼至极(唉!欺侮不幸的穷人反正没有风险!),然后我被交给皮特爵士。我不得不在一张老古董的床上过夜,旁边还有一个阴阳怪气的老婆子,她是看守房屋的打杂工,够讨厌的。整整一宿我连一眨眼的工夫也没睡着。
我们这些傻丫头在契绥克读《塞茜丽雅》[119]的时候,曾想象准男爵必定是怎样的,皮特爵士可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很难想象有谁比他跟奥维尔勋爵[120]更不相似的了。他是个矮墩墩的老头儿,又粗俗又邋遢,衣着寒酸,还打着破旧的绑腿,抽一支讨厌的烟斗,自己用一只平底锅做难以下咽的晚餐。他说话的乡土音很重,冲着打杂老婆子和出租街车的车夫粗话连篇。我们先坐街车到客栈,再坐驿站马车从客栈出发,这次旅途的大半程我一直待在车厢外面。
天刚破晓,我就被打杂老婆子叫醒。到了客栈,我先被安置在车厢内。到了一处名为利金顿的地方,竟下起倾盆大雨来了。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不得不从车厢里出来,因为皮特爵士是驿车的车主,而中途上车的一名乘客要一个里边的座位,于是我只好到外面去淋雨,幸好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青年男士带着好多件大氅,他很客气地让我裹在他的一件大氅里避雨。
这位男士和一个押车员看来深知皮特爵士其人,对他的作为大加耻笑,两人都同意外界把他叫做“老抠门儿”,意思是贪得无厌,一钱如命。他们说谁也甭想从他那里要到一个铜子儿(我痛恨这样刻薄待人)。青年男士向我解释,最近这两站驿程我们的车走得很慢,因为皮特爵士在驭者座上,因为他是这段路的驿马主人。“可是等我接过缰绳以后,难道不会把它们一直抽到司阔什摩尔吗?”那位剑桥的年轻人说。“您就放手收拾它们吧,杰克少爷,”押车员说。原来最后一段路杰克少爷打算自己赶车,好把恶气撒在皮特爵士的马身上,我弄清楚这话的意思后,自然也笑了起来。
不过,到了离钦设克劳利镇四英里的马德伯里,一辆套着四匹骏马、挽具马衣上有纹章图案的自备车已等在那里。于是我们很风光地坐车进入准男爵的庄园。通向宅院的林荫道有一英里长,大门的柱子上方铸有一条蛇和一只鸽子,由它们托着克劳利家族的纹章。古老的镂花铁门令人想起可恶的契绥克那重校门。一个看门的女人把大门敞开,同时向我们行了好几个屈膝礼。
“这条林荫道长一英里,”皮特爵士说。“这些树的木材价值六千镑。你能说那都不值一提吗?”
他的发音很古怪,avenue(林荫道)读成evenue,nothing(不值一提)读成nothink。在马德伯里他把庄园总管霍德森先生叫到车厢里和他坐在一起,他们谈的是什么扣押和变卖财产啦、排水和翻松底土啦,很多是和佃户和耕作有关的——远远超过我能理解的程度。塞姆·迈尔斯在偷猎时被当场抓获,彼得·倍利终于进了贫民习艺所。“那是这狗×的活该!”皮特爵士道。“他和他家前几辈的人在那片农场上糊弄了我一百五十年。”我估计是某个老佃户缴不起地租。其实,皮特爵士完全能做到说话不那么粗鄙,可是有钱的准男爵们没有必要像穷家庭教师那样讲究出言吐语的礼貌规范。
马车经过时,我注意到有座雄伟挺拔的教堂尖顶耸立在庄园里好些古榆的上空。在榆树前面一片大草坪和若干附属建筑之间,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红砖房,它的高烟囱上爬满了常春藤,窗户在阳光下熠熠闪亮。
“这是不是府上的教堂,先生?”我问。
“对,该死的!”皮特爵士说,不过,亲爱的,他用的词儿要难听得多;“霍德森,比尤蒂好吗?”接着他向我解释:“亲爱的,比尤蒂就是我的牧师弟弟比尤特。我管他叫比尤蒂和比斯特[121],哈哈!”
霍德森也笑了,接着变得严肃起来,点点头说:
“恐怕他的身体确实好些了,皮特爵士。昨天他骑上他的小马出去看了我们的庄稼。”
“他关心的是他的什一税[122],该死的,”此处他用的还是那个下流的词儿。“难道对水白兰地怎么也整不死他?他的身体可真经得起折腾,简直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对,简直像玛土撒拉[123]。”
霍德森先生又笑了起来,说:
“您的两位侄少爷从大学里回来了。他们把约翰·斯克罗金斯好一顿痛打,差点儿把他打死。”
“痛打我的猎场副看守?!”皮特爵士咆哮如雷。
“当时他进入了牧师的地界,爵士,”霍德森先生说。
皮特爵士怒不可遏地赌咒道,若是他们在他的地界内偷猎让他给逮住,非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不可,他向上帝发誓。后来他又说:
“霍德森,我已经把圣职推荐权卖掉了,那两个崽子将来一个也别想从教区得到俸金,我担保。”
霍德森先生说他做得完全正确。从这番话里我可以肯定他们兄弟不和——弟兄之间往往如此,姐妹也是这样。契绥克的两位斯克拉奇利小姐就经常打架吵嘴;还有玛丽·博克斯老是打露薏莎·博克斯——你记得吗?
就在这个时候,霍德森先生见有两个男孩在林中捡枯枝,立刻奉皮特爵士之命从车厢里跳出去,带着鞭子向他们冲过去。
“给我狠狠地抽,霍德森,”准男爵吼道;“揍得他们魂灵出窍,然后把这两个小流氓带到庄上来;我要把他们送官究办,要不我就不叫皮特。”
紧接着,我们听到霍德森先生的鞭子呼呼地抽在那两个可怜的小家伙肩背上,痛得他们又哭又喊。皮特爵士见违禁者已被拿获,便驱车直抵厅堂前。
全体仆佣都在那里迎接我们,于是
亲爱的,昨晚我写到这里,被一阵猛叩我房门的响声打断了。你猜是谁?皮特·克劳利爵士头戴睡帽、身穿晨袍站在门口——竟是这样的仪表!我看到这样一位来访者,吓得往后倒退,他走过来夺去了我的蜡烛。
“蓓姬小姐,十一点以后不点蜡烛,”他说。“摸黑上床睡觉去,你这漂亮的小丫头片子,”这是他对我的称呼,“记住了,十一点钟必须上床,除非你希望我每天晚上来拿走蜡烛。”
说完,他和管家霍罗克斯先生放声笑着走开了。你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再次劳他们的大驾。白天用链条拴起来的两只大猎狗,每到天黑被放开。昨晚它们就对着月亮又吠又号闹了一整夜。
“这两条狗是娘儿俩,”皮特爵士说。“我管小的叫铁獠牙,它咬死过一个人,而且能制伏一头公牛;以前我管它的娘叫福罗拉[124],现在我给它改名汪汪,因为它已经太老,咬不了啦。嗬!嗬!”
克劳利宅院是一座难看的老式红砖楼房,高高的烟囱和山墙都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风格。楼前的一片露台两侧分别有族徽上的鸽和蛇保护,出了厅堂的门便是这片露台。哇,我亲爱的,这厅堂大得要命,而且阴气森森,想必我们熟悉的尤多尔福城堡[125]的大厅也不过如此。那里的壁炉架大得足够容纳平克顿学校一半师生员工,炉栅上至少可以烤一头整牛。四周墙上挂着不知多少代克劳利的画像:有的蓄须,脖子上围着轮状波纹领;有的头戴巨大的发套,鞋尖向外翘出;有几位女眷绷着长长的紧身衣和裙服,直挺挺的像一座座塔楼;有的垂着长长的鬈发,可是——我的天哪!——居然没有穿紧身衣。厅堂一端是宽阔的楼梯,通体由黑橡木做成,其阴森之状简直无以复加。楼梯两侧都有高大的门,门楣上方各钉着一颗牡鹿头,由此可以通向台球房、藏书室、黄色大客厅以及上午晒太阳的起居室。我估计二楼至少有二十间卧房;其中一间放着伊丽莎白女王睡过的床;今天上午我的新学生曾带领我参观所有这些美轮美奂的居室。由于老是窗户紧闭,我敢说它们给人的印象照样郁闷压抑;若是能让亮光透进去,我会在每一间屋子里看到一个鬼魂。三楼有我们的一间课堂,它的一边通我的卧房,另一边通两个女孩的卧房。然后是长子皮特先生(这里称他克劳利先生)和次子罗登·克劳利先生的屋子,每人各有好几间;后者和某人一样,也是位军官,目前在所属团内服役。这里的房间太多了。即使让拉塞尔广场所有的居民都住进来大概还有富余。
我们抵达后过了半小时,开饭的钟敲响,我和我的两名学生一起下楼去(这是两个瘦骨嶙峋、毫不起眼的小不点儿,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我是穿着你那件珍贵的薄纱连衣裙下去的(由于你把这件衣服给了我,那个可恶的丕纳太太对待我好生无礼)。我在这里将被看作家庭成员,只有举行盛大聚会的日子除外,那时两个小女孩和我就在楼上用餐。
言归正传,开饭的钟声响了,我们大家都聚集在克劳利准男爵夫人常坐的小客厅里。她是皮特爵士的续弦夫人,也是两个小姑娘的母亲。她父亲是做五金生意的,她与皮特爵士这门亲事被认为高攀了。她看上去好像曾经风姿绰约,现在她总是为红颜不再而珠泪暗弹。她苍白枯瘦,两肩高耸,显然不善于保护自己。她的继子克劳利先生也在屋子里。他穿着全套礼服,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像个殡葬承办商。他面无血色,又瘦又丑,极少开口;他两条腿很细,几乎没有胸廓,鬓脚呈干草色,头发呈麦秸色。他活脱脱就是壁炉架上方一幅画中他那已故的母亲——出身名门的格丽泽尔·宾基。
“克劳利先生,这是新来的家庭教师,”准男爵夫人走过来拉住我的一只手作介绍。“夏普小姐。”
“哦!”克劳利先生说着把头向前伸了一下,然后重又专心阅读一本有相当篇幅的小册子。
“我希望你能善待我的两个女儿,”准男爵夫人说时,她那微红的眼睛里照例噙满了泪水。
“哎哟,妈!她当然会的,”较大的一个说。我一眼就看出,我用不着害怕那个女人。
“夫人,开饭了,”一身黑服的管家说,他的白衬衫胸前镶着偌大的荷叶绉边,看上去就像厅堂墙上画中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轮状波纹领。于是,准男爵夫人扶着克劳利先生屈出的胳膊走在头里,我一边一个搀着两个学生跟在后面前往饭厅。皮特爵士已经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把银壶。他刚去过酒窖,也是一身礼服——就是说解去了他的绑腿布,两条粗壮的短腿穿上了黑色毛线长统袜。餐具柜上摆满了亮闪闪的古董器皿——有古老的酒杯(金的银的都有),有古老的浅盘和五味瓶架,就像在兰德尔和布里治的铺子里[126]。餐桌上每一件用具都是银质的,两名红头发的听差身穿鹅黄色制服侍立在餐具柜两边。
克劳利先生做了一番长长的食前祷告,皮特爵士说了“阿门”,然后菜盆上很大的银盖子被一一揭去。
“今天咱们正餐吃什么,贝特茜?”
“大概是羊肉汤吧,皮特爵士,”准男爵夫人回答。
管家煞有介事地补充道:
“Mouton aux navets[127](请按他的发音读成‘木桶搁那边’);汤是potage de mouton à l'Ecossaise[128]。配菜有pommes de terre au naturel和choufleur à l'eau[129]。”
“羊肉到底是羊肉,”准男爵说,“绝对没治的好东西。霍罗克斯,这是哪只羊的肉,你们是什么时候宰的?”
“是一只黑脸苏格兰羊,皮特爵士;我们是在星期四宰的。”
“有谁买了些去没有?”
“马德伯里的斯蒂尔拿了脊肉和两条腿,皮特爵士;不过他说上回那只羊太小,而且毛多得要命,皮特爵士。”
“您要不要来一点potage,小姐——是布伦特[130]小姐吧?”克劳利先生问我。
“那是呱呱叫的苏格兰清汤,亲爱的,”皮特爵士说,“虽然人家用的是法国名儿。”
“我认为像我那样说菜名正合上流社会的惯例,先生,”克劳利先生的口气相当傲慢。
穿鹅黄色制服的听差把羊肉汤给我们盛在汤盆里,羊肉萝卜也一起端上。接着听差拿来“对水的麦芽酒”给我们这几个姑娘斟在小酒杯里。我并不是品评麦芽酒的行家,但我可以凭良心说:我宁愿喝水。
在我们用餐的时候,皮特爵士利用这机会询问那只羊余下的肩肉等部分哪儿去了。
“想必是下人们吃掉了,”准男爵夫人恭顺地说。
“的确是这样,夫人,”霍罗克斯说,“除此以外我们在下房什么也没有吃到。”
皮特爵士纵声大笑,并继续与霍罗克斯先生交谈。
“那头肯特郡母猪下的小黑仔现在该长得肥头大耳了吧。”
“它并不像要胀破肚皮的样子,皮特爵士,”管家说的时候表情极其严肃,先是皮特爵士,其后两位小姐这一回也跟着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克劳利小姐,露梓·克劳利小姐[131],”克劳利先生说,“你的笑声令我震惊,太出格了。”
“别在意,大少爷,”准男爵说,“星期六咱们尝尝肥乳猪。约翰·霍罗克斯,星期六早晨把它给宰了。夏普小姐特别爱吃猪肉,是不是,夏普小姐?”
餐桌上的谈话我所记得的大致就是这些。食毕,下人把一壶热水放到皮特爵士前面,还有一只可以插入箱格的瓶子里盛的估计是朗姆酒。霍罗克斯先生给我和我的学生每人一小杯酒,给准男爵夫人斟了满满一杯。我们退席回到客厅里,这时她从女红抽屉里取出一件大得永远做不完的编结活儿;两位小姐用一副脏兮兮的纸牌开始玩克立别集[132]。我们四人只点一支蜡烛,但烛台却是十分精美的古董银器。在回答了准男爵夫人的寥寥数句问话后,我的消遣便是在一本布道书和饭前克劳利先生读的一本有关谷物法的小册子之间作出选择。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直到有脚步声传来。
“姑娘们,把纸牌收起来,”准男爵夫人大惊失色地说;“夏普小姐,把克劳利先生的书放下。”
我们刚刚遵命照办,克劳利先生就走进了房间。
“姑娘们,我们把昨天讨论的题目继续下去,”他说,“你们轮流着每人读一页,让你们的老师肖——肖特[133]小姐听听你们读得怎么样。”
可怜两个小女孩结结巴巴地开始拼读一篇冗长而又乏味的布道演说,那是在利物浦毕士大教堂发表的,说的是奇克索印第安部落皈依基督教的事[134]。多么有意思的一个晚上,不是吗?
十点钟,仆人被派去通知皮特爵士和合宅上下来做祷告。皮特爵士到得最早,他脸上红彤彤的,步态相当不稳;继他之后到来的是管家、穿鹅黄色制服的听差、克劳利先生的跟班、另外三名身上散发出刺鼻马厩味的仆人以及四名女佣,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衣着过于花里胡哨,她在跪下时向我投来的一瞥包含着极度的轻蔑。
克劳利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大道理之后,我们分别领到了蜡烛,然后各自就寝。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写信,不料被叩门声打断,经过情形我前面已给我最亲爱、最宝贵的爱米莉亚作了描述。
祝你晚安。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吻你!
星期六——今天清晨五点,我听到小黑猪的尖叫声。露梓和薇奥丽特昨天领我去看过它,还参观了马厩、养狗场和果园,她俩苦苦哀求正在摘果实准备上市的一名果园工人给一串温室葡萄,可是他说皮特爵士把每一串都点过数,要是给了什么人一串,他会丢掉饭碗的。两个挺可爱的小女孩在围场内逮住一匹小马,问我要不要骑;她们自己刚开始骑,让马夫看见了立刻发出可怕的詈骂过来把她们撵走。
准男爵夫人老是在打毛线。皮特爵士每到夜晚总是醉醺醺地两脚拌蒜,我猜想他是和管家霍罗克斯在一块儿厮混。克劳利先生晚上照例要朗读布道演说,上午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便是骑马上马德伯里处理郡里的事务,逢周三和周五则到司阔什摩尔去给那里的佃户宣讲教义。
代我向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拜谢请安。你那位可怜的兄长是不是从亚力潘趣引起的贵恙中恢复过来了?哦,上帝啊!哦,老天爷!男人们可得小心提防十恶不赦的潘趣酒!
永远永远属于你的
瑞蓓卡
考虑到种种因素,我认为对于拉塞尔广场我们亲爱的爱米莉亚·塞德立来说,夏普小姐与她分手实在是件好事。诚然,瑞蓓卡颇有幽默感;她刻画可怜的准男爵夫人哀叹红颜不再,描写其继子蓄有干草色鬓脚、长着麦秸色头发的那些笔墨,无疑非常传神,显示她相当了解这个世界。也许你我都会感到困惑,为何她跪着祈祷时不多思考一些正经事,却对霍罗克斯小姐的缎带发生兴趣[135]。但我敦请好心的读者不要忘记本书题为《名利场》。顾名思义,名利场是个死要面子、华而不实、人心叵测、世风愚顽的地方,那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招摇撞骗、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虽则封面上那位道德家(正是在下的准确写照)[136]在喋喋不休地大放厥词,还声称他既不穿长袍,亦不戴领箍[137],装束与听他絮叨的对象同样蠢态毕露;然而,您瞧,一个人对真情实况应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管他头上戴的是小丑的系铃帽还是教士的宽边帽。笔者既然立意实话实说,那就免不了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给抖搂出来。
我曾在那不勒斯海滨听一位以讲故事为业的同行向一群游手好闲的懒人布道。他在描述某些歹徒所干的和他编造的劣迹时,直讲得义愤填膺、激昂慷慨,致使听众无法抵挡其强大的感染力,跟着胡编乱造者一起咆哮如雷,大声咒骂向壁虚构的恶棍。当募款的帽子向在场的群众一一转过去的时候,那铜子儿乘着情绪共鸣的高潮,竟如倾盆大雨落入帽中。
另一方面,在巴黎的一些小剧场里,你们不但会听到人们吼叫“啊,坏蛋!啊,恶魔!”以及包厢观众诅咒剧中暴君恶霸的骂声,甚至演员本人也会断然拒绝出演坏蛋,诸如可恶的英国佬和残暴的哥萨克等辈;宁可少拿一些报酬扮演忠贞的法国人一类贴近本来面目的角色。我把以上两种情形加以对比,好让诸君看到,笔者揭露和鞭挞恶人并非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因为我打心眼里痛恨这些人而又遏制不住憎恶之情,结果必然发为适当的谴责和臭骂。
所以我要提请对我“怀着善意的朋友们”注意,我打算讲一个关于坏事和罪行的故事,坏事令人恼恨,罪行则错综复杂,但我相信能扣人心弦。我敢担保,我笔下的坏人并不是一些窝囊废。写到适当的场合,我不会吝惜浓墨重彩——不,决不!但眼下笔者正写到恬静宁谧的乡居生活,不得不保持平和冲淡的气氛。在倒残茶的水盆里表现疾风骤雨、惊涛裂岸,岂不荒唐可笑?这种场面还是保留到浩瀚的汪洋和凄凉的子夜为好。目前这一章的基调非常温和。下面的章节么……这是后话,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
在笔者带领一个个人物登场的时候,请允许我以人类一员的身份,以同类兄弟的身份,不仅仅把他们介绍给你们了事,偶尔还要从台上走下来对他们议论一番:如果他们仁厚善良,我就夸他们几句,跟他们握握手;倘使他们傻里吧唧,那就附在读者耳朵旁边悄悄调侃他们;假若他们奸刁狠毒,我会用最激烈的言词谴责他们,当然以不失体统为度。
要不然你们会以为是我在嘲弄虔诚笃信的行为,其实是夏普小姐觉得这种现象十分可笑;你们会以为是我在拿准男爵开心,说他两脚拌蒜像个酒仙,其实如此贫嘴薄舌的那个姑娘除了崇拜财富对什么都没有敬意,除了仰慕成功简直目空一切。这样的人却在世上活得优哉游哉——他们既没有信仰,又不可救药,更缺乏仁爱之心。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竭尽全力向这等人开火。另有些同样大走鸿运的人,其实不过是江湖骗子和草包蠢货,跟那帮家伙斗争并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疑正是嬉笑怒骂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