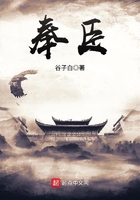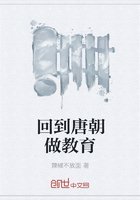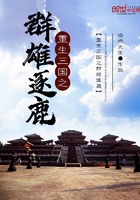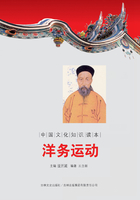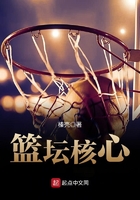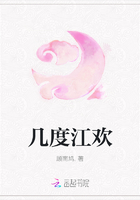“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8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1789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1815年的法国,已被波拿巴主义压制了15年,并业已听任欧洲列强支配,却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一没有首领、没有政治局、没有常委会的运动若有似无,但又无法根除。它的组成人员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但有时亦可能成为专职政治家。这些人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第一帝国【10】是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紧张准备之夜。在这些文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此,因为专制者并不缺乏那些讨人喜欢但毫无价值的玩意,用以确保文人俯首帖耳。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人采取一种被视为审慎的方式,而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与邦雅曼·贡斯当之类的人物则为此被迫流亡……自由的捍卫者在这样一种时刻,如同在战场上运气出现逆转,在拿破仑的历程行将结束之际恢复了力量。我们的叙述即从“雄鹰王的翱翔”【11】,也就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以及在滑铁卢“令人沮丧的搁浅”前重新令欧洲颤抖的“百日”开始。
众所周知,复辟王朝【12】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作为“复仇”化身的极端保皇派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补发被迫流亡期间的年金。但是,路易十八的登基并非旧制度的简单恢复。法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民事平等重新受到质疑。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王权的限制,已作为宪政标志写入由路易十八“赐予”人民的宪章之中。该宪章保障法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即便天主教重新成为国教)以及表达自由(“只要不违反必须对滥用这一自由予以制止的法律,凡法国人均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的见解”)。此外,《宪章》允诺国民的代表制,虽然这种代表制是一种极为受限的纳税选举制——根据这一严格的纳税选举制,只有几万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可以在更为有限的够格者当中选定议员——但它依然是与旧制度相异的重要区别。从此以后,选举将使公共生活具有节律。一个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把一种英国特色添加到了整体之中,并维持了一种与得到确认的平等相抗衡的贵族制习俗,但是,贵族院仍是另一个任由人们提出抗议的论坛。
尽管制度安排很好地做出妥协,复辟王朝却未能维持必不可少的对自由主义的让步和在王朝秩序、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平衡。数年之后,复辟王朝变得强硬。1824年,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成了“王位与祭坛结盟”制度的化身。自由主义运动在很晚的时候才形成,并与极端保皇派政府唇枪舌剑。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甚至夏多布里昂,皆用自己的方式充当了《宪章》所允诺的言论自由的代言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标志。由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发起的反对政府企图控制报刊的斗争,不久即有摆脱了天主教和王权主义起源束缚的浪漫派作家加入,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无法阻挡的请愿的基础上,查理十世的统治趋于崩溃:由“邪恶的敕令”诱发的1830年革命,首先显得像是旨在反对当局对表达自由的审查。被废黜的查理十世的出逃,使“自由之神”这座稍后时期出自奥古斯特·杜蒙之手,并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纪念柱顶端的不朽之作臻于完善。
1830年7月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荣三日”当然并非仅仅是记者和作家的杰作。德拉克洛瓦在其涉及1830年革命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以一个街垒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阶级的融合。目不识丁者有力支持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是,这些最为缺乏自由的人曾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势必有助于而不是有悖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正是在七月王朝为期18年的统治期间,社会主义获得了它的名字和封册:大量学说、抨击性短文、乌托邦以及某些组织的雏形,向自由派人士提出新的挑战。后者直至那时还在为反对“旧的蒙昧观念”(雨果语)而斗争;自那以后,他们将被一股因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壮大的年轻力量所否定。不过,社会主义以它的方式恢复了权威原则:为了改变生活,给弱者以希望,解放被压迫者,它要求限制、组织和镇压。直至那时,仍作为进步媒介的自由主义变得令人生疑。共和派枉费心机地调和自由、平等、博爱,蒲鲁东的著作则在徒劳地宣示自由与社会主义重归于好:从此以后,在文学界与政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矛盾。
1848年革命似乎在“抒情诗般的幻觉”的最初时光,通过建立共和国解决问题。起义者在街垒上讴歌阶级调和的美德,神职人员为遍布全国的“自由之树”祈福,临时政府的首脑拉马丁让那些赞成使用红旗的人接受三色旗,普遍选举得到确立,人们宣布劳动权,解放殖民地的奴隶……唉!6月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工人的造反与当局对他们的镇压,使得幻觉最终灰飞烟灭,自由与博爱的婚礼被无限期推迟。维克多·雨果在1848年11月失望地写道:“不,你没有伟大神圣的共和国!亦即人们所期待、福音书所展现的共和国。”
11月极为令人失望!但最为糟糕的事情发生于12月。1851年12月2日,亲王-总统【13】公开以武力埋葬共和主义最后的自由。时隔一年,他又重建帝国。凡此种种,皆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并有普遍选举的保障。人们对此所进行的抵抗虚弱乏力,经常采用的形式是流亡,这对于仍然不肯妥协的维克多·雨果和埃德加·基内来说尤其如此。拿破仑三世把他的专制制度根植于新型的王位和祭坛的结盟之上。波拿巴主义政权知道法国天主教会的力量和天主教徒选票的分量,以及从古老信仰中得到明显保护的好处。自由派天主教徒在这个教会内部几乎无足轻重,该教会用教会法中宣判、禁止宗教活动的命令以及对自由主义和近代世界的绝对谴责来回应每一次威胁。但是,杜伊勒里宫和圣彼得大教堂之间订立的协约由于民族运动而中止,该运动使得皇帝支持的意大利人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与教皇国统一。这一取消协约的行为导致正在寻求新的拥护和支持的第二帝国实行自由化。
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一种面向精神与政治生活的内部变革开始了。虽然欧内斯特·勒南还因一部具有异端思想的《耶稣传》引起纷纷议论,但是,报刊检查的钳制在松动,报刊在逐渐变得自由,以至于工人也无视司法追究组织运动。自由的声音在加强。这种声音既来自雨果和基内等流亡者,亦来自法国国内从低调的普雷沃-帕拉多尔到富有煽动性的罗什福尔等人物。
1870年,普法战争突然中断了波拿巴主义在某些人看来不可逆地转向自由主义的倾向。帝国倾覆、巴黎受到围困、宣布共和之后法国军队失败、君主派在1871年2月8日选举中获胜,凡此种种,最终导致巴黎这座以“自由之城”自居的城市相继与偏安于波尔多、凡尔赛的“乡村”国民议会分庭抗礼,爆发起义。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由狂热的希望、牺牲的行为与杂乱的狂欢组成的72天,本身即贯穿着自由或专制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以蒲鲁东式的腔调向法国各个市镇发出的公告,被打上联邦制与自治的标记。但是,实际上,雅各宾主义的遗产、恐怖统治的迷惑力、人质法令的通过,乃至救国委员会的追随者以及“反对专制”的战士,共同在凡尔赛军队的枪炮之下死于非命。在这一“凶年”期间,作家统统活跃在第一线,突发的爱国主义展露无遗。他们有的对巴黎公社社员表示愤慨,有的充当起义者(如儒勒·瓦莱斯),或向失败者敞开家门(如雨果)。理想的社会与普世主义的共和国,在成为“公爵们的共和国”之前,让位给了“梯也尔先生的共和国”。
旧制度的幽灵再一次萦绕国民议会与整个国家。共和国通过一次又一次投票和战斗,把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争取到自己这边之后,才在19世纪70年代末被人们接受。这一真正得到确立的共和制在当时堪称最为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投票批准针对被判刑的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法,以及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离婚的法律,等等。法国为法治和自由的国家树立了榜样,然而,法兰西社会自身并未得到和解。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不得不面对两大敌人,即过去的敌人与未来的敌人。的确,拥护反革命的人已被打败,但是,他们对长久以来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影响力还不容小视。风格显著的反动分子巴尔贝·道尔维利在此表现得比年老的弗约更有才华。新政权不得不考虑教士及其追随者对自己长期的敌视。下述双方之间的内战并没有结束:一方是梦想以天主教信条统一法国的“基督教十字军的参加者”;另一方是希望把共和国建立在将天国个人化(la privatization du Ciel)基础上的信仰新教的共和派、自由思想家和实证主义者。
在19世纪,宗教问题在所有冲突以及所有哲学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中皆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上帝已死的世纪”和“科学的世纪”,19世纪仍对神性抱有未被满足的怀念(这种怀念刚一产生就被对理性的期盼耗尽)。宗教不仅仅是对世界及其终结的一种解答、对受到死神召唤者的一种慰藉,也是集体认同与统一准则最为坚实的基础。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基督教的种种基础,但没用一种能使法国这一历史共同体(la communauté historique)黏合起来的信条(对于精神)和虔诚(对于心灵)的基础来取代它们。无论何时,19世纪的作家皆面临这一问题。也许,没有哪个时期在宗教上有如此丰富的设计:如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勒鲁或孔德的人道教(religion de l'Humanité)、乔治·桑的新基督教、拉马丁的新天主教、最初的社会主义含蓄的宗教感情(包括被耶稣形象所纠缠的反对有神论的蒲鲁东),更遑论对秘术(l'occultisme)毫不掩饰的传播——维克多·雨果等人一边痛斥教权派,一边却也热衷于秘术。
我们把这一叙述的终点确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举行之际。实际上,正是这一压轴戏象征着自由的实现。作为共和派大事年表中最重要的时期,这场为第二帝国的流放者、共和国的颂扬者以及“人类的诗人”举行的国葬,是使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生活愿望的非同寻常的世俗仪式之一。送葬行列的目的地——先贤祠使人想到法国人的宗教解放:雨果此前曾明确坚持要举行非宗教的葬仪。人们可能把这一事件解读为大革命在爆发近一个世纪之后大功告成。诚然,后来还应当对这一幻觉稍作纠正,但在当时,雨果似乎可以安息:这位年迈的斗士已被奉为“共和国之父”。
19世纪的自由史可以用不同方式、多种情节来构思,借用保罗·韦纳的表述“与小说一样,历史得挑选、简化、组织……”,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écrivains)与写作者(écrivant)——后两者依据罗兰·巴特的区别——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其他人可能会更重视维尼或奈瓦尔,我们则更关注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因而,文学上的等级丝毫不会左右我们的叙述:如果说贝朗瑞的作品是“死后声名大跌”(朱利安·格拉克语)的经典之作,比缪塞得到了更好的对待,那得归功于他对舆论的影响力,而不是写作才能。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承担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下述人士或多或少成功践行了同一原则: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博纳尔、库里埃、巴尔扎克、拉马丁、贝朗瑞、勃朗、比歇、卡贝、雨果、基内、托克维尔、拉默内、拉科代尔、米什莱、圣勃夫、梅里美、勒南、蒲鲁东、勒鲁、巴师夏、欧仁·苏、普雷沃-帕拉多尔、罗什福尔、瓦莱斯,等等。他们昭示信仰,进行宣传,参加宴会运动,彰显其在选票箱面前裁决的尊严,占据议席,质询与加入政府,藐视大众:推动他们更为努力的不是抱负(就此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失意而非得意),而是一种内在的声音、服务的意愿,以及拟态的(mimétique)引导、领导与指导愿望。
妇女当时仍无法期望得到选举权。她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更加令人惊讶,或许远甚于20世纪。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乔治·桑、弗洛拉·特里斯坦、玛丽·达古尔(达尼埃尔·斯特恩)、让尼·埃里库尔、波利娜·罗兰、路易丝·米歇尔、塞维里娜,等等,诸多妇女无视法律约束、社会谴责及讽刺或其挚友要她们谨慎行事的忠告,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政治斗争。当然,利害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将自由主义者斯塔尔夫人——启蒙运动和内克男爵的女儿,与积极的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这位巴黎公社社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但是,这种女性的出场依然在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中时时可见。
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学家、政论作者或讽刺歌谣作者曾三次直奔广场,参与事件并试图对事件施加影响。由此,划分情节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二月革命”(1848)和“凶年”(1870—1871)。19世纪的这三大政治危机也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时刻。作家、文人、艺术家在这期间,在议会讲坛或市政厅这些巴黎长久的革命圣殿的窗台上起了积极和中心的作用。通过始终从政治叙事角度出发,我们业已在我们看来最有意义的环节展现他们。这也向那些对我们做法感到惊讶的人说明了,何以未让巴尔扎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没什么名气的《巴黎评论》时出场——该杂志直接显示了他的正统主义倾向。
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等等,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窃以为讲述上面的一切并不会贬低他们,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心思不定、优柔寡断的生活态度与严谨的思想、大气的文笔形成鲜明反差的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的大变身呢?或者又该如何理解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呢?这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出于对克洛蒂尔德·德·沃神秘的爱,最终发明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1922年,莱昂·都德——阿尔方斯·都德的儿子、夏尔·莫拉斯的战友、“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借用昂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说过但后者不予认同的一句话,即“愚蠢的19世纪”作为标题。他的抨击被莫拉斯纳入已被付诸实践的反革命思想的基本方针。数目不下于22条的起诉要点使19世纪不堪重负,此外还有同样多他意欲表明的老生常谈和已被接受的观念。某些法国右派,即始终准备充满激情地反对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人,为这些指责喝彩。他们认为,由于与天主教和君主制传统、古典文化、秩序和良知一刀两断,这一“愚蠢的世纪”(而且对于反犹主义分子来说还是个“犹太人的世纪”)已经使法国陷入衰颓。所有的论证均旨在重复马蒂格的老师反复唠叨的事情,即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反复谈论的事情:必不可少的复辟(“在10年内,也许是在5年内,法国要么实行君主制,要么完蛋……”)。
如今,19世纪成了其他指控的枪靶,同时被讥笑为“郝麦【14】先生的世纪”(进步主义的蠢事)以及(迷信的招魂术使用的)“灵桌的世纪”。一个死板的、夸张的、蒲鲁东式的、“黄道的-社会主义的”(菲利普·缪莱语)、沙文主义、幼稚、“唉!雨果的”[1](安德烈·纪德语)……世纪。人们时下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经掩盖了集体期待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遗产、救世主降临说的乌托邦、美妙之城的允诺、必要的出逃路线和历史感。确实,19世纪充斥着上述一切。然而,对人类本性并不抱有夸大幻想的本书作者却无意掩饰自己对书中涉及的男男女女的敬佩,他们坚信以自由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与集体终会到来。从夏多布里昂、贡斯当的抨击性文章到举行起义的里昂丝绸工人的口号“要么劳动而生,要么战斗而死”,从里昂丝绸工人的歌声到根西岛流放者雨果的《惩罚集》,从雨果到瓦莱斯(两人均逝世于1885年),当思想似乎不再与历史亦步亦趋之际,那对自由的热爱便具有与日常生硬言辞——此种言辞是为了使日常事务运转流畅——不同的声音。
这并非一部依照某人提议来感化人,主角们作为和平天使将圣火代代相传的史诗。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