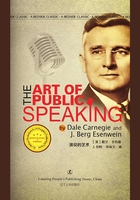漠月
这时,奇异的景象出现了,那两个草垛在水面上漂浮着,轻轻地打着旋儿,缓缓地往水的中央聚拢。后来,那两个草垛紧紧地靠在一起,顺水而下……
说是湖,其实并无水,那种大水汤汤的情景便不再存在。湖道,周围的牧人都这么叫,却是由来已久。旱的时候居多,等到进入秋季,才有难得的几场雨,湖道里就开始湿润起来,草根紧接着活了,茵茵的青绿泛开,然后就是连片的芦草。草深的地方,能齐了人的腰,一群羊走进去,霎时不见了踪影,倒像是草把羊给吃掉了。
草是命根子。
在沙漠牧区,这样的湖道并不多见。靠天放牧,逐草而居,牧人便将湖道看得珍重。只要有草在秋天的湖道里荡漾,牲畜度过寒冷漫长的冬春不愁温饱,牧人的日子就能过得很消闲。湖道好比是城里人开办的银行,那一排排随风涌动的草就是大票子。这真是上苍恩赐的,说是天上掉下来的芝麻烧饼也不为错。牧人就依傍着这湖道,活了一生一世。
八月将尽,天高云淡。湖道里的草开始泛黄,一天脱去一层绿。秋风中浮荡的草一波一折,花白的芦穗本是昂扬着的,这时也变得谦和,不停地点头哈腰。草香四处飘溢,醉透了一道道沙梁。眼下的这个湖道,按居住习惯就近划给了相邻的两家牧人。两家牧人恪守着古老的传统,谁也不会偷着去先动一根草。谁若先动了,一根草就会把这个人压得一生都翻不起身,一根草有如此巨大的重量,城里人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其实,这两家牧人早就等急了,把镰刀都磨过好几遍了。终于,天上传来一声“嘎咕”。大雁是在夜间飞过湖道上空的,这一声“嘎咕”,让牧人彻夜不眠。第二天,湖道的东西两头悄然地支起了两顶帐篷,又悄然地升起两缕炊烟。
正午的时候,阳光无遮无拦地照射着草浪中的两张脊背。两张脊背让稠密的草浪隔开,一起一伏的,晃动得很有节奏。草香里混合着人身上的汗味,渐渐地浓酽起来。两边的打草人虽离得远,却是头顶着头,乍一看就像两只在草浪里潜行的野兽,正蓄意地接近对方。两边的打草人还没搭过一句话,只听见“刷刷刷”,镰刀飞舞,阳光在刀刃上刺眼地一闪又一闪,挟起阵阵灼热扎进草浪里。镰刀很烫,刀刃扎进草根的瞬间,草被烫疼了似的剧烈颤抖。只要一开割,一切都变得单纯了,打草人眼里就剩下齐刷刷硬扎扎的草。都抢着多出草,便心照不宣地展开竞争,暗暗地攒着劲,屁股后面像有一群狼追赶着。两股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坚韧。
他们打掉了几个档子又宽又稠的草。大片的草根在湖道里挺立着,人的秃脑袋一样坦露出青湛湛的头皮,还有无数被踩死或让镰刀拦腰斩断的蚂蚱之类的草虫儿。湖道里开始一片狼藉。再接下去,两个打草人实力上的差异就显现了出来。湖道里的两个草垛,都在一日高过一日,却分明是东边的那个大出许多,西边的那个小下许多。说得难听一些,西边的那个草垛像个鸡窝。一大一小两个草垛自然是沉默着的,它们不能垛到一起去,如果能够垛到一起去,就很巍峨了,会像一座山头那样雄踞在湖道里。它们不能垛到一起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秋日渐短。每逢夕阳西下,湖道里一片幽暗。巨大的阴影水般漫漶而至,遮蔽了支起的沙梁之上的两顶帐篷,如果没有炊烟升起,可以将它们想象成两颗没有任何生命信息的石头。那两个草垛反倒在朦胧的夜色里变得温馨,仿佛两只栖息安睡的鸟,夜的秋风拂过,草梢子像鸟的羽毛在轻柔地波动。
东边的帐篷里,亮子咕咚咕咚灌下早就凉好的一壶茶水,肺腑立时通透清爽,没去了多半的疲累,从头到脚都很舒坦。亮子一声叫唤:娶了个……娶了个啥?后面的词颓然地噎了回去,扭头四处张望,竟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进湖道半个月不曾说过话,这可嗓子一声喊,把自己着实吓了一跳。人要是这么长久地不说话,没准就变成哑巴了,亮子这样想。西边的那顶帐篷里悄无声息,没有升起晚炊的烟火,真的跟石头一样。往日这时辰,那边早已燃起一堆火,帐篷像个灯笼透着光亮。亮子也没了做饭的心思,躺到羊毛毡上点了烟抽,心里仍旧乱哄哄的无法入睡。翻腾了一阵后,亮子光着膀子和脚板走出帐篷,晚间的沙地柔软中透出一丝温热,搓得脚板酥痒,宛若一只小手儿轻轻地抠着。亮子又忍不住瞄那西边的帐篷。那顶帐篷很旧了,有烟熏过的黑渍,有雨水淋下的黄斑,还缀着几块刺眼的补丁,大白天看上去,像是一颗有毒的花蘑菇。罗罗还没有走出湖道。罗罗起早贪黑,为的是让自家的草垛更大些。可罗罗是个女子,力气总是有限,十天八天还行,时间一长就跟不上趟了,怎能比得过亮子呢?亮子想,罗罗你能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那才叫日怪呢。你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我就没脸了。黑暗中,亮子自信地背着手,不出声地笑一笑。他不明白自己咋就没了睡意,打了一天的草,腰杆子仍硬着。亮子往湖道走去,他想乘着这股心劲儿,把天黑前割倒的草码到草垛上去。这样的草垛到了冬天也会绿着,羊吃了肯上膘,不比那娇贵得让人伺候的高粱和包谷差。羊就该吃这样的草,而不是吃那高粱和包谷,草才是羊的粮食。
不知不觉,亮子两只瓷实的脚板踏过草根,离罗罗很近了。亮子越过自己的那个大草垛,他把码草的事给忘了。“刷刷”的打草声和罗罗的喘气声,在夜幕下响得异常清晰,终于把亮子牵扯了过去。亮子像是无法抗拒,只有乖乖地走。夜还不是很深很黑,虚弱的星光在罗罗的镰刀上摇曳,像一滴一滴的水。星光下的镰刀是冰冷的,裹一层幽幽的寒气。亮子离罗罗很近了,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站住,把几束坚硬的草根踏进了沙地里,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亮子就居高临下地看着罗罗。罗罗弯着腰,屁股撅得老高,像一只母羊吭哧吭哧地嚼着眼前的草,饿极了的模样。罗罗身上的汗褂儿滑脱了,一大截皮肉露在背处,浑圆而饱满,这是一个女子熟透了的腰条。那腰条儿真是很白,白花花地闪着亮,褪去皮的锁阳一般,水光四射,柔嫩而新鲜。亮子就被狠狠地蜇了一下,眼前恍惚着一片雾似的,整个人都晃了几晃。
哦。亮子舌根颤一下,算是打过招呼。
罗罗没有应声,头都不抬。罗罗知道是谁,却照例操作着,镰刀深深地扎向草根。刀刃触到草的那一声响,一点都不清脆,亮子就知道镰刀钝了,不能游刃有余。被摁倒的草像受到惊吓的马一样猛地竖起鬃毛,直扫罗罗的脸面。有几根草和一撮头发纠缠起来,弄得罗罗很狼狈。罗罗的汗气很重,一股一股地弥散,像母羊身上发出的味道。亮子就暗暗地嗅着,沉迷地在罗罗面前站立很久。
你,还不睡么?亮子直通通地问。
亮子问罢又后悔了。平日里见面都不说一句话,这么突兀地问算怎么回事?没有道理的。罗罗果然还是不理不睬,就像亮子只是一个缥缈的影子。亮子自觉脸上发热,让谁凭空扇了耳光一般。亮子的意思是,夜里的湖道湿气太重,夜里打草容易落下病根,女人更不该。罗罗你是女人。这种话又不能说得很明白,亮子说不出口,就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心却一揪一揪的。
罗罗这时才直起腰,胸脯哗地一抖闪过脸去,看都不看亮子一眼,握着镰刀走了。罗罗的身后是稀稀拉拉一溜割倒的草。大部分草仍然挺立着,它们很轻松地躲过了镰刀,亮子觉得这些草都附了灵性,以某种嘲弄的姿态在夜风中倨傲地摇摆。罗罗走出草湖又走上沙梁,握着镰刀的样子像是端着一杆猎枪。亮子的目光曲折地穿透着夜色追随罗罗,直到罗罗的身影消失在西边的帐篷里。
亮子垂下头,长长地叹一口气。
亮子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四叉八蹬地躺倒,心里愈加不能平静。罗罗还在眼前晃动,罗罗那晃动的模样让他颠三倒四地回想许多事情。两家相距不过两里地,之间只隔一道枯水沟,共用一口水井。还有那一条小路,更像一根绳子连系着两座黄泥小屋。亮子和罗罗自小就很亲近,童年和少年时光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玩“丢羊拐儿”或结伴出去挖锁阳。那时候的亮子和罗罗虽不懂得人间烟火,从大人们的说笑中,却能断续地听见两家要对亲家的话。等他们长大后,亮子就娶罗罗做媳妇。亮子和罗罗由此而产生了少年最初的羞涩和隐约的幸福感。在那样一段日子里,他们都渴望自己能够尽快地长大。
却又出了那样的一件事。亮子十六岁那年,罗罗爹死了,据说与亮子爹有关。亮子爹是生产队长。那年冬天天气奇冷,亮子爹派罗罗爹到湖道里守草垛。罗罗爹人很老实,偏偏好酒,一场暴风雪掀翻毡房,罗罗爹酒醉不醒,一夜之间便冻僵了,硬得能当根拴马桩。罗罗家少个顶门立户的男人,寡母孤女的日子就开始滑坡,跟羊吃了醉马草一样,一天天地枯瘦,只剩下骨头架子。罗罗娘还年轻又有几分姿色,是生产队里少见的美人。轻薄的男人们寻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在罗罗家进出得频繁,门前的桩墩子上经常拴着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骟驼。罗罗娘刚开始还拒绝着这些男人们,时间一长便也顺水推舟,不仅学会了喝酒抽烟,还敢留男人在屋里过夜。狐狸精,亮子娘愤愤地骂,恨不得撕下罗罗娘身上的一块肉。起初,亮子觉得娘不该这样,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可是,娘每咬牙切齿地骂一次,爹那脸面上就有一片灰白。接下来亮子才明白,娘把罗罗娘和自己的爹裹在一起给骂了,而且骂得理直气壮。罗罗爹死后,亮子爹总想周济一下罗罗家,每逢杀了羊,不忘提一条羊后腿送过去。后来,亮子爹竟也和那些轻薄的男人一样,睡在了罗罗家的炕头上,半夜里让亮子娘扯着裤带牵牲口般牵了回来。时隔不久,亮子爹的生产队长就被撸掉了。这事风传许久,成了牧人们酒余肉后的笑谈,说亮子爹精明半世,糊涂一时,啃一口窝边草,好端端把一个生产队长搭进去。另外的一说是,亮子爹原本就没安好心,假公济私让罗罗爹去湖道里送命,自己好占了那个窝,窝没占着,反惹一身臊气。亮子爹羞愧难当,曾真心实意地上吊死过一回,又让亮子娘给救了,却再也抬不起头来。
从此两家断了来往。
亮子娘还自作主张,雇人重新打了一口井。
日子默默流淌。湖道里的草青了黄,黄了青。罗罗家屋前那个桩墩子一天天歪斜,再不见有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骟驼拴在上面。那个桩墩子后来让罗罗拿斧头劈了,当柴禾烧成了灰。罗罗家终于门可罗雀,清净得像一座破庙。
“狗日的男人,杂种。”
罗罗娘衰老得不像样子,整日靠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打喷嚏,口水扯成一道明亮的细线滴进脚前的酒碗里。口水和酒是一样的颜色,碗里分不清哪儿是酒哪儿是口水。碗里空了,再添上;添上,又空了。罗罗娘已经离不开酒,如同草是牧人的命根子,酒成了罗罗娘的命根子。罗罗娘的眼里再没了草,也没了羊,甚至没了女儿罗罗,只有酒。罗罗娘全部的世界是酒和口水这种无色透明的液体。为了让娘能够活下去,罗罗就要想办法把酒赊回来。大队部办有代销店,店里有成桶的酒。罗罗用不了十天就得走一趟大队部,背回家一鳖子酒。水鳖子成了酒鳖子。酒鳖子口小肚儿大,边上恰有四个穿绳子的扣,像极了鳖的四只短腿。罗罗就背着这样一个盛满酒的“鳖”,趔趄着穿行在起伏不定的那条小路上,像一个摇摇晃晃的酒鬼。酒鳖子的盖儿不很严密,浓郁的酒香播撒一路。罗罗娘的脸面黑里透红,骂过了大笑不止,笑过后接着再骂,让自己的口水淹死天底下的男人。罗罗得空闲下来就站在娘旁边,两眼红肿。亮子远远地从旁边经过,脚步匆匆,不敢多看一眼。如果亮子经过时稍有迟疑,站在屋顶上的娘便要大呼大叫,那声音像带刺的狼牙棒在虚幻的空气中飞舞,惹得滩里吃草的羊都抬起头来凝神谛听,防备着什么似的。罗罗像夏秋时节漫滩黄灿灿的野谷穗儿。罗罗是一棵黄灿灿的野谷穗儿,亮子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亮子又忍不住要多看一眼罗罗。罗罗的衣裳上又打了一块补丁。补丁很醒目,所以亮子一眼就看见了,心里被一块硬物猛地撞了一下。亮子觉出了一种疼痛,就背过身去匆匆离去,脊背上凉飕飕的。沙漠牧区的女子都要早说下婆家,此俗绵绵相传至今不改。罗罗还没说下婆家,她要像个男人一样操持生活,为娘赊来满鳖子的酒。罗罗要让娘活下去,就不能很早地说下婆家。罗罗已经放出口风,她这辈子不想嫁人,要看着娘喝酒晒太阳……
湖道里的夜很深了,深得很透彻,透彻得让满天星星一片繁忙。繁星笼罩着湖道。芦草都拔完了穗儿,也播下了新的种子,它们像无数的男人和女人拥挤在一起。草没有思想,可草是好东西。草不争风吃醋,草不当婊子也不做嫖客。草和草永远都在和平相处,彼此没有嫉恨和仇视。躺在帐篷里的亮子睡不着,他倾听着湖道里的草的呢喃,就想了这么多,终于很认真地想到了草。原来他没有这样想过,现在这样想了。草使亮子的心境变得平和沉静,同时也给了他一些启示。亮子就想抽烟,暗中摸索好一阵子,才找到烟和火柴。刚把一根火柴划亮,有个黑东西穿过帐篷带起一股冷风,将火柴扑灭了,接着又是几声瘆人的怪叫。亮子吓得头皮发麻,毛发一根根竖立起来,脑子里突然闪出罗罗爹活着时候的模样。罗罗爹就是死在这个湖道里的,那年冬天,好大的一场雪。亮子扔掉烟和火柴,扯过被子裹住自己,大气不敢出。湖道里起了夜风,时紧时慢地掠过沙梁,吹得帐篷“噗噗”直响,像一个无礼的人摇撼着手里的扇子,吐着口水。
两个草垛差不多一样大小了。
亮子干一阵歇一阵,坐在草捆子上打着盹儿,眼皮子却在忽悠忽悠地动,他睡不着。有时候嘬起嘴巴打几声口哨,眯了眼瞧对面的罗罗。罗罗毫无反应,自顾低头打草。罗罗换了一把镰刀,割过去的草根齐刷刷的,很干净。罗罗把镰刀挥舞得得心应手,草就一排排地躺在罗罗身后,有几十个草捆子了,像一群羊分散地卧着,很慵倦的样子。亮子很想和罗罗说说话,却又不敢走到近前去。亮子心想,罗罗你是个木头疙瘩么?我若是甩开膀子大干,能由得你多打草?湖道里就长下这些草,我亮子要是不让着你罗罗,你的草垛可真要变成个鸡窝。
这般的几日过去,两个草垛果真一样大,像骆驼背上等量齐观的两个驼峰。
亮子悄然地笑了。
再往后的情形又变了,亮子坐下,罗罗也坐下,等到亮子起身去打草,罗罗也摸起镰刀。罗罗的心里豁亮着,她不愿把自己的草垛弄得比亮子的还大,她知道自己的草垛应该大到什么程度。罗罗不稀罕旁人的施舍,她只要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罗罗让亮子感觉到了这一点。罗罗的沉默与坚韧震动了亮子,亮子就无奈了起来,暗暗地羞惭了起来,他觉得罗罗将他打倒了,而且不动声色。亮子突然失去了自信,就“恨”起罗罗了,心里很不好受。亮子索性扔掉镰刀躺进帐篷里去,罗罗也不露面了,湖道里没了两张晃动的脊背和“刷刷”的打草声,草被委屈着,就让草虫儿得着了机会,它们开始发疯地吵闹,吵得不分彼此,吵得幸灾乐祸,吵成了一锅肉粥。
这日,天脚涌起乌黑的云团,很快遮住了太阳,笼罩了湖道,草虫儿敛了声息不再疯吵。湖道里阴沉沉的,变得一片死寂。天要下雨了,有可能是最后一场秋雨。乌黑的云团在湖道上面积蓄了整整一天,不断地增添着厚重感。夜里,亮子被一声巨大的炸雷惊醒,整个湖道都震荡了,一个车轱辘似的火球沿着湖道滚动,一路畅笑地消失在沙梁背后。过了没多会儿,雨水就泼下来了,抽打得帐篷摇摇欲倒。雨水来得凶猛暴戾,湖道里来不及渗水,霎时一片汪洋。在转瞬即逝的闪电中,亮子看见西边的帐篷霍然倒下,罗罗在雨水里挣扎。罗罗像一只打湿了翅膀的鸟。亮子傻呆呆地看了一阵,然后光着膀子弹跳起来,奔向那边的沙梁。亮子却又无法阻止罗罗,罗罗的力气大得惊人,头发长长地披散着,被雨水湿透的身上很滑,亮子抓了几把没抓住,让罗罗挣脱了。罗罗挥舞着胳膊在沙梁上奔跑,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与闪电的交替中时隐时现。罗罗跑,亮子也跟着跑,在沙梁上来来回回兜起了圈子,仿佛做着一种游戏。在雨里折腾了大半夜,罗罗才面口袋一样变软了,有气无力地瘫倒在泥水里。亮子要扶起罗罗,手触着那身子时又猛地缩了回来。罗罗的身子又硬又凉,像一块冰。亮子又闻见了罗罗身上的那股味儿。那股味儿虽然也是湿漉漉的,却很顽固地附着在罗罗身上,雨水都浇不掉。亮子的头就又有些晕,他觉得自己也是累得不行,快要站不住了,很想歇息一阵。
亮子说,你坐起来。
罗罗不理不睬。
亮子说,你坐起来。
罗罗终于坐直了。亮子也坐下了。
罗罗说,你是谁?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说,你是鬼。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说,男人都是鬼。
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哭了。
亮子说,你哭,我知道你想哭,你就哭吧。
呜呜呜——
罗罗就开始了她的哭泣,以至大放长声。
亮子不再说话,很认真地听罗罗哭。长了这么大,亮子还没听过罗罗大放长声地哭过。在黑沉沉的夜里,罗罗的哭声和雨声连成了一片。罗罗的哭泣比雨声更淋漓,在雨水中穿行,内容十分丰富,有幽怨有哀伤有悲怆,仿佛一只鸟的羽毛,起初是芜杂的,被雨水洗沐着,逐渐地变得洁净,甚至有一种灵动和翩然了。亮子想,罗罗你真该哭上一场,美美地哭上一场,像你这样的女子,泪水存得跟天上的雨一样多了。
罗罗就哭。
罗罗哭了整整一夜。
雨水是在罗罗的哭泣声中悄然而止的。天亮的时候,从草湖里传来哗哗的水声,罗罗停止了自己的哭泣。这是一个鲜亮亮的早晨,湖道里聚满了水,真的是大水汤汤了,像一条兀生的河流。这时,奇异的景象出现了,那两个草垛在水面上漂浮着,轻轻地打着旋儿,缓缓地往水的中央聚拢。后来,那两个草垛紧紧地靠在一起,顺水而下……
坐在沙梁上的亮子和罗罗都怔怔地看着。
罗罗说,草。
亮子说,草。
草……
(《雨花》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