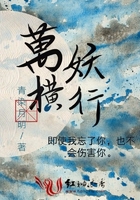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卡车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工作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上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的。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1]。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褐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十五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 ? ?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条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今日,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吗,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睡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 ? ?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睡觉,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睡了的。
一次,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三十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最终我也许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睡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 * *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乐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睡了,是第一次。
* * *
她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致是说高中一年级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也跑出高中),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上是同对方睡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2]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3]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来了又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二十一岁,再过几周就二十二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到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里我都未能踏出新的一步。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一九七〇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甚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梦都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闷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坐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 * *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个奇特的下午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被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的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在大衣袋里,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人脚踩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不好的梦?”
“总做不好的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了笑,手放在我膝头上,又缩了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上“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中。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了下头,“说不准,或许一年,也可能花上十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嗳,你不认为十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啃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的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的形象,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在大衣袋里,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一眼钟:凌晨二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嘛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在呼呼大睡时间里。”
“我不是杀人的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二十五,”她说,“然后死掉。”
* * *
一九七八年七月她死了,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