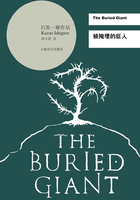增援部队到了。原来空着的位置都已经住满了人,营房里的草垫很快都被占去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老兵,可是也有二十五个年轻人是从训练新兵的野战军营送来的。他们差不多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我一下:“看见这些小家伙没有?”
我点点头。我们挺起了胸脯,在庭院里刮胡子,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打量着那些新兵,觉得自己都是石器时代的老战士似的。
卡钦斯基也加入了我们这一伙人。我们一起溜达着,经过运马拖车,到了增援部队那里,他们正好发到了防毒面具和咖啡。卡钦斯基问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你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像样的’东西了吧,是不是?”
他做了个鬼脸。“早餐是萝卜面包,午餐是萝卜做的炖杂烩,晚餐是炸萝卜饼和萝卜沙拉。”
卡钦斯基老练地吹了个口哨。“萝卜面包吗?你们还算运气,就是拿锯屑做的也算不得新奇。可是,菜豆呢,你认为怎样,要不要来一点?”
那年轻人的脸刷地红了。“你别逗我了。”
卡钦斯基只说了一句:“去把你的饭盒拿来。”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把我们带到他的草垫旁边的桶那里。桶里确实装着多半桶菜豆煮牛肉。卡钦斯基挺立在那个桶前面,如同一位将军,说道:“眼睛要尖,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都很惊奇。我问道:“好家伙,卡钦斯基,这些东西你都从哪里弄来的?”
“那番茄脑瓜很高兴,让我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我给了他三块降落伞绸料,作为交换。冷的菜豆,吃起来味道也好得没话说咧。”
他恩赐似的给了那年轻人一份,说道:“下一次你带着饭盒到这来的时候,另一只手里要拿一支雪茄或一块嚼烟。懂吗?”
然后,他朝我们转过身来。“当然,你们都可以免费吃。”
卡钦斯基是一个大家少不了的人,他具备一种第六感。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可是大家不会一开始就赏识这类人。每个连队里,总有这么一两个人。卡钦斯基在我认识的人里,要算是最机灵的一个。他的职业是鞋匠,我相信,不过那倒一点也没有关系,他什么手艺都会。跟他交朋友才好呢。我们都是他的朋友,克罗普和我,还有海伊·韦斯特许斯多少也算是他的朋友。不过,海伊这个人更像一个执行的工具,因为逢到什么事情需要用拳头来解决的时候,他便在卡钦斯基的指挥下行事。在这方面,他倒也有他的长处。
举例说吧,一天夜里,我们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可怜的小城镇,一眼看去,马上发现除了墙壁,东西都给搬走了。我们驻扎在一家又小又暗的工厂里,为了驻兵,这家工厂临时改建了一下。里面有床,或者不如说是床架——几根板条,上面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垫在那上面,一条毯子是要盖的。帐篷布又太薄了。
卡钦斯基对这些东西打量了一下,就对海伊·韦斯特许斯说:“跟我走。”他们出发了,虽然对这个地方他完全不熟悉。半小时以后,他们回来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大捆稻草。卡钦斯基发现了一座马房,里面有稻草。要是大家不是饿得那么难熬的话,我们当时就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一大觉了。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过的炮兵:“这附近有没有食堂啊?”
他笑了:“有没有什么?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连面包皮你都找不出来呢。”
“那么,这儿难道连居民也没有吗?”
他吐了口唾沫。“有的,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们自己都围着每个炊事房的锅炉打转,想要点东西来吃呢。”
情况很糟糕。那么我们只好勒紧裤带,等到明天早晨军粮送来以后再说了。
可我看到卡钦斯基已经戴上了帽子,便问:“上哪儿去,卡钦斯基?”
“只是去稍微察看察看这个地方。”他逍遥地走了。
那炮兵咧着嘴讥讽地笑了笑。“让他去察看吧!不过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失望地躺下了,心里在盘算着是不是应当把非到必要时不能动用的应急备用粮啃掉一点。可是那样做太危险了。因此,我们就试着打会儿盹吧。
克罗普将一根纸烟折成两段,把一半递给了我。加登谈起他的一道家乡菜:大菜豆炖熏肉。要不用点香杨梅来调制,他是不屑一顾的。所有的东西应当放在一起煮,千万不要把马铃薯啊、菜豆啊、肥肉啊分开了烧。有人在埋怨,要是加登再不马上住嘴,就要把他捣成香杨梅。这样一来,偌大一间屋子便变得鸦雀无声了。只有插在瓶颈里的几支蜡烛在闪烁发光,那个炮兵在不时地吐唾沫。
我们正要迷迷糊糊地睡去,房门推开,卡钦斯基回来了。我想我准是在做梦:他胳膊肘底下夹着两块面包,手里提着血淋淋的一沙包马肉。
那炮兵的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他摸了摸面包。“一点不假,上帝啊,真正的面包,而且还热着呢!”
卡钦斯基什么也没解释。他已经弄到面包,别的事情也就无所谓了。我敢肯定,如果把他扔在沙漠里,一小时之内他也会找到椰枣、烤肉和酒当一顿晚餐的。
他粗暴地对海伊说:“去劈些木柴来。”
接着,他从外衣下面拿出一个平底煎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还有一块猪油——他什么都想到了。海伊在地上生了火。火光把空空荡荡的大厂房都照亮了。我们全从床上爬了下来。
那个炮兵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该不该称赞卡钦斯基几句,好分到一点东西来吃。但是卡钦斯基竟连一眼也没有去看他,只当他是空气。他便咒骂着出去了。
卡钦斯基知道怎么样才能把马肉烤得很嫩。不应当把马肉直接放到锅里去煎,那样肉会老的。应当先用水把它煮一下。我们拿着小刀,蹲成一个圆圈,把肚子都塞饱了。
这便是卡钦斯基。假如一年之中,只能在那么一个地方,而且只有在那么一个小时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那么就在那一个小时之内,仿佛鬼使神差似的,他会戴上帽子,走出去,径直奔向那个地方,好像拿着指南针一般,把那点东西找到手。
他样样东西都找得到——如果是冷天,他就能弄到一个小炉子和一些劈柴、干草和麦秸、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可是首先会是吃的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人家还以为他是用魔法从空气中变出来的呢。他的辉煌杰作是四盒龙虾。不过,我们宁可要一块牛排。
我们安顿在营房前面晒到太阳的一边。有一股焦油、夏天和汗水涔涔的脚的气味。
卡钦斯基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很想谈话。今天中午,我们一直在练习敬礼,因为加登一时疏忽,没有向一位少校行礼。卡钦斯基头脑里总是甩不开这件事。他说:“你记住我说的,这次战争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
克罗普高视阔步地走过来,他两脚光着,裤脚高高卷起。他把刚洗好的袜子摊在草地上晾着。卡钦斯基抬头望天,放了一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豆子不大,也要出声。”
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又拿一瓶啤酒来打赌,看正在我们头顶上进行的空战谁胜谁负。
卡钦斯基完全不肯让步,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把这种意见用顺口溜表达了出来:“让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拿一样的军饷,战争保准立刻结束。”
正相反,克罗普却是一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应当是一种民间的节日,卖门票,组织乐队,仿佛斗牛一般。然后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穿着游泳裤,拿着棍棒,不妨让他们自己先决斗。到最后谁没有死,他的国家就算胜利。这种做法要比现在的安排更加简单,更加公道,现在是让不应该打仗的人去打仗了。
这个话题结束了。于是,谈话逐渐转到兵营操练上去了。
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营房庭院里一个火辣辣的正午。暑热笼罩在广场的上空。营房里阒无一人。样样东西都沉睡了过去。能听到的只是鼓手在那里练习,他们在什么地方一安顿,就呆笨、单调、乏味地练习起来。好一支谐和的和弦!正午的炙热、营房广场以及鼓手的敲打!
营房的窗子空荡荡、黑漆漆的。有几个窗口还晾着帆布裤子。人们渴慕地望着它们。屋子里很阴凉。
啊,黑暗发霉的士兵寝室,里面有铁床架、方格花纹床单、柜子和矮凳!连你们居然也能成为被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这里,你们甚至还有家的那种传奇似的余晖,你们的一间间屋子弥漫着陈腐的食物、睡眠、烟雾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用斑斓的色彩把这一切描绘了出来。只要能够回到那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予啊!比这个更远,我们的思想就不敢再追索下去了……
那些清晨训导——“98式步枪分成几个部分?”那些下午的体能训练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跑步走。到伙房报到,削马铃薯皮去。”
我们陶醉于对往事的追怀之中。克罗普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在勒讷[3]换车。”
这是我们那位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讷是一个铁路中转车站。生怕我们的弟兄休假回去的时候在那里迷路,希默尔施托斯常常叫我们在营房寝室里练习换车。我们必须了解,在勒讷车站,要到支线去,一定得穿过一条地道。我们的床当作地道,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床位的左边立正。然后命令下来了:“在勒讷换车!”于是像闪电一样,人人从床底下爬到对面去。这个玩意儿,我们要练习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德国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它像彗星一般,拖着一长条浓烟倒栽下去。克罗普打赌的那一瓶啤酒输掉了,他心情恶劣地把钱掏了出来。
“希默尔施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等克罗普的失望情绪消退以后,我才说道,“为什么他一当了下士,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虐待人的恶棍了呢?”
这个问题使克罗普又活跃起来。“这倒不只是希默尔施托斯一个,那样的人还多的是。他们一旦肩上缝上了一个显示军阶的纹饰,或者佩上了一把军刀,就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了,好像吞下了混凝土似的。”
“是由于军服的关系。”我揣测道。
“大体上说,是对的,”卡钦斯基说,他准备长篇大论了,“可是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譬如说,假使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后来你又拿一块肉放在它面前,它还是会把肉抢来吃的,这是它的天性。假使你给一个人一点点权威,他也会和希默尔施托斯一样,就像狗吃肉一回事。事情完全一个样。因为人在本质上首先也是一头野兽,不过也许正像涂着黄油的面包,他把自己文饰得道貌岸然一点罢了。军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个人总得要有管理别人的权力。糟就糟在每个人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士官可以折磨一个小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士官,一个上尉又可以折磨一个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发疯为止。而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干,大家不久也便或多或少地养成了这样干的习惯。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吧:我们正从练兵场列队回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又下来了命令:唱歌。好吧,我们便没精打采地唱着,因为大家还要扛着步枪步履艰难地前进。可是一下子又要连队向后转,再来操练一小时作为惩罚。列队回来的时候,又命令大家唱歌。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唱起来。这种种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无非是因为有了那么点权力,连长的脑袋瓜就起了变化了。而且,没有什么人会责备他。正相反,倒是有人会因为他的严格而器重他。这当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可是其他许多截然不同的事情也无非是这样。现在我问你:在和平年代,一个人随便干什么,究竟会有哪一种职业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不被人家打断鼻子的?只有在军队里他才能这样干!你瞧,这些都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了!而且平民百姓中越是无足轻重的人,爬到他们头脑里的这种东西可就越多。”
“当然,他们说应该有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不错,”卡钦斯基埋怨道,“他们总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许确实是这样。不过总不该恶意刁难啊。再说,你试一试把这些事给一个铁匠,或者一个雇农,或者一个工人解释解释,你试一试把这些道理给一个小兵讲清楚,这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他已经受过折磨,被送上了前线,可他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简直是咄咄怪事!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人反对,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可是到了火线后面几公里的地方,操练又得重新开始,又得重新来那一套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分列前进。因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总得让士兵们有些事情做。
这时,加登满面红光地进来了。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有点结结巴巴了。他喜气洋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希默尔施托斯已经在路上。他也上前线来了。”
加登特别仇视希默尔施托斯,因为在宿营地时希默尔施托斯教育他的方法太恶毒了。加登是个遗尿病患者,一到夜里他就在睡梦中把尿撒在床上。希默尔施托斯非常武断,硬说他不过是偷懒,还发明了一种自以为可以治好加登那个毛病的值得称道的方法。他从隔壁营房里另外觅得一个患遗尿病的人,名叫金德瓦特。他就把他调了过来,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照例是双层床铺,上下两层,床面是用铁丝网做的。希默尔施托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那个睡在下面的人,当然是够他受的。第二天晚上,把位置变换一下,原来睡下铺的改睡上铺,这样他就可以报复了。这便是希默尔施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个主意有点卑鄙,可是构思倒也巧妙。可惜并无用处,因为那前提便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两个人,谁也不是偷懒。任何人一看他们苍白色的皮肤,就可以知道了。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其中一个人一直睡在地板上。这样一来,他就经常感冒。
这时候,海伊在我们旁边坐下了。他向我挤了挤眼,还思虑满满地搓了搓手掌。我们曾经一起度过军队生活中最美妙的一天。那就是我们开往前线去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团里,可是首先得回到卫戍部队去领取制服,这当然不是到新兵驻地,而是到另外一个兵营。我们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跟希默尔施托斯清算一下。几星期前,我们早已立下誓言要干这件事了。克罗普甚至考虑得更远,他想在战争结束以后进邮政部门工作,以便往后在希默尔施托斯重新当邮递员的时候做他的上司。他幻想着自己将来怎么样教训他,便觉得洋洋得意。想着这些才让我们熬过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一直在盘算,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一定要向他报这个仇。
这会儿,我们先决定狠狠地揍他一顿。如果他认不出我们,他对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啊,而我们反正明天一大早就要动身的。
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总要去小酒馆。回营房的时候,他一定得走过一条又黑又荒凉的路。我们就在那里躲在一堆石头后面等他。我随身带着一条床单。大家等得直打哆嗦,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后来,我们终于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这声音我们是一听就知道的,因为每天早晨我们经常会听到,房门突然打开,他大声吼道:“起来!”
“一个人吗?”克罗普悄悄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一起溜到那堆石头前面。
他的腰带搭扣闪闪发光。希默尔施托斯似乎有几分醉意,他一路唱着歌。他毫无疑虑地走过来了。
我们抓住那条床单,轻轻一跳,从后面把他的脑袋蒙住,将下面捆紧,使得他站在一个白布袋里,连胳膊也举不起来。唱歌停止了。
不大一会儿,海伊·韦斯特许斯来了。他张开双臂,把我们推开,好让他先来。他兴致勃勃地摆好架势,举起一条胳膊,活像信号桅杆似的,一只大手,如同煤铲一般,照准那口白布袋声音清脆地打了一拳,那股劲头简直连头公牛也能给打死。
希默尔施托斯栽倒了,在地上滚了五米远,开始大声吼叫。可是我们早已料到,所以事先带来了一个坐垫。海伊蹲下身去,将坐垫放在膝盖上,摸摸希默尔施托斯的头到底在什么地方,便把那个脑袋一个劲儿地往坐垫上压。他的嗓音顿时给闷住了。海伊不时让他透一口气,于是他从咕噜声中又会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嚷,可这吼声马上就被捂住了。
加登解开希默尔施托斯的吊裤带,把他的裤子剥了下来。加登用牙齿咬着一根鞭子。随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希默尔施托斯倒在地上,海伊朝他屈着身子,让希默尔施托斯的头抵在膝盖上,他自己脸上露出一种恶魔似的狞笑,还乐呵呵地大张着嘴,随后是那颤动着的有条纹的衬裤,腿在那里面蜷曲着。每抽下一鞭子,那被拉下的裤子里面种种最独特的动作,还有仿佛一个伐木工人耸立在这一切之上的孜孜不倦的加登。后来,我们不得不干脆把他拉开,这样才轮到我们。
最后,海伊让希默尔施托斯重新站立起来,单独给了他一顿教训作为结束。当他伸出右胳膊,准备打他一记耳光的时候,那个神态简直像是要去摘下一颗星星似的。希默尔施托斯仰面朝天倒下去了。海伊又将他扶了起来,自己摆好一个准备姿势,用左手准确而结结实实地揍了他第二下。希默尔施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匍匐着逃跑了。他那有条纹的邮递员的臀部在月色下闪着光。
我们飞奔着消失了。
海伊再一次向四周望了一望,既愤怒又满意,还带几分神秘意味地说道:“报复嘛,就像是血和猪肉制成的黑香肠。”
希默尔施托斯理该觉得高兴,因为他说的我们应当相互教育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结出了果实。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了。
他始终没有打听出来,这件好事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不管怎么说,他好歹从中捞到了一条床单。因为过几个小时我们回去寻找的时候,那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使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出发的时候心里觉得相当满意。有那么一个蓄着大胡子的老家伙,居然还满意地称我们是少年英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