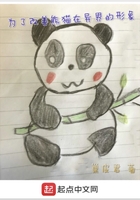闲来无事,治水君走出治氏族地,准备去村委会找村长聊聊那个无边落木境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别致。到哪才发现那里比治氏还忙,因为旧的村政府大楼已经借外来人之手义务拆迁了,地下室贮藏的已提取过灵气的普通木柴也被人义务处理了,除了可以用来养花的灰烬外还可以借机敲诈几个村落一笔。代价是在新的政府大楼建成之前,村政府都要在中央广场上露天办公,而现在旧址清理还没结束,那几个村子的赔偿款项还在谈判中,所以估计整个夏天都要在户外度过了,最惨的是村长,他策划了这样一个拆迁重建项目,结果一不小心发现,没住处了啊…。
治水君见到村长时他正一个人悠闲地端着杯茶在广场一角的树荫下看夕阳,微微抬起沧桑的目光准备应对下属有关各项困难的抱怨,结果发现来人是治氏的小土豪,脸色陡然一转极为慈祥的拉着治水君的手嘘寒问暖,准备忽悠他给自己这空巢老人安排个巢。治水君察觉不对但手已经被村长挽住不好挣脱,只好赔笑道:“都挺好的,我妹挺好的,我爹也挺好的,如果今天不是被关了大半天那我也会挺好的。”
村长热情接话:“嗨,没事儿,这不是对村里下一代的领袖特别关照嘛,是我作为村长应该做的。对了治水啊,你在村中央广场附近有没什么房产啊,最好是独栋的别墅,带个院子就行,你也知道这不是村政府大楼被极端恐怖分子炸了嘛,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只好拜托你了呀,价钱什么的咱哥俩谁跟谁啊,想当年我和你祖父那可是过命的交情,跟你父亲也是忘年之交,谈钱多伤感情对吧。”治水君丝毫不敢就这错综复杂大逆不道的友谊多做讨论,但是村政府附近的房产那可不便宜,主要是独栋的别墅就那两家,还都有人住,总不能…村长听了治水君的解释诚恳地点了点头,一拍他肩膀,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代表我去和他们谈,要是不肯那就是不给你面子,不给你面子那就是不给治云(治水君父亲)面子,不给治云面子那可就是不给治丰(治水君祖父)面子,要是连治丰的面子都不给嘛…。
治水君生怕村长把他自己搁里边,便打算应付下来,大不了把名下店铺搬一个家就是,结果村长脱口而出,“那你就把柴治治派他家去闹,当然先说好不到紧要关头这种大型杀气还是不要轻易使用,毕竟有伤天和。”治水君深以为然,而后又犹豫是不是要和村长探讨下第八阶的专属神通名字是不是有些草率就听村长嗯了一声,“确实草率了点,当初修成的时候原本还想取名为刀王之境什么的,不过这名字有些偏离中心思想了,无边落木萧萧下就很不错,切合题意,一听就很会砍柴,一刀下去无数柴火滚落在地,就是名字略长念起来很不方便……”。
治水君满头黑线,本想问村长是不是又偷听他走神时的自言自语了,结果村长好奇问道:“为什么你脸上有这么多黑线啊?哦这个梗已经不好笑了是吧,好吧我承认刚刚真的听到了你内心想法,不过这次不是因为你的碎碎念,而是我真的修成了心境通明哈哈!”就不该来这里讨论什么无边落木境,我真是闲得够慌的,治水君和村长告别,一个能随时随地监听到心中所想的人实在太可怕了,妈妈我再也不找村长聊天了。
夕阳落下夜月升起,从脚下青玉色地砖到树梢苞蕊初绽的梨花,被皎白月光笼罩散发出淡淡的辉光,与月湖村擅长的带着湖波水声的月华不同,此处的月是静中显动,如烟一般轻盈朦胧,树下的少女挽着略显成熟的梁家堕马髻,长发于颈后结髻垂在背部,另从髻中分出一綹头发朝一侧垂下,不同于垂鬟分髾髻的稚气青春,也未像平时一样束发垂于柳腰所系的白色束带上,这种略有些奇怪的发型是那位族姑为她梳的。青衣长裙白鞋袜,让某个自隐秘小路溜进来的青年一见忘情,一时不知要说些什么,只觉得眼前人熟悉又陌生,半晌才从她嘴角的一颗小痣辩认出是想见的人,倒是少女被盯得久了有些不自然,眉眼间的欣喜融化月光以及少年的镇定自若。
“我父亲在小姑那边喝多了,有些无聊便想出来转转”,她轻声讲着,自青年眼神中读出某个有些煞风景的猜测,忽又羞恼道,“没错我刚才又吃撑了,出来消消食,不行吗?”
青年看到她嘴角微撅起的浅浅弧度,听着她轻轻责备嗔怪的话语,眼睛被月光恍得想要挪开视线又舍不得,慢慢的有莹润的光点在眼中凝集,却是不回答她的责问。
“我陪你走走吧。”~( ̄▽ ̄~)~
说着他牵起姑娘的柔荑,指尖碰触时还有些颤抖,等到十指交叉后又恢复平日的镇定沉稳,只是村花发现他步伐有些飘浮,于是关切地问道:“是中午那时受的伤?还疼吗?”
原本只是摔了几下的阿柴摇摇头,不禁嘶的倒吸一口冷气,村花扑哧轻笑,踮起脚尖伸手按在他头上,阿柴连忙低头任村花处置,村花的小手指轻轻地抚过他的头发,往复几次,然后邀功似的问道:“现在不疼了吧?”两年间身高突飞猛进的青年用另一只手环住姑娘柳腰,厚着脸皮贴着她的耳朵说现在不疼了,鼻尖嗅到浓郁的花香,他略显急促的呼吸挠着村花的耳朵,察觉到彼此身体温度的飞速上升。
最开始认识的时候,花滢滢不过只见了他两次就交换了彼此的名字,嗯,还是经小丫头搭的桥,那时的村花只觉得眼前的瘦小少年没什么闪光点,也提不起兴趣,托小丫头的福,终于不再无感,三个月便见之生烦,偏还要皱着眉礼貌地打招呼。半年后这种隔两天便遇上一次的厌烦也渐渐退去,慢慢转为一种带着些许期待的日常项目,偶尔出趟门几天没见还会有些不习惯,就在恶感慢慢转为好感不久,大约一年多的样子,小丫头再出昏招,偏偏那个缺心眼儿的木头当了真,不知从哪速成的养花理论,居然和他父亲相谈甚欢,熟识不久就上门提亲,最重要的是一件礼物也没有,这不是礼物轻二重有无的问题,而是让她心里有那么一丝不得劲儿,从而决定不能太纵容他不通事故人情了,加之父亲有所误解触了她的霉头,她一怒之下便将那个身形渐高的少年推出门外,把自己的内心暂时封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村子另一头躲着某人的她边散步边在心里骂着,榆木脑袋,也不见来找找她,更没办法就此放他一马,越想越气,就揪着身边迟迟不去那边给个暗示的小丫头出气,每次见到会烦,不见了又会因突然不烦了感到一阵新的烦闷,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一般,明明记得就在那儿却怎么都找不到。
再次见面是受不了那委屈的小丫头开了窍,缠着她去看柴疯子的受封礼,再一不小心透露行踪给那根木头,结果弄巧成拙,那天连刀都被砍断的某人昏迷前还是溜到她面前,明明不轻的伤疼得要昏过去了却还要挤出笑容来。虽然她百般厌憎他的不自量力哗众取她一人之宠,厌烦他败得太惨丢人现眼,厌弃他满身尘土且不顾别人目光扑倒在自己身前,厌恨他不敢再向前半步而是躺在她脚下,还得她蹲下身去搀扶起来,艰难地搬运回他那个小破院子,连累她又被小丫头嘲笑了一通。
原来厌着恨着,某个人的影子还是在她心里生根发芽,自干涸的湖底生出朵朵莲花,而后终于积蓄雨水成了荷塘,有了夏秋冬春,有了万物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