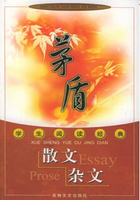岁月神偷
倪国欣我从小就知道,母亲店里传来的“哐当哐当”声中是流着金的。我日日夜夜都在这生涩却绵延不绝的声响中醒来或者睡去。它像生活的背景乐,有了这声音,日子便活了起来。母亲的缝纫机有些年头了。飞人牌。机身上黑漆剥落,露出锃亮的铁,铁又在南方濡湿的空气中生了锈,爬满岁月的痕迹。母亲说,我长个子的时候时常撞上缝纫机上的木板,嗷嗷大哭。或者将沾了棉絮的机油洒到衣服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油渍。
我不穿母亲做的衣服,因为走出去,镇上的人识得是母亲的手艺,便开始打趣说又不知道是赚下了哪家的布料。小镇人不多,母亲的服装店开在主干道西边一条窄小的巷子里,说是服装店,实际上连同住家,卧室与店面一门相隔。卧室后面是厨房,母亲照看店面繁忙,碗橱蓝色的纱布上蒙着一层腻腻的油烟。
巷子里手艺人不少,理发的、修鞋的、蒸糕点的,能把人一身的行头和吃喝都包揽了去。手艺也禁锢了这些人的一生,将他们的灵魂敲打成俯耳听命的薄片,一如我的母亲。巷尾种着一棵高大的合欢树。绕过合欢树,是邮局,墨绿色的邮筒在经年的风吹日晒中色泽暗淡,锁眼锈迹斑斑。小镇上信件少,鲜能看见邮局叔叔的绿色帆布包里塞得鼓囊囊的。
翟越得以离开小镇是因为他从邮局叔叔的挎包里取回了一张大红的录取通知书。正是初夏时节,合欢伞状的小花簌簌落了一地。
彼时,我在镇中学念书,即将升入高三,人尽皆知的尖子生。翟越要去有海的城市。他说,念大专不过是学一门手艺。阿慈,今后,我靠双手吃饭,你要靠大脑吃饭。翟越学的是厨师,小镇上没有大饭店,零零散散开着几家小吃部,不过是提供些寻常饭菜。他还说,这样我就有理由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了。
九月,盛夏的溽热气息还未退却。热气在水泥地上似乎能蒸腾出万马奔腾的模样。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半小时一班,我在车站送翟越走,直到第三辆车来的时候他才离开,交给我一包晒干的合欢花。
车轮扬起的尘埃久久散不去。过往的无数个分分秒秒碎成颗粒。回去的时候要经过翟越家,他家住在巷头,翟叔叔是白铁匠人,敲打白铁的声音一如既往“叮当叮当”。他抬头看我一眼,自言自语道:“走了啊。”
我也从小就知道,小巷里每家手艺人手指下的声响都是流着金的。这些声音遁入时间的长河,经年累月,便可以从父辈们的发梢眼角觅到踪影。我和翟越吃喝用度的哪一分不是从这昼夜不息的声响中慢慢熬出来的。
哐当哐当……叮当叮当……
走到叶姨门口的时候我顿了一下。叶姨有好听的名字,叫燃音。母亲说她是城里的歌女,声音里藏着一团火,能把人的爱恨情仇通通勾上心头,烧得炙热。我只听她说过,是这副嗓子把她焚成了灰烬。
叶姨搬到小巷里来的时候我7岁,她的房子是一个姓江的男人特意给她建的。那个时候,屋顶崭新的鱼鳞瓦反射出的太阳光让我的视线迷离虚晃。她是个明丽的女子,初见那日,淡黄色旗袍上绣着大团大团的木槿。母亲不做旗袍,那是20世纪中叶的奢侈衣物,线条流畅,摇曳生姿。母亲店里挂着的是最平常不过的女式西装或缀有碎花的棉布衬衫。
镇上妇女的穿着大多色彩晦暗。她们也不像叶姨那般修眉施粉配以精致衣物。亦见不惯她的作风,三五扎堆说着她的闲话。
我却喜欢她。我喜欢她是因为157天前的那个夜晚,她曾收留我。还是三月阳春天气,翟越和我回到小镇上时极为狼狈。警察在我们双方家里做完笔录走后,四周静得让人遍体生凉。母亲手里攥着断了好几节的皮尺对我吼道:“滚!滚出去!”我生性倔强,皮尺抽在裸露的皮肤上没吱半声。她是那样隐忍的妇人,曾在岁月的舛途中一次次与命运握手言和。
那一晚,母亲的温和性情消失无影。我在深夜被她赶出家门。狭窄的巷子里只有三两盏路灯,透过支离破碎或者积满尘垢的灯罩散出晦涩的光。手艺人这时候也歇下了,周围静得能听见猫的肉垫踩在低矮屋顶上的声息,老旧的鱼鳞瓦片上有裂纹蔓延开来。
叶姨裹着素色大衣站在我面前,伸出她纤长的手:“来,先跟我回家。”发春的猫在嗓眼扯出婴孩啼哭般的叫声。森森的凉意。
八年了,昔日修建一新的屋子也显出陈旧的色调来。樟木地板发出“吱呀吱呀”的细碎响声。我以前从未去过叶姨家,她极少出门,偶有几次相见也不过是她携几件起褶的旗袍托我母亲熨烫。
屋子里熏着香,宁神的雅淡气味。她真是精致的女子。这般懂得疼爱自己。她打开衣橱的门,让我挑一件合身的衣服穿上。
对坐于妆台,叶姨点一支细长的烟。卸了口红的唇角微微开裂。她问我:“怎么落魄而归?”
我不答。小镇上的人早就被平淡的日子磨成了无棱无角的石头。又怎会懂得这般枯燥的生活于我就是枷锁,一点一点扼死跃动的灵魂。
翟越带我离开的时候身上只有七百块钱。他扬一扬手中的火车票,仿佛多年来的沉重枷锁找到了解封的咒。我们在升旗仪式结束后翻墙逃出学校,踏上往西的列车。
目的地是稻城。我曾在地理书上用红笔圈出这座四川省边陲的小城。那一页纸被我翻看得起了皱。北纬27°58",东经99°56"。与我所在的小镇相距1407千米,21小时车程。
我对翟越说,我太累了。生之艰辛已将我的青春饿得精瘦。母亲店里夜以继日的“哐当哐当”声同她在暗夜里的哭泣一样能把人的心脏揪成团。生活将我逼到一条只能拼命读书的死路上。
坐在叶姨的屋里我不住地咳嗽,她掐灭烟头。去院子里摘一把枇杷叶。洗净后加上冰糖放在瓦罐里用文火慢慢地煎。
她拢了拢衣领,跷着腿靠在椅背上:“我年轻时也如你这般不安分。那时候家里有钱,父母一心要把我调教成大家闺秀模样。我受不了那样严苛的家教,只身逃了出来。”我从母亲口中听闻叶姨不是本分的女子,她搬到小镇上不过是被那个叫作江易的男人豢养在外,如同一只昂贵的宠物。
“你一定知道我曾经是歌女。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叶燃音三个字是吸金石。都说歌场上的梦想和爱情是幻影。我叶燃音不信。”叶姨的眼里映着梳妆台上那盏复古台灯琉璃灯罩的色彩,水光潋滟,“那是我最好的年华,20岁出头。一颦一笑皆风姿绰约。我爱极了那夜夜笙箫。富家子弟砸的钱都是我成为歌星的铺路石。”
叶姨念过书,也能说上几句洋文。容貌气质俱佳。她说:“阿慈,你知道吗。我的歌声引来了在上海写生的Brian。法国人,金发碧眼。他日日带一束鲜花来看我,散场以后便约我去看曲谱。肖邦或者李斯特。他也给我画肖像,素描简笔和油画。我用蹩脚的英文与他交谈。逐渐彼此都心生好感。”
注定不会是美好的结局,我想。一个是在大上海唱着靡靡之音的歌女,一个是游荡于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
“Brian说,等他结束在中国的写生就带我走。他的眼睛像高山上的湖。深蓝的瞳仁能吞噬任何一个少女的心。他夜夜在满城流光溢彩中对我说‘Iloveyou’。我亦夜夜做着有他的梦。我要跟他去法国,那个素有浪漫之称的国度。去看塞纳河畔埃菲尔铁塔上的星空,去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放风筝。”
叶姨讲得入神,对着窗户微微颔首。已过了午夜,窗外漫起沉沉的雾霭。母亲店里仍然亮着灯,在这雾霭中散出大片大片的空白。
她起身,拨弄衣橱里挂的齐整的旗袍。淡黄、金粉、洋红、深蓝、象牙白、宝石绿。大多绣着色彩明丽的花朵或鸟雀。“Brian爱极了身体的曲线美。他给我买各式各样的旗袍。他说,歌场上的女人应该用这样奢华的服饰做装点。我更换不同的旗袍和姿势让他作画。他把画寄回法国卖得好价钱。”
瓦罐里的枇杷叶水煮沸了。气泡掀着盖子“咕噜咕噜”地响。叶姨端起瓦罐将煮成淡黄色的水倒入白瓷杯中。文火照着她的脸。她的眼角眉梢有细小的褶皱。
她拢了拢散到额前的发。叹一口气。
“后来,我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来。Brian给我做了道残忍的选择题。打掉孩子继续做他的模特或者给我一笔钱让我自生自灭。呵,我竟忘了,Iloveyou三个单词算什么承诺。”
叶姨眼中的光彩暗淡下来:“打掉孩子后我再没见过他,那一定是一个好看的混血婴孩。我的手术有风险,从此再不能生养。”
“那个夜晚我哭得狼狈不堪,住在狭小的出租房里第一次那么想家。我就想啊,一辈子庸庸碌碌又怎样?不做歌星又怎样?至少不会让我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我喝了口白瓷杯中的枇杷叶水,苦涩的味道堵在嗓眼。呛得我咳嗽连连,直到把眼泪咳出来。
“叶姨,我们没有打算离家出走。稻城有我没见过的高山草甸。翟越只不过想在他毕业之前带我义无反顾去一次远方。叶姨,我在课本上见过‘梦想’这个词。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我想去找它。”
叶姨将我的脑袋搂在胸前,轻轻抚我散开的发。她的身上有好闻的香味,胸前的温热气息让我安心。
“我们坐了21小时的火车抵达稻城。列车上我来例假,小腹疼得死去活来。下车以后便开始发低烧,翟越背我去医院,身上的钱不知在何处被偷了去。两个人在荒原上彳亍难行。后来被巡视的警察发现,翟叔叔和母亲也已经在县城报了案,我们才得以回来。叶姨,你相不相信,我和翟越只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纤长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信。”一夜无眠。叶姨揽着我轻声哼着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嗓音里没有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那团火。平静如窗外的月色。
小镇的清晨依旧被馒头的香味唤醒。叶姨买了早点让我吃下。我回家取课本,母亲呆坐在缝纫机前,陈旧的木板上有一条条用剪刀划下的崭新的印痕。
她抱住我:“你去哪里?”“回学校上课。”她松开手,应一声:“好。”
我从来都不知道母亲对我离开小镇有那样深厚的恐惧。前夜,叶姨告诉我,我的母亲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生下我三年后,父亲乘坐第一趟从小镇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再也没有回来。那个周一,我被剥夺做升旗手的权利。翟越同其他三个护旗手举着旗帜昂首阔步向升旗台走去。他在阳光下朝我所在的方向笑,似乎前夜的事并未让他介怀。此后,每当我回家路过翟叔叔的店门,他便用警惕的眼神打量我。我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外头的风言风语自是指向了翟越,他被冠上不好好学习还带坏别人的恶声名。小巷里只有我愿意与他一起玩,也只有叶姨知道,是我求着翟越让他带我出去走走。
翟越毕业了,去了那座叫作大连的城市学厨师。我亦升入高三,坐在他曾经坐过的教室里与唐诗宋词、三角函数、动能定理厮杀。
他时常给我写信。我满心欢喜从邮局叔叔的绿色帆布包里取出薄薄的信件。翟越说。阿慈,远方有那么多的未知。课程不忙时,我便一个人沿着海滩闲逛。
你可知道,我能在那澄澈的波光里看见你的眼。他说。大连这时候的海风凛冽且腥湿,你的课程也应已进入繁忙的阶段。从前听你说起夜里常常烦闷不得入眠,你让你母亲给你做个枕套,塞上我给你的合欢花。可以宁神。
他说。大连已飘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南方虽还温暖,但也是凉风乍起时节,你多穿衣服。
我回信回得勤,将信纸叠成好看的形状,装入黄褐色的信封,用糨糊封口,交给邮局的叔叔。而翟越的信却来得越来越少了。在越来越少的信件里越发频繁地提到叫茗雅的女子。
他说。今夜,我与茗雅在海滩放飞孔明灯,它飞着飞着就成了遥远的星辰。时光那么静好呵。
他说。茗雅想看江南的小桥流水。我告诉她,长江南岸散落着许许多多古镇。同里、千灯。每一座小镇都有不同的传说。
他说。阿慈,我已能做得一手好饭菜,连挑食的茗雅都赞不绝口。有机会我请你吃饭,绝对是小镇上没有的风味。
得知叶姨死讯的时候我正在给翟越回信。母亲匆匆叠起叶姨送来熨烫的旗袍,让我乖乖待在家里。她说,叶燃音的屋里不吉利,你别去沾了晦气。
我听闻叶姨在河边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自己却溺死在结了薄冰的河水里。那个叫江易的男人前来为她办理丧事。江易是她以前所在歌厅的老板,有妻子和孩子。叶姨堕胎万念俱灰之后,江易顺从她的愿望,将她送到我们这座远离上海的小镇上。
叶姨的葬礼简单潦草。没有挽联,没有亲友。母亲回来以后摇头道:“真是可怜,那么袅娜的一个人,被河水泡得浮肿,连她生前最爱的旗袍都穿不上。”
我逃掉了当天的晚自习去了叶姨家里。只有江易和落水孩子的家人为她守灵,她的一生就连死后都是此般凄清模样。屋里燃着几炷檀香。推门声惊动了坐在椅子上出神的江易。他抬头看我一眼说:“你来了。”
我讶异,他微微动了动嘴角:“你是阿慈。”我应一声。跪在叶姨的灵前。“燃音说你像当年的她。”江易闭着眼,眼角有未干的泪。“多少人曾愿为博叶燃音一笑不惜一掷千金,谁能想到,她的结局竟是如此。都说风月场上的女子薄情。燃音她不信,她要为理想和爱情焚尽此生。她要守着回忆和愧疚安静度过余下的岁月。阿慈,你可知道,她一直对父母和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心怀愧疚?”
我摇头。“我曾许诺离婚以后娶她,她不愿,说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几个月前,她在电话里跟我说身边有个女孩叫阿慈,像极了曾经的她。倔强而隐忍。她说不能让你重复她的路。燃音只想在这座与世无争的小镇里熬罢此生,却不能。她是在用生命赎罪。”硕大的泪从江易的眼中滚落,他用手掌捂住脸,泪水顺着手指的缝隙流出来。江易的声音哽咽:“燃音,你为何不信,生命不过是大梦一场。Brian不过是这场梦的细枝末节,你为何不愿醒?”冬天的夜来得早,九点刚过,窗外便漫起沉沉的雾霭。半年前,叶姨还能揽着我的肩膀,给我用瓦罐煎枇杷叶水止咳。那个时候,窗外也有这样沉沉的雾。那封本要寄给翟越的信迟迟没有再落笔。我依旧每日每夜听着母亲店里“哐当哐当”的声响。听着它们在清晨响起,听着它们在深夜息止。然后抱着塞满合欢花的枕头久久不能入睡。
再见翟越是次年五月中旬。他在大连公安局刑满释放。依旧是阳春三月去追寻浪漫,却不想入了牢狱。
茗雅说,最想见三月的江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翟越是那般痴的男子,愿携心上人的手,把万水千山走遍。大连开往苏州的火车上,夜深时分,有人将手伸向茗雅的口袋。茗雅惊觉便开始大声呼叫,翟越护着茗雅将小偷打成重伤。
虽判定是正当防卫,案子了结后就被释放,却毕竟是留下了案底。翟叔叔不愿他再出去惹是非,便帮他办理了退学手续。茗雅没有大碍,仍然去上学。此后他们有没有联系,我不知道。
翟越在店里跟他父亲学白铁手艺。放学路过他的店门,我与他打招呼:“嘿,翟越。”他“嗯”一声,然后低下头,不再言语,专心敲着手下的白铁。“叮当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