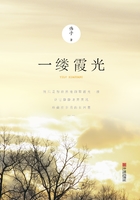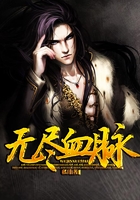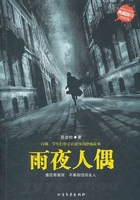童道明
一
安东·契诃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既是个小说家又是个戏剧家。
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称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就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而言,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可以与契诃夫抗衡的。
但托翁对契诃夫的剧作评价极低。一九〇一年的一天,契诃夫去探望到克里米亚养病的托尔斯泰。临别时,大文豪对契诃夫说:“莎士比亚的戏写得不好,而您写得更糟!”
然而一个世纪过后,恰恰是当年不入托尔斯泰法眼的莎士比亚和契诃夫,成了当今世界两位最令人瞩目的经典戏剧作家。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威望的大戏剧家彼得·布鲁克的导演代表作便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契诃夫的《樱桃园》。
二
在十九世纪末看低契诃夫戏剧的不单是托尔斯泰一人。当时的戏剧评论界普遍不接受这位剧坛新人。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七日《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之后,当时最有名望的剧评家库格尔写文章对此剧作了毁灭性的批评:“契诃夫先生是小说家出身,他有一个致命的误解,他认为小说笔法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神圣的戏剧领地。由于有了这个致命的误解,这个原本就不及格的剧本,便变得不可救药了。”
当然还得承认库格尔的眼力,他在《海鸥》中看出了契诃夫的“小说笔法”,以为这样就破坏了传统的戏剧规则,于是把它打入了另册。而契诃夫的戏剧革新也的确包含有戏剧散文化的诉求。他在创作《海鸥》时给友人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您可以想象,我在写部剧本……我写得不无兴味,尽管毫不顾及舞台规则。是部喜剧,有三个女角,六个男角,四幕剧,有风景(湖上景色);剧中有许多关于文学的谈话,动作很少,五普特爱情。
另一封信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剧本写完了。强劲地开头,柔弱地结尾。违背所有戏剧法规。写得像部小说。
《海鸥》对当时欧洲戏剧传统的“戏剧法规”的冒犯,显而易见。在第一封信中指出《海鸥》是“四幕剧”,就违背了分幕的“戏剧法规”。
我们知道,传统的欧洲戏剧的分幕一般都采取奇数结构,即分五幕或三幕。奇数分幕结构的剧本易于获得高潮居中的戏剧性效果。契诃夫背离奇数结构的编剧传统,把他所有的多幕剧都写成四幕剧,这正好反映了他不想像其他的剧作家那样去刻意追求戏剧的高潮点,而是把舞台上的戏剧事件“平凡化”与“生活化”。契诃夫开了“散文化戏剧”的先河。
在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能够认识到契诃夫戏剧美质的戏剧家,只有正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筹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他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给苦闷中的契诃夫写了封信,表达了要排演《海鸥》的愿望:
戏剧观众还不知道你。应该让一个有艺术趣味、懂得你的剧作的美质的文学家(他同时又是个出色的导演)表现你。我以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选。我抱定了揭示《伊凡诺夫》和《海鸥》中的对于生活和人的灵魂的奇妙展现的目标。《海鸥》尤其吸引我,我可以完全担保,只要是精巧的、不落俗套的制作精良的演出,每个剧中人物的内在的悲剧就会震撼戏剧观众。
丹钦科的这封信没有得到契诃夫的积极回应。丹钦科便于几天之后的五月十二日又发出一信,用近于哀求的口吻对契诃夫说:“如果你不给,那会置我于死地,因为《海鸥》是唯一一部吸引着作为导演的我的现代剧。”契诃夫终于被丹钦科的诚恳所打动。
这样就有了在世界戏剧演出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舞台演出——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艺术剧院《海鸥》首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在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时说:“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
丹钦科后来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的盛况。他下了“新剧院从此诞生”的断语。后来,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鸥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丹钦科解释说:“绣在我们剧院幕布上的‘海鸥’院徽,象征着我们的创作源泉。”
一个演出造就了一家剧院,也拯救了一个剧作家,这在世界演出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三
在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后,高尔基深化了对于契诃夫戏剧革新的美学意义的认识。
一八九八年年尾,高尔基给契诃夫写信,说起了他对于契诃夫戏剧的划时代意义的认识:“《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别人的剧本不可能把人从现实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而您的剧本做得到。”
高尔基一语破的,揭示了契诃夫戏剧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契诃夫把传统戏剧的那个封闭世界打开了。契诃夫不仅把戏剧与散文(即小说)以及抒情诗之间的樊篱打破,同样的,也拓宽戏剧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十九世纪末刚刚露头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嫁接。也就是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纳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内,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也帮助契诃夫戏剧“可能把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到哲学的概括”。
于是我们就能知道《海鸥》第一幕的戏中戏里妮娜这一段独白的意义:“我只知道要和一切的物质之父的魔鬼进行一场顽强的殊死搏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
只要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的境界,仍旧是人们心中的希望,契诃夫戏剧就永远能保持新鲜的现代感。契诃夫戏剧之所以能让现代文明世界的人们感到亲切,就是因为这些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现代人,可以理解契诃夫戏剧人物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痛苦。
四
小说家契诃夫早已名震遐迩,但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得到世界公认,却是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在巴黎夜游人剧场演出,揭开了“荒诞派”戏剧的序幕,一九五二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问世,更是标志着这一现代戏剧流派的崛起。而戏剧专家们在探索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特征时,发现它们与传统欧洲戏剧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这些现代戏剧中没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分,支撑这些戏剧的行动展开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这一群人与包围着这一群人的社会环境的冲突。
而当学者们寻根溯源,力图追溯这样新型的戏剧冲突的源头时,便找到了契诃夫戏剧。
的确是这样。契诃夫不仅对艺术具有现代精神的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同样具有现代精神。他不愿意用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人与事,他扬弃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判断,因此,他的戏剧人物也无法用传统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加以分割,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他的剧本里“既没有一个天使,也没有一个魔鬼”。
这样,到了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的一九六〇年,我们从俄罗斯出版的《戏剧》杂志编辑部文章里,读到了如此掷地有声的断语:“实际上,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契诃夫对于俄罗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意味着什么。”而理由之一也恰恰是:“在世界上,契诃夫首先创造了剧中人物彼此之间几乎不发生斗争的戏剧。”
然而,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乐观主义,又与充满绝望感的荒诞派戏剧拉开了距离。
《万尼亚舅舅》里的索尼娅最后劝慰悲痛中的万尼亚舅舅说:“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布满钻石的天空……”
《三姊妹》结尾时,大姐拥抱着两个妹妹说:“我们要活下去!军乐奏得这么快乐,这么愉快,仿佛再过不久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
《樱桃园》里的青年主人公也期望着在俄罗斯出现更加美丽的樱桃园……
而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式的“等待”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他的剧中人物对时间概念,采取一种揶揄的态度。波卓向弗拉基米尔发怒说:“你干吗老是用那混账的时间来折磨我?”
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在戏剧家们越来越承认契诃夫的现代戏剧的拓荒人地位的同时,契诃夫戏剧跨出俄罗斯的国门,走向了世界。而首先在西方世界震撼观众的,竟是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没有父亲的人》(即《普拉东诺夫》)。在一九五七年,法国和比利时的导演先后将它搬上舞台,从此契诃夫戏剧在世界舞台上进入了上演次数最多的经典剧作之列。
与此同时,契诃夫戏剧在俄罗斯也时来运转。在过去,演出契诃夫戏剧乃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专利,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俄罗斯的每家著名话剧院的保留剧目中,几乎都有契诃夫的剧作。
五
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这部戏剧处女作比较陌生,所以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这部处女作,实际上也是少作。契诃夫是在十八九岁时把它写出来的,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剧本写在笔记本上,但直到契诃夫去世十九年后的一九二三年才被发现。原稿无剧名,因听说契诃夫曾写过一个名叫“没有父亲的人”的剧,于是就用它为新发现的剧本命名。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欧诸国竞相上演此剧时,大都以此剧的主人公普拉东诺夫的名字来命名。
那时的欧洲导演对此剧感兴趣,是因为对普拉东诺夫这个戏剧人物感兴趣,认为他就是“当代的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的精神痛苦很容易在西方世界的年轻人那里得到共鸣。
剧中的普拉东诺夫也说起过自己与哈姆雷特的“异同”:“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
普拉东诺夫是个中学教员,但他在周围世界找不到可以交心的对象,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可以献身的力量。于是他只好叹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所应该的那样生活。”如果我们读完《没有父亲的人》之后再读《伊凡诺夫》,就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普拉东诺夫是伊凡诺夫的前身。
中国第一个对《没有父亲的人》感兴趣的导演是王晓鹰。他于二〇〇四年以“普拉东诺夫”的剧名将此剧搬上了舞台。主演是果静林。我问他普拉东诺夫的哪一句台词最让他震撼,他说是“普拉东诺夫在痛”这一句。这一句台词出现在全剧快结束的第四幕第十一场:
格列科娃您哪里痛?
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在痛……
我记得当年翻译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也在隐隐作痛。
《林妖》也是个较为陌生的剧本。契诃夫是如何把《林妖》改写成《万尼亚舅舅》的,可参阅作为附录收入《没有父亲的人·林妖》一书的短文《从林妖到万尼亚舅舅》。
六
哪一部契诃夫剧作最好?肯定会众说纷纭。但如果问:哪一部契诃夫剧作演出最多?答案便很明确:是他的绝命作《樱桃园》。《樱桃园》是世上少有的一部从它诞生直到今天每年都有演出记录的经典剧目。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时代,契诃夫的剧作里也只有《樱桃园》有幸每年都有机会与观众见面。为什么?因为它最适合作社会学评论。试看它的戏剧情节:
为了挽救一座即将被拍卖的樱桃园,它的女主人从巴黎回到俄罗斯故乡,一个商人建议这位女贵族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楼出租。女贵族不听,樱桃园易主。而从拍卖会上拍得这座樱桃园的正是那位建议把它砍伐掉后改建成别墅楼的商人。擅长社会学批评的批评家们随即作出了对于此剧的价值判断:从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了没落的地主贵族阶级。
但半个世纪之后,当全世界的不同民族的观众蜂拥进入各自国家的剧场观看《樱桃园》,难道他们是因为对于一个遥远国度十九世纪末的阶级变动发生了兴趣?显然不是的。
二〇〇五年的一天,我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讲契诃夫,讲到《樱桃园》时,我说起了北京的老城墙,说起了当年为倒塌的老城墙哭泣的梁思成。我说“樱桃园”是个象征,象征那些尽管古旧但毕竟美丽的事物。《樱桃园》写出了世纪之交人类的困惑。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与一些古旧而美丽的事物告别。回家之后,我便写了一篇散文《惜别樱桃园》,文章最后写道:
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纪之交,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的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樱桃园”的就地消失。我们好像每天都能隐隐听到令我们忧喜参半、悲喜交加,令我们心潮澎湃,也令我们心灵怅惘的“伐木的斧头声”。我们无法逆历史潮流,保留住一座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记忆。大到巍峨的北京城墙,小到被曹禺写进《北京人》的发出“孜妞妞、孜妞妞”的声响的曾为“北平独有”的单轮小水车。
谢谢契诃夫。他的《樱桃园》同时给予我们以心灵的震动与慰藉;他让我们知道,哪怕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为什么站在新世纪门槛前的我们,心中会有这种甜蜜与苦涩同在的复杂感受;他启发我们将要和各种各样复杂的、冷冰冰的现代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七
一九三八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世。一九四〇年,聂米洛维奇丹钦科接过战友的导演棒,重排《三姊妹》,头一次对契诃夫戏剧的“种子”,即“主题”作了阐述。要言不烦,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丹钦科的这句“导演阐述”,影响深远。一九九一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总监叶甫列莫夫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排演《海鸥》,就用“对于另一种生活的渴望”这句显然脱胎于“丹钦科名言”的话,来概括《海鸥》的主题。
至于如何解释“海鸥”的象征意义,叶甫列莫夫以为妮娜象征着飞翔着的“海鸥”,而特里勃列夫则象征着夭折了的“海鸥”。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解读。但今年六月初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二〇一一级的学生演了一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海鸥》,导演是来自圣彼得堡的伊凡诺娃。她在《导演的话》里,对“海鸥”的象征意义作了全新的解读:“在为这出戏工作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那只‘海鸥’存在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海鸥’在等待,在呐喊,在跃跃欲试……”
契诃夫戏剧也容许多元解读的。
那么再听听更有人生哲理意味的彼得·布鲁克的解读: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死亡无处不在——对于这个他知道得很清楚——但在这死亡的存在里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因素。死亡的感觉与生命的渴望并行不悖。他笔下的人物具有感受每一个独特的生命瞬间的能力,以及要把每一个生命瞬间充分享用的需求。就像在伟大的悲剧里一样,这里有生与死的和谐结合。
契诃夫创作《樱桃园》的时候,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是在日复一日的顽强书写中,寻找生命的律动。《樱桃园》最后费尔斯说的那句台词“生命就要完结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难道不也是表达了契诃夫本人对于生命的眷恋?
丹钦科强调了契诃夫的乐观主义,彼得·布鲁克强调了契诃夫的生命意识。但无论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还是生命意识,都能打动世世代代的观众的心。
八
现在该说一说中国戏剧家对于契诃夫戏剧的接受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一九三〇年上海辛酉剧社演出了《文舅舅》(《万尼亚舅舅》),主演是袁牧之。距此十四年后,才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执导的《万尼亚舅舅》的辉煌演出。
但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让人感奋的,还是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美质的天才发现。我们今天读曹禺一九三五年在《〈日出〉跋》里写下的这段文字,还感佩不已:
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奥尔加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在江安的国立剧专的讲坛上,曹禺对于契诃夫戏剧的讲解,造就了一批具有心理现实主义思维的戏剧人。
一九五七年,不为人知的中国广播剧团演出了一部轰动京城的《北京人》,导演是曹禺在国立剧专的得意门生蔡骧。很多年之后我向蔡骧先生讨教他排演《北京人》的心得。他说:“要排演《北京人》,就得想到,曹禺是在学习了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之后写作了《北京人》。”蔡先生也是契诃夫戏剧的爱好者。我相信,蔡骧先生是通过曹禺走近和认识了契诃夫,就像焦菊隐先生一再说的他是通过契诃夫认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的导演工作道路的开始是独特的:不是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才约略懂得了契诃夫,而是因为契诃夫才约略懂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引自《契诃夫戏剧集·译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就在焦菊隐在重庆翻译契诃夫几个多幕剧的时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天津,两个刚刚登上戏剧舞台的青年人——黄宗江和于是之却被契诃夫的独幕剧《天鹅之歌》深深感动。于是之读过《天鹅之歌》后说“这个戏写出了演员的辛酸与风骨”,而黄宗江写了篇名为《空台赋》的散文,为契诃夫这部独幕剧叫好。他们两位一直有登台演出这个独幕剧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实现。二〇一二年九月,北京人艺在纪念中国小剧场运动三十周年之际,由濮存昕和何冰两人来演出了《天鹅之歌》,之后何冰还演出了独角戏《论烟草的害处》。但在中国演出次数最多的契诃夫独幕剧还是《熊》和《求婚》。
九
回想十年前的二〇〇四年,这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破天荒地在中国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口号的国际戏剧节。王晓鹰导演的《普拉东诺夫》(《没有父亲的人》)为开幕戏,林兆华导演的《樱桃园》为闭幕戏。
刚刚宣布国际戏剧节开幕的时候,有些记者还发出疑问:契诃夫不是小说家吗?怎么会有契诃夫戏剧节呢?但当戏剧节成功举办之后,这样的疑问就不再有了。
在戏剧节举办过后不久,我和王晓鹰导演应邀到北京图书馆作讲座。主持人说了一句很让我感动的开场白:
五十年前,我们请汝老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小说,今天我们请童道明先生和王晓鹰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戏剧。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破天荒地在中国出版了《契诃夫戏剧全集》。抚今追昔,我们能想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焦菊隐和李健吾这两位可敬的戏剧前辈,是怎样地怀抱着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精神,完成了他们的皇皇译著;与此同时,我们也深信,《契诃夫戏剧全集》的出版,能让更多更多的人认识到:契诃夫不仅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