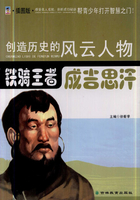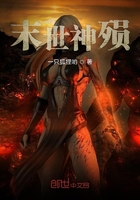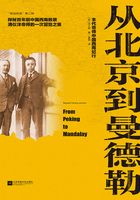现在再介绍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国女教授,她是德国人华兰德小姐,讲授法语。她满头银发,闪闪发光,恐怕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终身未婚。中国人习惯称之为“老姑娘”。也许正因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气有点变态。用医生的话说,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级法语,像是教初小一年级的学生。后来我领略到的那种德国外语教学方法,她一点都没有。极简单的句子,翻来覆去地教,令人从内心深处厌恶。她脾气却极坏,又极怪,每堂课都在骂人。如果学生的卷子答得极其正确,让她无辫子可抓,她就越发生气,气得简直浑身发抖,面红耳赤,开口骂人,语无伦次。结果是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全骂走了,只剩下我们五六个不怕骂的学生。我们商量“教训”她一下。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一齐站起来,对她狠狠地顶撞了一番。大出我们所料,她屈服了。从此以后,天下太平,再也没有看到她撒野骂人了。她住在当时燕京大学南面军机处的一座大院子里,同一个美国“老姑娘”相依为命。二人合伙吃饭,轮流每人管一个月的伙食。在这一个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恶毒咒骂。到了下个月,人变换了位置,骂者与被骂者也颠倒了过来。总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好像吵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内容。
我在上面介绍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概情况,绝没有一句谎言。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我也绝不是说,西洋文学系一无是处。这个系能出像钱锺书和万家宝(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这里无法详细推究了。
1997年12月
终生受用的两门课(本文为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绝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这同他写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我对他的学术论文已经读了一些,比如《四声三问》,等等。每每还同几个同学到原物理楼南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阅读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觉得文体与流俗不同,我们戏说这是“同光体”。有时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走到什么地方去上课,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实(光潜)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当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扞格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身难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1997年12月
我的老师们(本文为季羡林先生《清华园日记》引言节选)
我只谈西洋文学系的老师们。
我的原则仍然是只讲实话,不说谎言。我想遵守古希腊人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不想遵守中国古代一些人的“为尊者讳”的办法以自欺欺人。读者将在下面的日记中看到同样的情况。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时间相距将近七十年,但我对老师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同今天一样,当时北大与清华双峰并峙,领袖群伦。从院系的师资水平来看,两校各有短长。但是专就外文系来看,当年的清华似乎名声在北大之上。原因也极简单,清华的外国教授多。学外文而由外国人教,难道这不是一大优点吗?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我慢慢道来。
我先介绍中国教授。
王文显系主任,不大会说中国话,只说英文,讲授“莎士比亚”一课,有写好的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我们就笔记。除了几个用英文写的剧本外,没有什么学术著作。
吴宓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古貌古心,待人诚恳。在美国留学时,师事白璧德。讲授“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课。擅长旧诗,出版有《吴宓诗集》。我认为,他是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
叶公超英文非常好,中国旧体诗词好像也读过一些。主编《学文》,是属于新月派的一个文学杂志。讲授“大一英文”、“英国散文”等课。没有写什么学术论文。
杨丙辰北大德文系主任,清华兼职教授,讲授“德文”、“浮士德”等课程,翻译过一些德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对待学生极好。
刘文典中文系主任,著有《淮南鸿烈集解》,讲授“大一国文”,一个学期只讲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两篇文章。
金岳霖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一课。
张申府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一课。
朱光潜北大教授,讲授“文艺心理学”一课。
孔繁霱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通史”一课。
下面介绍外国教授。
温德(Winter),美国人。讲授“文艺复兴文学”一课和“第三年法文”。没有写任何学术论文。是建国后还留在北大任教的唯一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
翟孟生(Jameson),美国人,讲授“西洋文学史”一课,著有《欧洲文学史纲》一书,厚厚的一大本,既无新见解,错误又不少。
毕莲(Bille),女,美国人,讲授“语言学”、“第二年英文”等课,不见任何研究成果。
华兰德(Holland),女,德国人,讲授“第一年法文”。患有迫害狂,上课就骂学生。学生成绩好了,她便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艾克(Ecke),德国人,讲授“第二年德文”、“第四年德文”。他在德国大学中学的大概是“艺术史”。研究中国明清家具,著有《中国宝塔》一书,他指导我写学士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
石坦安(Von den Steinen),德国人,讲授“第三年德文”,没有著作。
吴可读(Pollard Urquert),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一课,也没有任何著作。
葛其婉,女,教法文,大概是一个波兰人。
以上就是西洋文学系外籍教师的简略情况。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在那里他们最高能得到助教,或者像德国的Lektor(外语讲师)。中国则一律教授之,此理殊不可解。文学院其他各系并不是这样子的,那里确有术业有专攻的,甚至大师级的教授。可偏偏就是这个西洋文学系,由于外国教授多而驰誉学坛,天下学子趋之若鹜。
2001年11月23日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本文为季羡林先生《清华园日记》引言节选)
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当时这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俗话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济南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
一毕业,就算是走过了独木桥。但是,还要往前走的,特别是那些具备经济条件的学生,而这种人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父母也必千方百计拼凑摒挡,送孩子上学。旧社会说:“没有场外的举人。”上大学就等于考举人,父母怎能让孩子留在场外呢?我的家庭就属于这个范畴。旧社会还有一句话,叫“进京赶考”,即指的是考进士。当时举人进士都已不再存在了,但赶考还是要进京的。那时北京已改为北平,不再是“京”了,可是济南高中文理两科毕业生大约有一百多人,除了经济实在不行的外,有十个人都赶到北平报考大学,根本没有听说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的。留在山东报考大学的也很少听说。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是无法抗御的。
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学校既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大学,我只微闻其名,却没有看到过,因为,它只有几间办公室,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就发给毕业证书。等而上之,大学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学生,但教授和学生水平都不高,马马虎虎,凑上四年,拿一张文凭,一走了事。在乡下人眼中,他们的地位就等于举人或进士了。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燕大也不错,但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收费高,享受丰,一般老百姓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
当时到北平来赶考的举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各省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总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前者是为了报名费,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
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说,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个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惊人,比现在要困难多了。我曾多次谈到过,我幼无大志,当年小学毕业后,对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进了“破正谊”。现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连冠,我的勇气大起来了,我到了北平,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偏偏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经过了一番考虑,为了想留洋镀金,我把宝押到了清华上。于是我进了清华园。
同北大不一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我选的是西洋文学系。到了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我记得,课程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现当代长篇小说”、“英国散文”、“文学批评史”、“世界通史”、“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西方哲学史”等等,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还有“莎士比亚”,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国文”、“逻辑”,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的。“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像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比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后来到了50年代,我同她熟了,笑问她此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我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
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上面列的必修课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读的;但偏又别出心裁,把全系分为三个专业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个学生必有一个专业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选的是德文,就叫作Specialized in German,要求是从“第一年德文”经过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读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说它奇怪,因为每一个学生英文都能达到四会或五会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与英文水平相距悬殊。这一桩怪事,当时谁也不去追问,追问也没有用,只好你怎样规定我就怎样执行,如此而已。
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也许是一个好现象,为其他大学所无,这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个体育项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远、游泳等等,都有具体标准,达不到标准,就算不及格。幸而标准都不高,达到并不困难,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
200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