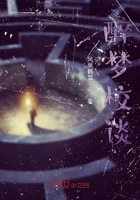罗密欧从楼上的房间里出来,快步跑下楼梯——如此英俊而且活力四射,安妮不由得垂下眼帘。他先是给亚布里尔一个热情实在的拥抱,然后带他来到屋外的庭院中,两人一起坐在一张不大的石凳上。春夜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还隐约有细碎嘈杂的声音,那是成千上万朝圣者在大斋期间罗马的大街小巷中喊叫和交谈。不过最响亮的声音仍然来自城中的教堂,几百只圣钟一上一下同时敲响,宣告复活节即将来到。
罗密欧点上一根烟:“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终于到了,亚布里尔。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将千古流芳。”
他还真把浪漫当回事,亚布里尔觉得很可笑。罗密欧有强烈的个人荣耀感,亚布里尔对此多少有些鄙视。“应该是遗臭万年吧,我们对抗的可是历史久远的恐怖势力。”亚布里尔一边说,一边琢磨两人刚才的那个拥抱。于他而言,这样的拥抱本来纯属礼节客套,但此时却似乎洞穿肺腑,让他回忆起某种恐怖,好像他们是两个弑亲的逆子,就站在刚刚被他们联手放倒的父亲旁边。
庭院的围墙上有一圈昏暗的灯光,不过两人的脸都隐在暗处。罗密欧说:“人们终究会知道这一切是我们干的,但是他们会因此而颂扬咱们吗?还是说,他们会把我们描绘成一群疯子?管他呢!将来的诗人会理解我们。”
亚布里尔道:“我们现在可操不了这个心。”有时候罗密欧有点神经兮兮,这让亚布里尔很不自在,而且忍不住要怀疑这样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成事。其实罗密欧早就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身实力,别看他长得细皮嫩肉,头脑也不太清晰,却是个地道的危险分子。不过这两个人有本质的不同:罗密欧太无所畏惧,亚布里尔则太老谋深算。
一年前在贝鲁特,两人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他们看见路上有个棕色的纸袋,满是食物的油渍,不过似乎已经空了。亚布里尔从旁边绕过去,但是罗密欧却一脚把纸袋踢飞,然后一下接一下地踢,直到它落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毕竟天性不同:亚布里尔相信世上到处隐藏着危险,而罗密欧则天真地信任一切。
两人的差异还不止这些。亚布里尔长得很难看,他生了一双小眼睛,褐色的眼珠如同大理石一般,罗密欧则堪称美男子;亚布里尔因丑陋而自豪,罗密欧却因英俊而羞愧;亚布里尔老早就懂得,单纯的人一旦坚定地投身政治革命,往往会走上杀人之路。罗密欧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个道理,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他勉强接受了自己的转变。
罗密欧的英俊外表让他在情场上颇为得意,其家族财富又保证了他在经济上也一直很宽裕。罗密欧并不傻,知道自家的财富来路不正,所以很快厌弃了生活中的物质享受,转而沉溺于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中不能自拔,这又让他的革命理想更加坚定。自然而然地,他接受了那些教授的极端理论,坚信自己应该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
罗密欧的父亲,一个意大利人,在发廊里做头发花的时间比那些混迹高层的交际花还要多,罗密欧可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也不想用一辈子时间到处寻芳猎艳。最重要的是,他再也不会挥霍那些靠穷人的血汗劳动而获得的财富了。穷人必须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然后他才能感受快乐,他因此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他一生中领受的第二次圣餐。
亚布里尔的转变则是发自内心,彻头彻尾的。他小的时候住在巴勒斯坦,过着伊甸园一样的好日子。那时候他是个很快乐的孩子,聪慧过人,还非常听话——他特别服从父亲的管教,每天要听父亲给自己读一个小时的《古兰经》。
他们的家是一栋豪宅,仆人成群。虽然坐落在沙漠地带,但是他家巨大的草坪却四季常青。在亚布里尔五岁的某一天,他的生活蓦地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深爱的父母忽然人间蒸发,家中的别墅和花园也化为乌有,只剩下一团团紫色的烟尘。突然之间,他就住进了山脚下一个肮脏的小村子,成了靠亲戚接济过活的孤儿。他手头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父亲留给他的那本《古兰经》,这本经书印在上等小牛皮卷上,图案是金灿灿的,文字是漂亮饱满的蓝色。他一直记得父亲高声朗诵的声音,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字字句句都准确无误。真主给予先知穆罕默德的命令都是不容置疑、无可辩驳的。亚布里尔长大之后,曾经对一位犹太朋友说过:“《古兰经》可不是《妥拉》律法。”然后两人都大笑起来。
显而易见,他被逐出了天堂,不过好几年之后他才完全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父亲一直秘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地下运动的头目。父亲被人出卖,在一次警方突袭行动中遭射击身亡。他们家的别墅和花园也被以色列人炸毁,之后母亲也自杀了。
亚布里尔成为恐怖分子的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的亲戚和当地学校的老师都教育他要仇恨所有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教化却不甚成功。他仇恨的是自己的真主,因为要不是他,儿时天堂般的日子不可能说没就没。十八岁,他把父亲的那本《古兰经》卖了一大笔钱,然后去贝鲁特上大学。在大学里,他把大部分钱都花在女人身上,两年以后,他成了巴勒斯坦地下组织的成员。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成为地下运动中屡立奇功的一员猛将。不过争取民族自由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真正的目标是寻求内心的平和。
此时此刻,就在藏身地的庭院里,罗密欧和亚布里尔用了两个多小时把行动计划的每个细节又过了一遍。罗密欧不停地抽着烟,有一件事情令他不安。“你觉得他们会放了我吗?”他问道。
亚布里尔柔声说:“到时候他们要交换我手里的人质,怎么会不放你呢?相信我,你在他们手里比我在舍哈本可安全多了。”
黑暗中,他们最后一次拥抱对方。复活节之后,两个人将再也不会见面。
也是在受难日这天,总统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召集智囊团中的几名高级幕僚和自己的副总统开了个会,并向他们宣布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他是在白宫的黄色椭圆办公室和这群人会面的,这是他最喜欢的房间,虽然不如著名的椭圆办公室名气大,但是更宽敞,更舒服。黄色办公室更像一间起居室,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着,享用英式茶点。
大家已经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看到特勤保镖引领着总统走进来,便纷纷起身迎接他。肯尼迪挥挥手,让大家坐下,同时告诉保镖到房间外面等着。眼前这情景有两点让他心里不快。头一件,按照规矩,他得以个人名义命令特工保镖离开房间。次一件,出于对总统的尊敬,副总统得站着。他之所以感到不快,是因为副总统是个女的,唉,社交礼仪此时就要服从于政治礼仪了。副总统海伦·杜·普雷比他还年长十岁,但仍然相当美丽。她不仅通达世故,而且颇具政治智慧。当然,他就是看中了这几点,才不顾民主党内几位头面人物的反对,将其招至麾下,成为自己的竞选伙伴——这样出色的人还得站着,他更觉得不舒服。
“行了,海伦。”弗朗西斯·肯尼迪道,“我进房间的时候,你就不要站起来了。现在我得给每个人倒茶,以免显得我太狂妄。”
“我想以此表示感激之情,”海伦·杜·普雷说,“你叫副总统来参加你和幕僚的会议,我个人理解是因为总得有人收拾杯子碟子。”两人大笑,但其他幕僚都没有笑。
暮光中,罗密欧在庭院里抽了最后一根烟,他的目光越过石头围墙,看到了罗马一座座教堂的圆顶。然后他走进房间,该给手下交代任务了。
安妮在这个团伙里负责管理枪械,她打开一个巨大的箱子,分发武器弹药。有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铺开一条肮脏的床单,安妮把擦枪用的润滑油和破布搁在上面。他们准备一边擦枪上油,一边听罗密欧介绍情况。他们边听边提问,还把一些动作预演了一下,花了几个小时。安妮把行动服装发下去,大家纷纷拿衣服开起了玩笑。最后,全体人员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是罗密欧和几个男人一起准备的。他们喝着开春的葡萄酒,干了几杯,预祝行动成功,然后其中几个人打了一个小时的牌,才各自回到房间。他们不用派人站岗,为了安全起见,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武器搁在床头。不过,他们还是都睡不着。
安妮敲响罗密欧的房门时,已经过了午夜,罗密欧还在看书。他刚让安妮进屋,她就将他正在看的那本《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把扔在地上,不无鄙视地说:“你又看这本烂书了?”罗密欧耸耸肩,笑道:“这个作家很有趣,他书里的那些人物,就像意大利人一样努力装得一本正经,我觉得特别来劲。”
他们三下两下就脱了衣服,一起仰面躺在脏兮兮的床单上。他们浑身紧绷,并不是因为性冲动,而是出于某种莫名的恐惧。罗密欧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安妮则闭着眼睛。她躺在罗密欧左边,用右手慢慢地、轻轻地给罗密欧手淫。他们的肩膀略略靠在一起,但是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接触。罗密欧勃起了,她的右手动作没停,同时用左手自慰。他们全程都节奏缓慢,其间罗密欧还犹犹豫豫地伸手摸了摸她小小的乳房,但是她像孩子一样一脸痛苦,紧紧地闭上眼。此时她右手攥得更紧、更加有力,撸动的节奏乱了,变得疯狂。罗密欧高潮了,黏糊糊的液体流得她满手都是,此时她也进入高潮,眼睛猛地睁开,瘦小的身体似乎要蜷缩到空气当中。她抬起身,转向罗密欧,好像要吻他,但是忽然又低下头,把脸埋在他的胸口,一直到全身不再抽搐。然后她表情淡定地坐起身,在肮脏的床单上擦了擦手。接着,她从大理石的床头柜上拿起罗密欧的香烟和打火机,开始抽烟。
罗密欧走到卫生间里,把一条毛巾弄湿。然后他回到安妮身边,先给她擦了擦手,又擦了擦自己的。他把毛巾递给她,她接过来擦了擦两腿中间。
执行另外一次任务时,他们也这么干过。罗密欧明白,这是安妮唯一能够接受的亲昵方式。她的独立意识非常强,因此,无论如何她都不能接受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进入她的身体。他也曾建议用口交或者舐阴的方式,但是安妮觉得这仍然算是某种形式的妥协。刚才他们采取的方式既满足她的需要,又不会背叛她坚持独立自主的理想。
罗密欧端详着她的脸,这张脸现在不那么严峻了,目光也柔和许多。她真年轻,他想,她怎么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无情呢?“今晚你想和我一起睡吗,就当作个伴?”他问。
安妮掐灭香烟。“不,”她说,“我干吗还要跟你睡一起?我们不是已经满足了嘛。”她开始穿衣服。
罗密欧开玩笑道:“你走之前至少可以说两句软话。”
她在门口站了一站,转过身来,此时他还以为她会回到床上来。她微微地笑着,他第一次感觉到,她是一个可以去爱的女孩子。然后她好像踮起了脚尖:“罗密欧,罗密欧,为何偏偏是你,罗密欧?”她把拇指放在鼻尖上,冲他做了个鬼脸,走了。
犹他州普鲁瓦市,杨百翰大学。两名学生——大卫·贾特尼和克莱德·科尔已经准备了全套工具,就是为了参加每学期举办一次的传统刺杀猎捕游戏。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这样的游戏又再度流行起来。根据游戏规则,某个学生小组有二十四小时来实施刺杀,他们要用玩具手枪向五步之外的纸板总统人偶射击。除此之外,还有一百来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法律与秩序”兄弟会,阻止他们的“刺杀”行动。游戏结束后,获胜的一方将赢得一笔赌注金,用来举办庆功宴。
因为摩门教的影响,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普遍反对这些游戏,但它们还是在全美国的校园中流行开来——这就是自由社会中过度放纵造成的恶果之一。趣味低下、追求恶俗正在年轻人中蔚然成风。这样的游戏正是他们痛恨权威的最好宣泄,是一事无成者对功成名就者的抗议。这种反抗更具象征意义,而且比游行示威、街头暴力和静坐抗议等活动更受欢迎。猎捕游戏就是一个安全阀门,可以防止这些荷尔蒙旺盛的年轻人制造暴乱。
两名猎人大卫·贾特尼和克莱德·科尔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溜达。贾特尼制订计划,科尔负责执行。所以,正说着话的人是科尔,频频点头的则是贾特尼,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总统人偶走去,此时兄弟会的那帮人正看守着人偶。这个纸板人偶一看就是弗朗西斯·肯尼迪总统,但是用色夸张,蓝西装、绿领带、红短袜,还没穿鞋。应该是鞋子的地方由罗马数字IV替代。
“法律与秩序”一伙人用玩具手枪威胁着两名猎人,于是两人只好绕道走。科尔大声叫骂,以壮声势;贾特尼则板着一张脸,他完全把这个游戏当成了真实任务来完成。贾特尼把他的绝妙计划又回顾了一遍,确信他们最后肯定能成功,这已经让他获得了强烈的满足感。他们故意当着兄弟会的面散步,就是为了让敌人看清楚两人的全套滑雪装备,从而以为他们是准备到校外去度周末的。这样,他们两人随后就可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按照猎捕游戏的要求,总统人偶展示的路线要对全校公布。午夜之前,人偶将被安排在胜利晚宴上展示,贾特尼和科尔准备就在午夜之前实施他们的最后行动。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下午六点,贾特尼和科尔在选定的饭店再次碰头。老板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两个大学生,已经在店里做了两个星期的兼职招待。他们干得非常不错,尤其是科尔,所以老板对两人都相当满意。
当晚九点钟,一百名“法律与秩序”的保护者——都是壮实的小伙子——带着总统人偶走进店里,并派人分头把守住了饭店的各个门口。桌子排成一圈,纸板总统就放在圆圈的中心位置。老板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生意,兴奋得不停搓手。当他走进厨房,看到两名兼职侍者正将玩具手枪藏在汤碗里,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的天哪,”他说,“你们两个今晚就卷铺盖走人吧。”科尔朝他咧嘴笑了笑,但是大卫·贾特尼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们大步走进餐厅,两人都高举着汤碗,把脸遮住。
那些守卫们已经在为胜利干杯了。这时,贾特尼和科尔把汤碗放在圆圈中心的桌子上,一把揭开盖子,掏出玩具手枪。他们举起枪,对着色彩艳丽的纸板总统扣动了扳机。科尔开了一枪,大笑起来;贾特尼早就盘算好了,他连开三枪,然后把手枪扔在地上。他不动也不笑,直到那帮守卫一拥而上,骂骂咧咧地向他表示祝贺,并一起坐下来吃饭,他才露出笑容。贾特尼踢了纸板总统一脚,纸板便滑到地板上,没人注意了。
这一次游戏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在其他地方的大学里,学生们对这个游戏要认真多了,他们不仅会建立严密的保安系统,而且那些纸板还能喷出人造血液。
美国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克里人在华盛顿特区,但是掌握着所有这些刺杀游戏的文件资料。正是贾特尼和科尔活动的照片和内参报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特地在报告上注明,要安排一个任务组,跟踪调查大卫·贾特尼和克莱德·科尔两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