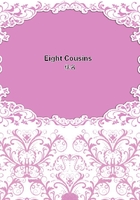看完电影,她沿着莱克星顿大道溜达,因为按照任务要求,她得在公用电话亭中打几个电话。然后她来到一家著名的餐厅,准备小小地犒劳自己一下,结果又被粗鲁的服务员侮辱,更被端上来的模仿拙劣的罗马风味菜式惹怒了。他们怎么敢这样?要是在法国,这样的餐厅老板非被处以私刑不可;要是到了意大利,黑手党会干脆把这样的餐厅烧个精光,还算得上是为民办事。
纽约城将屈辱降临在成千上万的居民和游客身上,现在也想让她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份辱没。因此,餐厅里发生的事对她而言不啻为一种激励。
晚上,她还在闲逛,这是她睡前必需的锻炼。这期间,她分别遭遇了两次强奸或者抢劫的企图。
第一次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着实吓了她一大跳。当时她正在第五大道看蒂凡尼珠宝店的橱窗展示,一男一女——都非常年轻,不超过二十岁——从两边把她摁倒。那个年轻男子的脸长得像只山猫,典型的无药可救的瘾君子。他长得特别丑,而安妮非常看重长相,所以一上来就不喜欢他。那个女孩挺漂亮,但一看就是那种被宠坏的任性美国青少年,这种孩子安妮在街上见过不少。女孩穿得像个荡妇,那是近期电视偶像引领的新潮流。两人都是白人。
那个小伙子狠狠地摁住她,安妮隔着薄薄的外套,能感到有坚硬的金属顶着自己,她并不感到惊惶。
“我手里有枪,”年轻男子小声说,“把你的皮包给我的女朋友。乖乖的,友好一点,只要不惹麻烦,我们不会伤害你。”
“你投票吗?”安妮问。
年轻男子有点分神:“什么?”他女朋友伸手要拿皮包。安妮抓住女孩的手,把她拧到身前当作盾牌,同时又用另一只戴着戒指的手劈面打了女孩一拳。蒂凡尼那装饰典雅的橱窗上突然溅上一大团鲜血,引得行人纷纷惊讶驻足。
安妮冷冷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你不是有枪吗?开枪呀。”这时他手握着口袋里的枪,身体另一侧闪开。这个蠢货曾经在黑帮电影里看过这动作,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姿势完全没用,除非受害者僵住不动。但安全起见,她还是紧紧抓住他的另一只胳膊,一把将其拧脱臼了。他痛得直叫,手也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螺丝刀当啷一声掉到人行道上。果不其然,安妮想,愚蠢的青春期把戏而已,她撇下他们,走开了。
这个时候,谨慎的做法应该是回到她自己的公寓,但是为了熟悉地形,她继续溜达。然后,她走到中央公园南角,那里有一排奢侈酒店,由穿制服的门童守着,一辆辆豪车停在路边,里面坐着健壮的司机。就在这时,她被四个黑人青年团团围住。
几个人长得不错,兴致勃勃,她看着还挺顺眼。他们很像罗马街头的那些年轻混混,个个觉得在街上碰到姑娘就一定得搭讪攀谈,责无旁贷。其中一个小伙子开玩笑地说:“嘿,小妞,和我们一起到公园里走走,你会很开心的。”
他们拦住她的路,她没法继续往前走。她觉得这几个人挺有趣,也知道自己很乐意去开心一下。这几个人并没有惹着她,真正让她愤怒的,是那些门童和司机故意对她这种困境不闻不问。
“走开,”她说,“否则我就要喊了,然后那些门童就会打电话叫警察。”她知道自己其实不能叫,因为可能会因此暴露自己的任务。
其中一个青年咧嘴笑起来:“那就叫呀,女士。”但是她看得出来,几个人都不由得摆好姿势,准备随时拔脚开溜。
看到她并没有尖叫,另一个年轻人马上就明白她并不会喊。“嗨,她不会叫的,”他说,“你们听到她的口音了吗?我打赌她肯定手头有货。喂,女士,给我们也来点。”
他们都开心地笑起来。其中一个说:“要不我们来叫警察算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离开意大利以前,他们已经跟她简单介绍过纽约的危险,但她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行动领队,而且对自己的训练十分自信,所以她拒绝带枪,担心这样会影响他们的行动。不过,她戴了一枚特别设计的水钻戒指,同样可以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而且,她的手提包里还有一把剪刀,比威尼斯匕首还要致命,所以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她只是担心警察可能介入,并且要她做笔录。现在她很有把握自己可以不声不响地安全逃脱。
不过她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紧张和天生的狠劲。一个年轻人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安妮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别挡我的道,你们这些黑小子,否则我杀了你们。”
四个人都不出声了,他们的好脾气也不见了,眼中都露出阴郁受伤的目光。她突然感到一阵悔意,意识到自己犯了个严重错误。她称他们黑小子,并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思,那只是西西里骂人的方式。具体说,就是如果你和一个驼背发生争吵,你就叫他驼背小子;如果和一个跛脚的人争吵,就叫他瘸腿小子。但是这四个青年怎么可能明白这一点呢?她马上想跟他们道歉,但是已经太迟了。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让我给这个白人婊子脸上来一拳。”这时安妮就失控了。她抬起戴戒指的那只手,在他的眼睛上一晃,那儿立即裂开了一道骇人的口子,仿佛将年轻人的眼皮从他的脸上割下来。其他几个青年惊恐地看着,安妮平静地拐过街角,然后跑起来。
这一天对安妮来说真够受的。一回到公寓,她心里就充满自责,觉得自己太过鲁莽,几乎因为一时冲动而坏了组织的大事。她其实是主动找碴,来舒缓自己的紧张。
她不能再冒险了,除了履行与行动有关的必要职责外,她必须待在公寓。她不能再回忆罗密欧,要控制因为他自杀而产生的愤怒。最重要的是,她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切计划都失败了,她是否要采取自杀式袭击。
克里斯蒂安·克里飞到罗马,与塞巴蒂斯奥共进晚餐。他注意到塞巴蒂斯奥有将近二十名保镖,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
这个意大利人情绪十分高昂。“我们的教皇刺客自杀了,这很幸运不是吗?”他对克里说,“否则在我们的左翼势力游行支持下,整个审判都会变成遥遥无期的拉锯战。只可惜亚布里尔没有帮您这个忙,真是太糟了。”
克里大笑:“不同的政府体制罢了。我看你被保护得很严实嘛。”
塞巴蒂斯奥耸耸肩:“我认为他们正图谋更大的行动。我要通知你件事,那个女人,安妮,我们暂时先让她逍遥法外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把她跟丢了,但是我们怀疑她现在就在美国。”
克里感到一阵激动:“你知道她在哪个机场入境吗?她使用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塞巴蒂斯奥说,“但是我们认为她现在正有所行动。”
“你们为什么不逮捕她?”克里斯蒂安问。
“我们准备通过她来放长线钓大鱼,”塞巴蒂斯奥答道,“她是一名意志十分坚定的年轻女人,一定会在恐怖主义行动中大展拳脚。我想用一张大网罩住她。但是你有个问题,我的朋友。我们听到传言,说在美国将有一场大动作,只有可能是针对肯尼迪的。安妮虽然很厉害,但是不可能单独行动。因此,一定有其他人参与。他们在了解你对总统的安保措施之后,接下来采取的行动肯定需要大量的物资和安全藏身地。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情报,你最好马上就着手调查。”
克里没必要再问为什么意大利安保主管没通过正常渠道将这些信息发给华盛顿。他知道,塞巴蒂斯奥不希望自己对安妮的严密监控成为美国官方记录的一部分,他并不信任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而且,他还想让克里斯蒂安·克里欠自己一个人情。
舍哈本。莫罗比苏丹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了克里斯蒂安·克里,就好像几个月前的危机从未发生过一般。苏丹表现得平易近人,但是看上去有几分警惕,还有一点困惑。“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对克里说,“经过这些令人遗憾的不愉快之后,我十分迫切地想要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和你们肯尼迪总统的关系。其实,我希望你的到访能和此事有关。”
克里笑了笑。“我正是为此而来。”他说,“我认为,以您当前所处的形势,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帮助,从而修补两国之间的裂痕。”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苏丹说,“你应该知道的,我并没有暗中参与亚布里尔的图谋,我也无法预知亚布里尔对总统女儿所做的一切。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对此十分悲伤,当然,我已经通过官方渠道传达了这一态度,不过你能私下里再跟总统本人表达一下这个意思吗?我个人无力扭转悲剧。”
克里相信他的话,谋杀并不在最初的计划之内。莫罗比苏丹和弗朗西斯·肯尼迪这样的人虽然有权有势,但因为无法控制他人的意志,竟然会如此无助,这让克里不无感慨。
不过现在他却对苏丹说:“您交出亚布里尔这一行为本身就向总统作了保证。”两人都知道这句话纯粹出于客套。克里沉吟片刻,继续说道:“但是现在我请您私底下帮我一个忙。您知道我负责总统的安全,我得到情报,有人正酝酿刺杀总统的阴谋,而且恐怖分子已经悄悄潜入美国。如果我能知道有关他们的计划、身份和藏身处的消息,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我觉得您有门路,可以通过您的情报部门了解一些情况。您可以给我透露一些信息。让我强调一下,这只限于我们两人,就你和我。不会有任何官方介入。”
苏丹似乎大吃一惊。他那张聪明的脸歪曲成一副难以置信的可笑表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问,“在你们的轰炸之后,在所有这一切悲剧之后,我还会掺和这样的危险行动吗?我是一个富裕小国的统治者,我们国家如果不和超级大国保持友谊,就无力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我既帮不了你,也无法反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