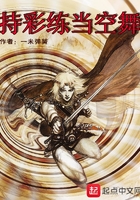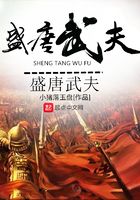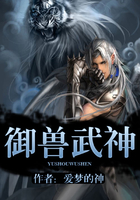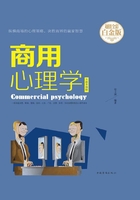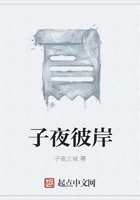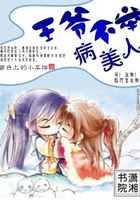冻灾害包括霜灾、冻灾和雪灾,是由低温天气所引起的导致动植物和人类冻损、冻伤甚至冻死的自然灾害,其中较多地表现为无霜期的霜降现象。明清时期,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虽然在“小冰期”内,气候状况有一定的起伏,存在不同的冷暖时段,但从整体上看,清代处于气温相对寒冷的时期。因此,清代的霜冻灾害比较明显。霜冻灾害属于气候变化的异常事件,在发生频次上不像同时期的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多,不过一旦发生,其危害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一、霜冻灾害统计
对于由低温严寒天气带来的灾害,因各朝代发生的具体情况有别,各家的区分方法也不一致。有的把冻灾、雪灾、霜灾合在一起,通谓冷害或冻害,有的则根据各历史时期发生次数的多少,单列为雪灾、霜灾、冻灾等。邓云特先生将清代的基本灾害类型定为旱灾、水灾、地震、雹灾、风灾、蝗灾、歉饥、疫灾、霜雪之灾等九个种类,统计出清代霜雪之灾共计74次。闵宗殿依据《清实录》资料统计,清代共计发生霜灾70次,其中大面积的霜灾占5次;对于雪灾、冻灾则未作统计。笔者依据《清史稿》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霜冻灾害177次,其中霜灾86次,冻灾46次,雪灾45次。关于冻灾和雪灾的区分,这里有必要作一说明。雪灾和冻灾多发生于天气寒冷的冬季,但个别情况下出现在不该发生的季节或月份,比如,据《清史稿·灾异一》: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临淄大雪深数尺,树木冻死;武乡大雨雪,禾稼冻死;沙河大雪,平地深三尺,冻折树木无算。”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通州大雪盈丈。”咸丰八年(1858)七月,“大通大雪厚二尺,压折树枝,谷皆冻,秕不收。”咸丰九年(1859)六月,“青浦夜雪大寒;黄岩奇寒如冬,有衣裘者。”等等。雪灾和冻灾并无明显的区分界限,笔者对两者进行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凡出现“木冰”、“木介”以及天气奇寒但无雪而形成的灾害通划入冻灾,因大雪而导致人畜冻伤、冻死,植物冻损的灾害划入雪灾。
霜冻灾害的发生是考察当时气候寒冷状况的主要依据。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状况的考察,结果表明,清代基本上处于气温相对寒冷的时期,即所谓明清“小冰期”。但有清一代268年,气温的冷暖总会表现出一定的起伏状态,为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了解,现把清代各朝霜冻灾害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一)年际分布
在清代各种自然灾害中,霜冻灾害发生的次数比较少,又过多地集中在某些年份。下面根据霜冻灾害相对集中分布的程度,大致划分出几个较长的时间段,对霜冻灾害的年际分布状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44~1698),共计55年。其间发生霜冻灾害71次,平均每年发生1.29次,年均发生概率为129%。
第二阶段:从康熙三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八年(1699~1763),共计65年。其间发生霜冻灾害48次,平均每年发生0.74次,年均发生概率为74%。
第三阶段:从乾隆二十九年至同治四年(1764~1865),共计102年。其间发生霜冻灾害51次,平均每年发生0.5次,年均发生概率为50%。
第四阶段:从同治五年至宣统三年(1866~1911),共计46年。其间发生霜冻灾害7次,平均每年发生0.15次,年均发生概率为15%。
通过对四个阶段霜冻灾害分布状况的对比,加以各阶段内综合指标的比照,可以看出,清代霜冻灾害在各阶段的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出明显的高发期和低发期峰值,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阶段是霜冻灾害的高发时间段,即顺治年间和康熙三十七年之前的清代前55年,霜冻灾害非常严重。期间发生的71次霜冻灾害占总次数(177次)的40%,而这一时间段才相当于清代268年的20.5%。此阶段霜冻灾害的发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年际分布范围广,55年中有39年发生了霜冻灾害,年覆盖率大大超过其他三个阶段。第二,个别年份霜冻灾害多发、频发。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发生5次霜冻灾害,其中2次霜灾、2次雪灾、1次冻灾,涉及今陕西、山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个省区;康熙三十年(1691)发生霜冻灾害多达6次,其中有3次霜灾、2次冻灾、1次雪灾,涉及今江苏、广东、山西、江苏、湖北五个省地;另有康熙十一年(1672)发生3次霜灾、2次雪灾,顺治十年(1653)发生3次冻灾、1次雪灾等。正是因为这些年份霜冻灾害多发、频发,才使得本阶段霜冻灾害发生的次数上升攀高。第三,本阶段存在一个小型霜冻灾害间歇期,从康熙四年至康熙九年(1665~1670),连续6年没有发生过霜冻灾害。第四,有多次霜冻灾害导致人畜冻伤、冻死,树木、庄稼冻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顺治九年(1652),“冬,武清大雪,人民冻馁;遵化州大雪,人畜多冻死”。顺治十年(1653),“冬,保安大雪匝月,人有冻死者;西宁大雪四十余日,人多冻死”。顺治十一年(1654),“冬,滦河大雪,冻死人畜无算”。康熙三年(1664),“三月,晋州骤寒,人有冻死者;莱阳雨奇寒,花木多冻死。十二月朔,玉田、邢台大寒,人有冻死者;解州、芮城大寒,益都、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寒,人多冻死;大冶大雪四十余日,民多冻馁;莱州奇寒,树冻折殆尽;石埭大雪连绵,深积数尺,至次年正月方消;南陵大雪深数尺,民多冻馁;茌平大雪,株木冻折”。其中康熙三年的两次雪冻灾害危害最大,今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等省数十州县都有民人冻死、冻馁的记录。
第二阶段包括康熙朝后24年、雍正朝和乾隆朝前28年共计65年,是清代霜冻灾害的相对高发期。期间发生霜冻灾害48次,占总次数(177次)的27%。此时期霜冻灾害的年际分布亦不均匀,有连续5年、6年、7年霜冻灾害的多发期,有连续3年、4年、6年无霜冻灾害的间歇期。另外,这一时期发生的霜冻灾害中,有半数为霜灾,记录多为“陨霜杀禾”、“陨霜杀麦”、“陨霜杀稼”等。但也有两次雪灾导致了人畜冻伤、冻毙,一次是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武强大雪,平地深尺许,人畜多冻死”;另一次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丰顺雨雪大寒,人畜冻毙”。
第三阶段时间单位最长,包括乾隆朝后32年、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和同治朝前4年共计102年。这一时段相当于清代268年的38%,所发生的51次霜冻灾害占清代总次数的28.8%,是霜冻灾害发生频次相对较低的时期。因为时间段长,霜冻灾害在年际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和无规则性表现比较明显。如从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年(1767~1785)连续19年无霜冻灾害发生,从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年(1821~1830)连续10年无霜冻灾害发生,这是两个时段较长的霜冻灾害间歇期;而从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元年(1786~1796)11年间发生了14次霜冻灾害,从道光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31~1842)12年间发生了11次霜冻灾害,这是期内两个霜冻灾害发生比较频繁和集中的时段。而在这100年间,因霜冻灾害导致人畜冻伤、冻死的记载有5个年份,分别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二十一年(1841)、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四年(1865),而第一阶段的55年中,有11个年份出现了人畜冻伤、冻死的记录,说明这100年间霜冻灾害特别是雪灾、冻灾的危害没有清代前五、六十年严重,同时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气候寒冷状况没有清代前期严重。
第四阶段即同治朝后9年及光绪、宣统年间是清代霜冻灾害的绝对低发期。本阶段共计46年,和第一阶段55年仅相差9年,只发生7次霜冻灾害,占总次数(177次)的3.95%。期间发生霜冻灾害的年份只有6个,分别是同治九年(1870)、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二年(1876)、光绪七年(1881)、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中光绪二年发生2次霜冻灾害(1次霜灾、1次冻灾),其他年份均为1次。这一阶段不但霜冻灾害发生次数少,而且所发生的灾害亦未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冻伤、冻死人畜的记录。
通过对四个阶段各项指标的综合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霜冻灾害的发生,从前期到后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递减情态。清代177次霜冻灾害有67次发生于17世纪的清代前55年,占总次数的38%,而55年的时间仅相当于清代268年的20.5%,说明清代前55年霜冻灾害的发生频次明显偏高。霜冻灾害属于低温所导致的气象灾害,根据竺可桢、任振球等人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五个低温期,17世纪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国最冷的期间是17世纪,特别是以公元1650~1700年最冷”。在低温期内,往往发生百年一遇的严冬、大早、大涝等严重灾害。清代前期频繁发生的霜冻灾害,也是当时最为直接的气候资料,这些统计数据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上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同时也和“明清宇宙期”(1500~1700)内气温偏低的理论相符合。
(二)月份与季节分布
如前所述,在霜冻灾害中,冻灾和雪灾多发生于天气寒冷的冬季,但由于天气变化复杂多端,个别年头也会出现在不该发生的季节或月份。比如冻灾,在清代所发生的46次冻灾中,有9次冻灾的发生属于异常,游离于年内寒冷期之外,出现在三至七月间天气应该比较温暖的时期,这些年头分别是康熙三年(1664)三月、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嘉庆三年(1798)五月、嘉庆十四年(1809)立夏前三日、嘉庆十九年(1814)秋、同治元年(1862)六月、光绪二年(1876)五月,发生次数占冻灾总次数的19.6%。雪灾的发生有13次属于异常,出现在三至九月间天气应该比较温暖的时期,这些年头分别是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和六月,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康熙五十七年(1718)七月、乾隆八年(1743)七月、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咸丰八年(1858)七月、咸丰九年(1859)六月,发生次数占雪灾总次数的28.9%。清代冻灾和雪灾发生的这些年份,说明当时气候异常、气温偏低。不过,也不能因为冻灾和雪灾发生在冬季月份,就表明该年的气候冷暖状况正常。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多雪本为正常现象,但因严寒和大雪而形成灾害,导致人畜冻伤、冻死,亦是少见的非正常现象。所以,凡是冻灾和雪灾发生的年份,均属于气温偏低的气候异常时期。
霜灾是指发生于无霜期的寒冷气候现象和霜期内的气候异常现象。霜灾的主要危害是导致农作物受损,诸如“陨霜杀麦”、“陨霜杀禾”、“陨霜杀稼”等,对人类和牲畜的生存虽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危害后果不及冻灾和雪灾严重。同时,在月份和季节分布上也表现出与冻灾和雪灾不尽相同的特征。
季但月份季节不明,其他84次均有明确的月份记载。其分布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从季节分布看。秋季是霜灾的高发季节,38次霜灾占四季总次数的44%;夏季是霜灾的第二个高发季节,32次霜灾占四季总次数的37%;春季共发生霜灾16次,占四季总次数的19%;冬季没有发生过一次霜灾,是清代霜灾的绝对低发季节。
霜灾主要是指发生于无霜期的寒冷气候现象。无霜期是指一个地方春天最后一次霜降至秋季最早一次霜降之间时间段,霜期是指入秋后第一次出现早霜至第二年春天最后一次出现晚霜之间的整个时段。我国虽然整体上都处在北半球,但南北间距长,横跨纬度大,气候状况复杂,所以,南北方各地霜期长短差别很大,一般来说,纬度愈高、海拔愈高的地区霜期愈长。
在霜期内每天都有出现霜降的可能,这是正常的气候现象。但是因霜降而致农作物受损,形成灾害,则是不正常的现象。秋季本属于霜降期,清代秋季发生霜灾的次数占了四季总次数的44%,说明这些年份秋季的气候状况异常、气温偏于寒冷。夏季属于无霜期,是春季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期,这时出现霜降,一般来说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霜冻的温度指标一般认为是气温在一摄氏度或者地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清代夏季发生32次霜灾,占了四季总次数的37%,说明这些年份霜灾发生地的夏季气温明显偏低。清代春季发生16次霜灾(占四季总次数的19%)以及冬季无霜灾发生,这不论从霜灾的生成机制比如孕灾的气候环境来看,还是从历史上霜灾的季节分布来看,都应属于正常现象。
第二,从月份分布来看。清代霜灾的月份分布极不均匀,4、8、7月份是清代霜灾的高发月份,分别发生21次、20次、16次霜灾,占总次数的百分比依次为24.4%、23.2%、18.6%。10、11、12月份属于冬季,没有发生过一次霜灾。3、5、6月份分布发生霜灾8次、6次、5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3至8月份是清代霜灾的6个高发时段,各月份发生次数的多少因各地气候冷暖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他6个月份(9、10、11、12、1、2月份)是清代霜灾的低发时段,共计发生8次霜灾,仅占总次数的10.5%,且集中在1月份(康熙十二年、康熙五十年共2次)、2月份(康熙四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咸丰九年、同治九年共4次)、9月份(康熙三十六年、乾隆十六年共2次)。这些月份出现的霜冻,一般来说,对农作物的生存不会有致命的打击,但既然形成了灾害,则说明这些月份的气候状况有别于常年,应该相对寒冷。
三、霜冻灾害空间分布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清代霜冻灾害的发生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霜冻灾害本身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气候资料,清代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各地气候状况因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下面再对清代霜冻灾害的空间分布情状进行分析考察,以便寻找出这种灾害类型的高发省区,为现代的防灾抗灾实践提供历史性的参考和借鉴。
如果按照现代行政区划统计,除去灾发地未详的记录,清代所发生的霜冻灾害涉及各省市共计205次,分布在20个省市中。根据各省市发生频次的高低,依次为山东34次、河北28次、山西24次、浙江20次、湖北16次、江苏16次、陕西15次、安徽12次、甘肃12次、广东7次、上海7次、河南4次、宁夏2次、青海2次、江西1次、天津1次、贵州1次、云南1次、重庆1次、内蒙古1次。为了直观地反映各省市霜冻灾害发生的频次及相互之间的对比关系,请参看下面的图示。
由上面的文字所提供的数据和图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山东、河北、山西、浙江、湖北、江苏、陕西、安徽、甘肃等9省区是清代霜冻灾害的高发地区,9省区共计发生霜冻灾害177次,占了总次数的85%,其他11个省市共计发生霜冻灾害24次,仅占总数的15%。从自然地域来看,霜冻灾害高发的省份基本上都处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两个霜冻灾害高发的自然地带。前文已经说明,这里所谓霜冻灾害实际上包括霜灾、冻灾、雪灾三种灾害类型。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所以霜灾、冻灾、雪灾发生的频次较高,究其原因,这些地区除了具备发生此类灾害的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外,其所在省区多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大省,有关自然灾害的记录较为详细,也是原因之一。至于南方一些省区,从冬季到早春,真正的冰冻天气、雪灾有但并不多见,倒是常有霜降天气袭击,有时候还会形成霜冻灾害,对农作物构成威胁。如广东、云南、贵州3个南方省份,《清史稿》共记录9次霜降和大雪成灾的情况,其中广东7次、云南、贵州各1次。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云南鹤庆“陨霜杀麦”;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贵州贵阳“陨霜杀稼”。这两次均为霜灾。广东省有4次霜灾记录,分别是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乐安陨霜杀麦”;康熙三十年(1691)六月,“龙川陨霜杀禾”;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潮阳陨霜”;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龙川陨霜杀禾”。其中康熙五十年正月,只载“潮阳陨霜”而无损害庄稼的描述,似乎危害不大。广东省还在康乾年间发生3次雪灾,分别是: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高州大雪”;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二月,“三水大雪,树俱枯;海阳大寒,冻毙人畜;揭阳大雪杀树;澄海大雨雪,牛马冻毙”;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丰顺雨雪大寒,人畜冻毙”。其中康熙十九年仅载“高州大雪”,后果似不太严重,但后两次雪灾均造成了人畜冻毙的严重后果,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的雪灾还波及广东三水、海阳、揭阳、澄海4个县地,这在南方是非常少有的现象。
第八节
疫病灾害疫病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相随的灾害。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疫灾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先民,带给我们祖先触目惊心的苦难。从我国历史上流传的疫病来看,其种类非常多,除常见的痢疾、伤寒、天花、麻疹、结核病、狂犬病、恙虫病、麻风病等外,明清以来,真性霍乱与鼠疫流行也造成深重的灾难。不论是哪一种疫病,倘若大规模地流行蔓延,都会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被可怕的疫病夺去生命,恐怕无人能够计算清楚。揆诸文献,诸如“疫死者几半”、“人死无算”、“死者不可计数”、“疾疫死者以万数”等记载可谓不绝于书;透过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我们可以想象到疫病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是多么惨重。
一、疫灾概况
据邓云特先生研究统计,我国历史上较大的瘟疫在各朝代中的分布如下:秦汉13次,魏晋17次,南北朝17次,隋唐17次(隋1次、唐16次),宋32次,元20次,明64次,清74次。其中清代发生次数为最多,从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来看,瘟疫的发生频次呈逐渐上升之势。龚胜生认为,在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春秋至清朝之间(前770~1911)的2681年中,共有疫灾之年669年,平均疫灾频度25.0%,即平均每4年有一年发生疫灾。在总共669个疫灾年份中,魏晋南北朝、明朝、清朝这三个时期发生疫灾的年份最多,分别占总年份的11%、25.3%、32.6%,三个时期共占疫灾总年数的69%。就疫灾频度而言,魏晋南北朝和北宋约20%,南宋和元朝约33%,明朝为61%,清朝近82%。总体上看,中国疫灾的流行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只是这种趋势不是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上升。宋正海、高建国等根据正史、方志以及医书、笔记杂录等各种资料,对我国自公元纪年起至辛亥革命期间的大疫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期间发生范围大、死亡重的瘟疫共有266起,其中公元纪年之初至北宋灭亡的1126年中,累计发生大疫68起,平均16.6年发生1起。而自南宋建立至清王朝覆亡的短短758年中,竟发生了大疫近200起,平均每3.9年便有1起。如果分开统计,则可以看出:南宋、金、元自1127年至1367年的240年中,共发生大疫36起,平均6.7年发生1起;明代自1368年至1644年的276年中,共发生大疫53起,平均5.2年发生1起;清代自1644年至1911年的268年中,共发生大疫109起,平均2.5年便有1起大疫流行,“充分显示了我国历史上的疫情,有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亡而呈不断频繁、加剧之势”。闵宗殿依据《清实录》资料统计,清代共计发生疫病灾害仅10次,其中大面积的疫灾占3次;这个数字说明了《清实录》记载之缺略。笔者依据《清史稿》统计,清代268年间共发生疫灾176次,分布在101个年头,平均每年发生0.66次,年均发生概率为66%。兹将清代疫灾状况。
二、疫灾时间分布
(一)疫灾年际分布
从整体上看,清代疫灾在年际分布上极不均匀,表现出较大起伏状态。下面依照其分布集中的程度,对清代疫灾进行阶段性考察。
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三十年(1644~1691),共计48年。其间共发生疫灾18次,分布在13个年份,有35个年头无疫灾发生,平均每年发生0.375次,年均发生概率为37.5%。
第二阶段: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1692~1735),共计44年。其间共发生疫灾51次,分布在24个年头,年际分布较广;平均每年发生1.16次,年均发生概率为116%。其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一年发生5次疫灾,为清代疫灾年发生最高次。
第三阶段: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36~1782),共计47年。其间共发生疫灾20次,分布在11个年头,平均每年发生0.425次,年均发生概率为42.5%。
第四阶段:从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83~1820),共计38年。其间共发生疫灾25次,分布在18个年头,平均每年发生0.657次,年均发生概率为65.7%。
第五阶段:从道光元年至同治十年(1821~1871),共计51年。其间共发生疫灾57次,分布在30个年头,年际分布较广;平均每年发生1.11次,年均发生概率为111%。
第六阶段:同治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72~1911),共计40年。其间共发生疫灾5次,分布在5个年份,有35年无疫灾发生;平均每年发生0.125次,年均发生概率为12.5%。其中光绪朝34年,仅有1年发生了疫灾,为光绪三年(1877)。
综上可以看出,清代疫灾的阶段性对比和年际分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清代疫灾的年际分布极不均衡,呈现波浪式起伏状态,而且波动幅度较大。第二阶段和第五阶段是清代疫灾的高发期,即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朝是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是又一个疫灾严重的时期;两个阶段共计95年的时间发生了106次疫灾,占清代疫灾总数的60%多。第六阶段是清代疫灾的绝对低发期,即光绪年间疫灾发生频次最低;清代最后40年总共才发生5次疫灾,而光绪朝34年只有1次疫灾发生,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第一阶段是清代疫灾的相对低发期,即清朝前48年疫灾危害相对较小。
第二,每一阶段的疫灾分布也不均匀,呈现出一定的起伏状态,相对集中在某些年份。在第二阶段疫灾高发期内,从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02~1710),9年中发生了22次疫灾,从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三年(1729~1735),连续7年只有1次疫灾发生。在第三阶段中,从乾隆元年至十年(1736~1746),连续11年只有2次疫灾发生,从乾隆十五年至乾隆二十年(1750~1755)连续6年、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1~1766)连续6年、从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76~1782)连续7年无疫灾发生。其他阶段也多存在此类情况。
(二)月份与季节分布
从以上对清代疫灾的阶段性考察可以看出,清代疫灾的年际分布极不均衡,具有非常明显的高发期和低发期时段。疫灾往往是由其他自然灾害及气候异常所致,其中多数与水旱等灾害密切相关,水旱灾害在月份及季节分布上的突出特点是明显集中在某些季节或月份,则疫灾应具有与之相类似的特征。曾有学者说过:“疫灾具有传播性,不仅不同地区发生疫灾的时间不同步,就是同一地区也可能在一年之内多次流行,从全国范围来看,疫灾往往要绵延数月乃至数年之久,这样,对疫灾进行季节分析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对于不同地区疫灾发生的不同步性以及疫灾往往具有传播性、持续性、复发性的特点,笔者表示非常赞同。但若说对疫灾进行季节分析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观点,实在难以让人苟同。其实,不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域来看,疫灾的发生都较为明显地集中在某些季节或月份,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灾害种类。而如果能认识和了解疫灾的年内分布规律或大致趋势,对疫灾的预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季节上看,清代疫灾主要发生于夏、秋两季,春季和冬季相对较少。夏、秋两季共计111次疫灾,占总次数(162次)的68.5%;其中夏季发生疫灾68次,是四季中疫灾发生频次最高的季节。春、冬两季共计51次疫灾,占总次数的31.5%;其中冬季发生疫灾16次,是四季中疫灾发生频次最低的季节。从发生频次的高低,四季的排序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
第二,从月份上看,3~8月是清代疫灾的多发期,这6个月共计发生疫灾86次,其中5月、6月是疫灾发生高峰月份,两个月合计发生疫灾多达42次,几乎占了这6个月86次的一半;5月份发生疫灾22次,是清代疫灾发生次数最高的月份。其余6个月疫灾发生频次较低,共计21次,其中10月份1次、11月份3次、12月份2次,这三个月疫灾发生次数最少。
疫灾之所以多发生在夏秋两季,特别是5、6、7三个月为高峰月,主要是因为这个时节从气候因素上看,“暑湿”二气严重,适合细菌的滋生繁殖和疫病的传播。如一些医书中指出:“夏秋暑湿二气为病最伙。”清代无名氏《平寇纪略》言:“夏秋之暑湿熏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葬亦开千人坑埋之。”当时医药局的送诊施药活动也多是在夏秋两季进行,一般为五月开局,八月收局。比如,民国《续丹徒县志》卷一四《人物志·义举》载:“每年五月十六日开局,至八月十六日止。”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三《营建·善堂》载:“(医局)六月朔起,八月十日止。”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疫灾在各月份的分布状况,以及各月份的次数所占总次数的百分比情况,下面以有明确月份记载的疫灾次数为依据,以备参照。
三、疫灾空间分布
按现代行政区划统计,除去发生地未详的记录,清代疫灾共计222次,在各省市的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浙江34次、山东33次、湖北32次、河北27次、江苏16次、甘肃12次、陕西9次、安徽9次、上海9次、山西8次、广东6次、河南6次、江西5次、北京4次、广西3次、宁夏2次、海南2次、云南1次、辽宁1次、黑龙江1次、吉林1次、台湾1次,其他省市无发生疫灾的记录。
清代所发生的疫灾分布在今天22个省市中,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清直隶)、江苏五省是疫灾的高发省份,五省共计发生疫灾142次,占了总数的64%;其中浙江省疫灾发生频次最高,共有34次疫灾。广西、宁夏、海南、云南、辽宁、黑龙江、吉林、台湾等省是疫灾发生频次较低的省份,最高纪录为3次,多数为1次;这八个省份共计发生疫灾12次,仅占总数的5.4%。四川、天津(清属直隶)、贵州、青海、重庆(清属四川)、湖南、新疆、福建、西藏、内蒙古等省市,没有1次疫灾记录。这是因为《清史稿》本身记载的缺漏,实际上,只要稍微查阅一下各省方志,就不难发现,湖南、福建、四川、云南等省在清代均有疫灾发生。但是,即便考虑到史料本身记载的缺漏,各省疫灾发生频次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这说明了清代疫灾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关于中国疫灾的空间分布格局,余新忠等人在《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书中,根据《明史》、《清史稿》、《古今图书集成》、《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等书中资料,对中国近世(1573~1948)疫情空间分布作出统计,按照发生疫灾的次数,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山东(83次)、湖北(58次)、河北(56次)、浙江(50次)、江苏(40次)。宋正海等人依据正史、方志、医书、笔记、杂录等多种资料,对中国历史上(从商朝至清代)发生大疫最多的地域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在他们所搜集到的385条大疫史料中,清代占了263条,按现代行政区划计算,大疫发生次数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山东(38次)、浙江(28次)、河北(23次)、湖北(19次)、江苏(15次)。笔者依据《清史稿》统计,清代疫灾发生频次排在前五位的省份是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这和余新忠、宋正海等人统计出的五个省完全相同,仅在名次上有先后之分。因此,可以说,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等五省作为清代疫灾的高发省区,由《清史稿》得出的这一研究结论,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疫灾成因与后果分析
(一)疫灾成因探讨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疫病(或称瘟疫)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解释疫病为“具有温热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性的一类疾病”。那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认为:“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所谓疫灾是指由疫病所导致的灾害,即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给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带来的一切危害。
根据现代医学的解释,导致疫病发生的致病微生物或寄生虫多种多样,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这些微生物或寄生虫的存在是自然界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环扣,也是影响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化的时间线路上,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各种微生物、寄生虫与人类保持着长久的和平共处,当这种共存的状态失去均衡,则说明自然生态链发生了变化,这时,微生物或寄生虫便会向人类发动进攻。可见,致病微生物或寄生虫等病原体的普遍存在,是疫病发生的最基本因子。但是,这些因子只要不作用于人体,仍然不会产生疫病。关于传染病形成的条件,现代医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其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不过,要促成这些条件的广泛存在并最终导致疫病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因素,在多数情况下,是自然和社会的复合因素。比如,气候的异常、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大规模的政府行为如战争造成生存环境的破坏等等,都有可能引发疫病或使疫病进一步传播。从历史上看,每个朝代疫病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各不相同,但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而酿成灾难,其基本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传播渠道、危害后果等则大致相同。
1.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存在着伴生、衍生、派生关系
从历史上考察,疫灾多数与其他灾害密切相关,尤其是水旱灾害。民间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说明某些疫灾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次生灾害。在我国传统自然灾害中,水旱灾害发生频次最高,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最大,清代表现尤为突出。水灾特别是江河决溢不但在短时间内造成人口直接死亡,而且水漫之处,积水经久难消,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引发饥荒进而缘生疫病;同样,由于淫雨历时良久而形成的水潦之灾也会引发这样的后果。另外,水灾还会造成水质的严重污染,而潮湿肮脏的环境又为细菌的繁殖和一些有害生物的孳生提供了便利,成为某些传染性疾病的诱因。关于水灾尤其是江河洪涝灾害容易引起疫病流行的原因,宋正海、高建国等人分析认为,“一是将传染病发生区的病原菌冲进河流,通过水源广泛传播;二是将土壤深层的病原菌冲至土壤表面,增加传染病发生的机会;三是某些昆虫大量繁殖,成为传播疫病的媒体。”与水灾相比,旱灾持续的时间往往较长,史书中常有某地长达数月、半年甚至一年无雨的记载。长期的干旱导致庄稼绝收或减产从而引起饥荒,大旱则导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由此引发瘟疫而在长时期内致使灾民大量死亡。下面以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饥荒等为例,来说明疫灾与这些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度和契合性。
水灾与疫病:康熙七年(1668)七月,河北内丘发生水灾与疫灾,《清史稿·灾异志三》:“七月……内丘霪雨,淹没民舍”;《清史稿·灾异志一》:“七月,内丘大疫”。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铜山自三月份起霪雨连绵,持续五个月,六月份遭受疫灾,《清史稿·灾异志三》:“铜山霪雨凡五月”;《清史稿·灾异志一》:“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道光十一年(1831),浙江永嘉五月份因大雨水而歉收,秋季发生瘟疫,《清史稿·灾异志三》:“五月,永嘉大雨水,歉收”;《清史稿·灾异志一》:“秋,永嘉瘟”。同治元年(1862),登州府属蓬莱、黄县、福山、招远、莱阳、宁海等地七月份遭受水灾,秋季发生大疫,《清史稿·灾异志三》:“七月,蓬莱、黄县、福山、招远、莱阳、宁海大雨连绵,禾稼尽淹。”《清史稿·灾异志一》:“秋……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乾隆三十六年(1771),“泗州水,大吏檄善富往赈之,厘户口之弊,民受其惠。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绝荤祈禳”。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安徽泗州继水灾不久,又遭“大疫”。嘉庆时期,直隶威县知县陈念祖,以治伤寒、瘟疫知名,曾著有《伤寒金匮浅注》。嘉庆中,“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很显然,这次大疫是因水灾而致。另据光绪《江安县志》卷四《祥异》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位于长江上游干流的四川省江安县,“大水入城,三旬始消,是岁大饥瘟疫”。据同治《德化县志》卷五十四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江西德化“夏,大水,民多灾疫”。再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水复大至,暴雨风三日夜,平地涌起数丈,村落漂没……其有就食扬州,舍于河干,席屋土门,上蒸下湿,疠疫交作……”
旱灾与疫病:康熙四十九年(1710)秋季,浙江湖州发生旱灾与疫灾,《清史稿·灾异志四》:“秋,湖州、台州、仙居旱”;《清史稿·灾异志一》:“秋,湖州疫”。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季,浙江永嘉发生旱灾与疫灾,六月份、七月份又发生地震、风灾,《清史稿·灾异志四》:“春,永嘉旱”;《清史稿·灾异志一》:“春,永嘉大疫”;《清史稿·灾异志五》:“六月十四日,永嘉地震”;《清史稿·灾异志三》:“七月十四日,永嘉大风雨,坏孔子庙及县署。”六、七月份的地震、风灾,应该和春季的旱灾、疫灾无必然的联系,但春季的旱灾、疫灾的发生则应存在一定的缘生关系。一年之内,浙江永嘉数灾同发,真可谓多灾多难的一年。又据光绪《川沙厅志》载:雍正十一年(1733),继上年发生潮灾后,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夏旱,大疫,死亦无算”。道光《遂溪县志》卷二载:“(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连岁,更经海寇蹂躏之后,复并瘟疫。耕者皆废,迫于追呼,死徙流离,荒残日甚,难乎其为邑矣。”
虫灾与疫病:据光绪《归安县志》卷五十二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浙江归安“夏,旱,蠓灾,大疫”。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五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东胶州“秋,大疫。有蝇自北结阵而南,所止疫作,全家没,村落成墟,后投海死,潮出成堆”。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四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浙江桐乡“四月,霪雨,异虫害春花,民大疫,死者枕藉”。民国《太仓州志》卷二十八载:乾隆二十年(1755),江苏太仓“大水,虫败禾,稼几尽。冬疫,并延至第二年春疫”。同治《弋阳县志》卷十四载:道光十五年(1835),江西弋阳“七、八月间,蝻生遍野,疫疠死者不可数计”。宣统《永绥厅志》卷一载:光绪十四年(1888),湖南永绥“秋八月,瘟疫大行,白日飞蛾浮水数万,饮水者立毙”。
地震与疫病:地震尤其是大震往往导致人员大量伤亡,使得尸体以及伤口成为病菌生长繁殖的理想场所;震后生活条件的恶化如食品、饮用水匮乏等,使受灾人群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病菌,进而造成大面积疫病爆发。比如,据道光《昆阳州志》卷二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云南昆阳“二月初二日,地大震,至十六日复震。是岁,疫疾流行,米价腾贵”。雍正《景东府志》卷三载:雍正六年(1728),云南景东“四月,地震,西南隅邦匾尤甚。是年灾疫遍染,合景皆然,猛统、大井死者倍也”。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十五载:咸丰三年(1853),江苏“宿迁县三月地震,大饥,疫”。同治《金乡县志》卷十一载:山东金乡“咸丰三年三月八日子刻地震,民饥疫多死者”。民国《茌平县志》卷十一《灾异志·天灾》载:山东茌平“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地震,秋多痧症,医药不及死者无数,城市尤甚,人畏传染不敢庆吊”。
饥荒与疫病:史书中因饥荒而引起疫病的记载最多。饥荒本来就是由水旱等自然灾害而引起,又进而缘生疫病灾害,形成所谓“灾害链”。比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季,陕西富平发生饥荒和疫灾,《清史稿·灾异志五》:“夏,富平、盩厔、泾阳饥”;《清史稿·灾异志一》:“六月,富平疫”。乾隆十三年(1748)夏,山东福山等地发生蝗灾、饥荒、疫灾,《清史稿·灾异志一》:“(夏)诸城、福山、栖霞、文登、荣成蝗”;《清史稿·灾异志五》:“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清史稿·灾异志一》:“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浙江永嘉因大雨而导致歉收,秋季发生瘟疫,《清史稿·灾异志三》:“五月,永嘉大雨水,歉收”;《清史稿·灾异志一》:“秋,永嘉瘟”。在一些温病学著作特别是地方史志中,则更多地记载了由饥荒引发疫病的实例。据邵登瀛《温毒病论》载:乾隆二十年(1755),“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
由上面的例证足可说明,诸多疫灾的发生都和灾荒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并不是说每一次大灾都会导致疫病的发生,更不能说所有疫病灾害均由灾荒引起。那么,疫灾的发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灾荒因素的影响呢?一些学者曾就地方瘟疫和灾荒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为我们研究此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如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中,依据地方志资料,对清代江南宝山、常熟、高淳、慈溪、嘉善等五地瘟疫发生的次数进行统计,并就其原因进行分析考察,结果表明,“由灾荒引起的瘟疫占到瘟疫总数的62%,如果刨除不详(指原因不详——引者)部分,则为81%,可见,在清代江南,绝大多数瘟疫的发生都与各类灾荒有关,特别是水灾和风潮等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各地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会受到当地经济、人口、环境等众多因素的不同影响,余新忠的研究结论只是区域性疫病原因的特征,我们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由灾荒因素带来疫病发生,其几率之大,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该怎样理解疫灾与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伴生、衍生、派生关系呢?其最简单的推论是:自然灾害发生后,灾民的生活突然在瞬间发生巨大变化,从正常生活的家庭沦为临建中的灾民,一时的饮水、食品困难,缺乏加热熟食的条件等,增加了传染病感染的机会。现代医学工作者认为,自然灾害与疫病之间的缘生关系主要表现为,灾害发生后,传染病发生、流行与控制的基本条件突然恶化,具体表现是:(1)多样性传染源的普遍存在,是在自然灾害后应特别警惕的。(2)灾害发生后,人群暴露于危险因素中,环境严重破坏污染,昆虫媒介大量孳生,各类传播途径都在传播病原体。(3)灾民们惊恐、悲痛、心理创伤,又瞬间失去正常生活条件,衣、食、水、住顿时无着,人群免疫水平急剧低下,对传染病的易感性增强。(4)灾发地区医疗卫生、疾病控制专业机构遭到破坏,专业人员伤亡失散,对传染病失去早期发现与早期控制的能力。(5)防治传染病及消毒杀虫的药品、器材、疫苗临时奇缺。
2.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与瘟疫的发生蔓延
疫灾既是天灾,又是人祸。说是天灾,是因为疫灾是病原体侵袭人体引起的生物灾害,是由自然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所导致,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其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非人力所完全能够控制。但另一方面,疫病在人群中的爆发流行又与一定人为因素相关,其中战争就是引发和加重疫病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战争不仅直接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且遍地腐尸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进而引起疫病流行。如据同治《饶州府志》卷三十一载:同治二年(1863)七月,“鄱阳被寇灾,各村大疫”。又据徐元龙《永定县志》卷一《大事志》载:同治四年夏秋,永定城乡因遭乱后尸骨遍地,夏秋之交遂生大疫。对此,清代一些医家曾论述道:“大疫之沿门阖境,传染相同者,多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另外,连年的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持续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兵民体质下降,也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当各种因素积聚在一起,战争波及地尤其是战场就成为疫病爆发的大本营。如据《清史稿》记载,咸丰八年(1858),刘培元率领清军水路合攻吉安太平军,“是年冬,军中大疫”。这次军中疫病,疫情未详,但既言“大疫”,则应相当严重。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扰我台湾,生番滋事;七月,清政府派唐定奎率军前往台湾,“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
以上所列举两例军中疫病,由于流布面不大,危害后果尚不算太严重。如果是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由此而引发疫病,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咸丰、同治之际,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一场规模罕见的大瘟疫。这次大疫始自咸丰十年(1860),于同治元年(1862)达到高潮,至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才渐趋平息,持续时间长达四、五年。瘟疫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侵袭到兵营。关于军中疫情,史书记载曰:咸丰十一年,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统清兵五千人防徽州,“寻移防宁国,值大疫,悍贼麕集,与霆军力拒之”。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所部清兵进攻江宁太平军,夺秣陵关、大胜关要隘,“会秋疫大作,士卒病者半”;清军主力会攻金陵,“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总兵刘松山与易开俊“守宁国,大疫,士卒多病”等。曾国藩在该年闰八月初四日的家书中亦称:“沅、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秽气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在南京的清军军营中,疫病流行传播之广、病毙之速,令人闻之丧胆,如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
这次大疫灾,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丧失生命。关于苏、浙、皖三省当时在这次疫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一文中说:“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的占70%。”余新忠则依据官府档案及方志等各种资料,对苏、浙、皖三省死于这次疫灾的人口数作出了估算,谓这次瘟疫前后共波及苏、浙、皖三省32县次,其中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之府县,是这次瘟疫的重灾区,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8%~15%之间;而在极个别地区,比如嘉兴的濮院,疫死率则有可能达到四五成。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大约在4000万,若按8%~15%的疫死率计,疫死人口多达320万~600万。这场瘟疫仅在江南就夺走了数百万人口的生命,不能不说是一场极其可怕的人间惨剧。
同治元年(1862)疫灾的发生地尚不止苏、浙、皖三省,据清代官方正史记载,苏、浙、皖北方的山东、直隶,西部的湖北等省,在这年的四月至秋季均发生了大面积的疫灾。如《清史稿》载:“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海大疫。秋,清苑大疫;滦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莘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而据一些方志记载,河南、陕西、云南、贵州这年也都发生了疫灾。如河南正阳县,从农历三月到七月,“瘟疫大行,被传染者大半,死伤颇多”;陕西华州(今华县)“大疫”;云南永昌府“瘟疫大行,尸骸遍地”;贵州天柱县“发大瘟,十死八、九”等等。
由上可以看出,同治元年所发生的疫灾几乎覆盖了清代的半壁江山。各地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是否具有同源性,或者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个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里关注的是此次瘟疫大流行所发生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谢高潮和余新忠等人认为战争是导致这场特大瘟疫流行蔓延的重要原因。关于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谢高潮从三个方面予以了论述:(1)几十万军队在此地聚集,造成了这一地区粮食的紧张;(2)湘军军纪败坏,滋扰地方,鱼肉良民;(3)战争使本来很坏的灾区环境受到了人为的污染。余新忠进一步认为,由战争直接造成的后果与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密切相关:第一,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第二,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各地难民不断增加,同时,咸同之际,苏北及江北其他省份时有旱蝗等灾发生,大量饥民纷纷南下觅食,难民生活无着,路途奔波,本来体质就差,加之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瘟疫。第三,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直接导致了疫病的流传。第四,战争使国家和社会对付灾荒的能力严重下降。上述两位学者所论,各有独到之处,但都着重说明了战争是这场特大瘟疫流行蔓延的重要因素。
3.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疫病和其他灾害一样,既然形成了灾害,则必须有受害的承载体。自然灾害的主要承载体是居住地的人群和居住环境。居住环境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但包括民房、官舍、祠庙、宫观、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等各种建(构)筑物,而且也包括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生态资源,诸如山川、河流、自然景观等。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人群作为承载体,其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就是疫灾。疫灾除了造成人口的死亡和病痛(当然还包括牲畜),一般不会像洪涝、地震、风灾、雹灾等自然灾害那样,对居住环境造成直接的危害。因此,疫灾分布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在空间上的契合关系,比其他自然灾害更为明显。
从医学角度来讲,疫病的发生首先要有致病力较强的病原体的存在,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则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易感人群、有利的疫病传播途径作为基础。而易感人群和传播途径都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疫病的传染源有人传染、动物传染两种。研究证明,人类特有的人传染源疾病如麻疹、天花、霍乱、伤寒等,均必须在人群聚集增加、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动物疫源性疾病,则与人类聚居地与动物疫源的毗邻关系成正相关系。关于人口密度对疫病的爆发、流行所产生的影响,有学者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大多数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2)密集的人口为疫病的传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生活垃圾的增多,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4)人口对疫病的影响除了人口密度,还包括人口移动。
另有学者如龚胜生通过对中国历史(公元前770~1911)疫灾的研究分析,认为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关系密切,中国古代疫灾主要分布区域是:华北平原、山东半岛、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形区,其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疫灾尤多。因为这些地区开发程度大,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交通密度高,还有众多港口与国外进行贸易和交往,这一切都为瘟疫的蔓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笔者依据《清史稿》统计,清代疫灾发生频次排在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五省共计发生疫灾142次,占了清代总数的64%。这些省份无一例外地全部处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两个自然地带。这些地区不但在清代开发程度高、经济和文化发达,同时也是人口密度大或人口数量众多的地区。以嘉庆二十五年(1760)的人口统计数字为据,浙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山东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江苏的人口密度排在第二位,湖北的人口数位居第四、人口密度位于第六,河北在当时属于直隶,为京师所在地,是清代的政治活动中心,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人口流动频繁。当然,随着各地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在不同时期,人口密度是有一定变化的。下面再以道光三十年(1850)的人口统计数字为据,该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5.45人,人口密度比较大的5个省份(每平方公里超过148人)分别是江苏(408.84人/平方公里)、浙江(294.96人/平方公里)、安徽(268.84人/平方公里)、山东(215.86人/平方公里)、湖北(179.94人/平方公里),在这5个省份中,疫病发生频次排在前五位的就占了4个,而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安徽省在清代同样是疫病多发区,在各省市中居于第八位。由此可见,清代疫病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很高的相关度或者说契合性。
一些学者从地方史志资料着手,对区域性人口密度和疫病发生频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度非常高。如余新忠利用竺可桢所提供的民国初年(1920)的人口数字,对清代江、浙两省11县(溧水、昆新、南汇、锡金、溧阳、宝山、临安、桐乡、长兴、上虞、镇海)的瘟疫次数进行分析比照,考察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制作出“清代江南瘟疫与人口密度关系图示”。通过图示可以看出,“总体上,在灾荒或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当时决定某一地区是否发生瘟疫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由上可以看出,清代疫灾分布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在空间上具有很高的契合关系,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亦往往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也是疫病一旦流行,常常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的主要原因。
4.缺少防治疫病的医疗机构和手段
疫病的发生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有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疫病发生后是否成灾,或者构成多大程度(如受灾区、感染人群、死亡人数等)的灾害,是和当时的政府行为、医疗条件等具体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
清代是中国荒政最为发达的时代,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灾荒应对机制,其救灾制度的全面和细微超过了之前任何朝代。从历史上考察,清代是一个疫病多发期,但是对疫病的救治,不论是在政府卫生医疗机构的设置上,还是在疫病发生后政府力量的投入上,都没有超越前朝的丝毫优势。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时期,政府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宋代官方对医疗事业非常重视,沿袭唐代制度,建立了一套官方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机构。梁其姿通过对宋代政府医疗资源的研究,认为北宋时期设置地方医疗机构时,不但延及县府,而且已经开始以人口密度为规制标准,她还举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所载元丰年间的礼部奏议为证:“诸医生京府节镇十人,内小方脉三人。余州七人,小方脉二人。县每一万户一人至五人,止三人以上,小方脉一人。”梁其姿认为“这种以人口密度作为派遣医生的准则是非常理性、甚至可说很‘现代性’的”。除了官方机构外,梁其姿还重点对地方医疗资源问题进行了论述:“宋代除了中央有较为主动的政策来试图增加地方医疗人员外,一些热心的地方人员或地方官也自动自发地在地方建立医疗机构”,她列举了这种地方医疗组织的几种形式:病坊、将理院、安济坊、养济院等,然后指出,“这些例子主要显示了宋代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医疗方面所施展的力量,同时亦让我们看到正在发展茁壮的民间力量”。
但是,到了明朝,除地方州县基本上还设有惠民药局外,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进入清朝,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代最为重要的医疗机构是太医院,太医院不仅科目分类比较齐全,而且制订了一整套医官升迁制度和医学知识传习与考核办法。但太医院只是专门为皇室成员及王公大臣防病治病的宫廷医疗机构,根本不可能惠及人民群众。可以说,政府对太医院的过分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地方医疗机构的投入。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朝廷有时也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举措,比如,康熙十九年(1860)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康熙帝一边命五城粥厂向饥民施粥、加恩展赈三月,同时“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太医官能够走出宫禁诊治饥民疾疫,可谓皇恩浩荡,但如此举措只是在饥民拥挤京城、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朝廷所采取的非常之举。毫无疑问,京师的稳定是朝廷的第一考虑,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是顾及到饥民的疾苦,实在不敢估计过高。而且这种少之又少的情况亦仅限于京城而已。根据清官制规定,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主要是对地方“医学”的设置,如《清史稿·职官志三》:“医学: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流——原注),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劄。”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一个州县的医药和救疗起到切实的管理作用,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种设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另据《清史稿·职官志六》载:“卫生掌检医防疫,建置病院”;“军医掌防疫、治疗,兼司军医升迁教育”。从这两则史料看,清代实行新官制后,有了卫生防疫的专门机构和官员,但此时已经是光绪年间的事情。可以说,光绪以前,清代国家对疫病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
由于没有专门的医疗行政机构作依托,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体系迟迟不能建立起来,所以,一旦疫病发生和流行,政府所能做的充其量是对灾民施以赈济或蠲免,在疫病的控制和治疗上,则主要靠地方官府设立临时性的药局延医治疗,或者由民间医者自愿地施药救急,或者听任江湖游医肆行蒙骗,其救治效力当然不会太高。而即便是这些医疗资源,在一些地方也非常有限,当此之地的病人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便寄望于古老的“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或者干脆坐以待毙。清代,驱避疫鬼、防灾祛病的方法甚至为一些地方官所采用。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沴气旋消,吴民大悦”。这里且不说是否真的收到了“沴气旋消”的实效,地方官督民祈禳的行为,实际上说明了人们面对疫病流行已经是无计可施,哪怕地方官府还有一点点的医疗资源可以利用,也不至于通过这种祈禳之术为自己的无能进行遮掩,而所谓“沴气旋消,吴民大悦”,不过是地方官为自己粉饰而已。
可见,缺少防治疫病的相应机构和手段,也是清代疫病成灾、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一个因素。那么,在传统医疗事业普遍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宋代能够建立起比较系统的卫生医疗体制,而疫病频发的清代却在救疗态度上如此消极呢?余新忠认为清代于瘟疫救疗,政府作为不积极的缘由主要有三点: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第二,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及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第三,还应该考虑到,在技术上,瘟疫的救疗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首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一致,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和资源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其次,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复杂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统一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对于余新忠所分析的“三点缘由”,笔者表示赞同。但笔者同时认为,疫病成灾的更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封建统治腐败,即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藐视民瘼。虽然瘟疫的流行、蔓延,不计对象、不分尊卑,但深受其害的总是人民群众,于民生有碍但只要对王朝统治不会构成大的威胁,统治者绝对不可能为了民众利益而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他们宁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去建设太医院和充实御药房,也不肯在地方医疗机构的建置上花费一点精力。太医院是清代最出色医生的聚集之处,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医学专家,他们曾研究出大量卓有成效的医术和药方,但这些成果除了用于宫廷贵人和王公大臣身上,是不可能流入民间为大众服务的。至于余新忠分析的第三点,说是瘟疫的救疗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从而使得政府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则更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推脱责任、漠视民生的反动本质。
如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疫病频发以及大疫不断的基本原因。疫病灾害不同于其他自然灾害,由于疫病成因机制的复杂性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上述四个方面不可能把疫病发生的所有因素都涵盖于内。晚清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一些疫病从境外传入我国,虽然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却无疑增加了清代疫病灾害的发生频率。比如,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再如,宣统元年(1909),俄国发生疫病,“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蔓延奉、吉、黑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