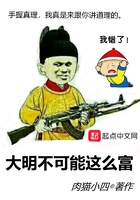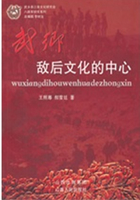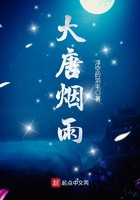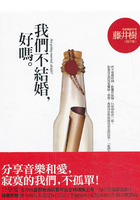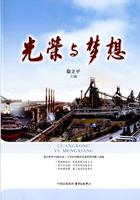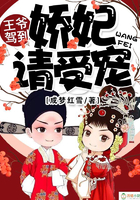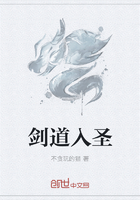经济现代灾害学认为,自然灾害的形成是“自然灾害系统”综合作用的产物,自然灾害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均是动态系统,其间又存在着复杂的互馈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灾害—社会经济动态体系。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直接的方面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水灾冲毁房屋,漂溺人畜;旱灾导致庄稼枯死,异常高温使人畜中暑而死亡;蝗灾导致庄稼减产或绝收,引发饥荒;地震因建筑物倒塌而引起人畜死伤等。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间接反映,是自然灾害链发展的最高层次。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直接反应的基础上,灾情进一步发展就会影响社会的经济和秩序,例如水旱灾害使农作物歉收或绝收,结果粮食短缺,物价上涨,严重时甚至出现大范围的饥荒;瘟疫流行使大量人口死亡,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等。
本节主要从灾害与清代小农经济、灾害与清代财政等方面,探讨自然灾害对清代经济的影响和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
一、灾害与清代小农经济
在传统中国,因受到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分散脆弱的小农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下才有可能顺利完成。封建王朝统治集团腐朽,封建剥削严重,是阻碍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小农经济分散单一,规模小,技术条件落后,也严重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另外,小农经济对外部条件如气候状况有很强的依赖性,风调雨顺是小农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的侵袭,就会因为沉重的打击而一蹶不振。甚至可以说,对农民而言,自然灾害的肆虐比地主阶级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候,重大水旱灾害对小农经济的影响甚至是致命的。
清代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关于自然灾害对清代小农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灾害对小农经济人力资源的戕害。关于自然灾害导致人口死亡之众,前文已经多次论及,对重大灾荒造成人口锐减的典型事例,也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提起,这里实无罗列的必要。另有学者对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基本参数作过研究统计,这里不妨就清代的情况作简要介绍,或可从一定程度上看出清代自然灾害对农业人力资源的戕害状况。如高建国曾以死亡千人以上的自然灾害为单位,对清代因灾死亡的人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有清一代在旱灾、涝灾、风雹、冻害、潮灾、地震六种灾害中,总死亡人数达5135万余,平均每年死亡19.16万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基本参数,清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死亡千人以下的灾害更不知凡几。况且死亡率很高的瘟疫亦未统计在内。如果把各种灾害的死亡人数累计计算,据有的学者统计,仅从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1888)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就高达6200余万之多。由于各人占有的史料不同,对灾害死亡人口的统计,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结果,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上述两项统计结果,足以说明清代灾害导致人口死亡之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必然造成劳动力资源锐减。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的多寡是经济起伏、国力盛衰的重要标尺。灾害对小农经济的影响,从小的方面比如个体家庭来说,主要劳动力的丧失,基本上宣告了个体家庭生产能力的崩溃,至少使家庭的再生产能力严重削弱,其连锁反应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减损,必然导致大片田土荒芜。耕地大量被抛荒,会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甚至可能导致局地小农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使得局地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并进一步影响到依靠小农经济支撑的国家财政,使小农经济和封建国家的互动援助能力减弱。
第二,自然灾害对小农经济畜力资源的摧残。这里的畜力资源包括生产和运输工具牛马以及农民所饲养的各种家畜。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清代依然如是。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多元化的格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以牛为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力和耕牛依然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即使在一些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耕牛不再作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并且有逐渐淡出耕作的趋势,但是,农民仍然会饲养牛、马和猪、羊等家畜,作为家中最主要的财产用来换取其他粮物而谋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大量的人口被无情地吞噬生命,牛、马和猪、羊等家畜同样不能幸免于难。这是自然灾害对小农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的又一表现。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洪涝、瘟疫、雨雹、地震、风灾、冻害、火灾等,是摧残牛马牲畜最为主要的灾害类型。下面就这6种灾害各举两个事例,以说明清代自然灾害对牲畜资源摧残之严重。
洪涝:顺治七年(1650)四月,“射洪大雨三昼夜,城内水深丈许,人畜淹没殆尽”。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山阳大雨倾盆,水高丈余,漂没人畜无算”。
瘟疫:据民国《和政县志》载,光绪十四年(1888),“秋冬,瘟疫流行,耕牛死者无数”。据光绪《平湖县志》载,光绪十九年(1893),“夏旱,牛疫而死者万计。死牛弃河,河为之塞,乡民乏牛耕田,田多荒芜,禾稻歉收”。
雨雹: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六日,“顺德雨雹,大如斗,击毙牛马”;五月,“汾西雨雹,大者如拳,小者如卵,牛畜皆伤,麦无遗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龙川雨雹,大如斗,坏民舍,牛马击毙无算”。
风灾:康熙三十五年(1696)七月,“二十三日,桐乡、石门、嘉兴、湖州飓风大作,民居倾覆,压伤人畜甚多”。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歙县大风,拔木覆屋,压毙人畜甚多”。
地震: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兴安、安康、白河、紫阳、洵阳、兰州、巩昌、庆阳等处地震,声如雷,坏民舍,压死人畜甚众”。光绪七年(1881)十月,“礼县地震,震毙四百八十人,倾倒民房四千有奇,牲畜无算”。
冻害:顺治十一年(1654)冬,“滦河大雪,冻死人畜无算”。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武强大雪,平地深尺许,人畜多冻死”。
火灾:康熙五年(1666)二月十三日,“钟祥火,毁数百家,延及府署,焚死人畜甚多”。据清代学者姚廷遴《历年记》续记卷四记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山西平阳府洪洞等三县于四月初六、七、八三日大雨,地震,房屋坍倒,压死多人。“既而地中出火,烧死人畜、树木、房屋、什物无算”。
第三,自然灾害对农作物和耕地的毁坏。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除了直接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大量丧失,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还表现在导致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水灾、旱灾、蝗虫、风灾、雨雹、霜冻等灾害,都会对农作物收成造成严重影响。水、旱、蝗一向被称为中国农业的三大灾害,对庄稼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比如,淫雨连绵会导致庄稼因长期浸泡而淹死;突发性洪水则使庄稼冲毁于瞬间。旱魃为虐对农作物的影响不亚于洪水,长期干旱会导致田土龟裂,庄稼萎蔫甚至枯死。蝗虫历来就是农作物的天敌,飞蝗成灾,往往使丰收在望的庄稼颗粒无收;旱蝗并发则为害更烈。风灾、雨雹、霜冻等灾害对农作物的破坏也非常严重。为了便于了解清代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损伤情况,下面就上述6种灾害各举两例进行说明。
水灾:顺治八年(1651)六月,“江阴霪雨六昼夜,禾苗烂死”。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宜城汉水溢,漂没人畜禾稼房舍甚多”。
旱灾: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昌乐、曲江、湖州、衢州、龙门、开化、江山大旱,禾尽枯”。乾隆三年(1738),“盐城自二月至六月不雨,大旱,赤地千里”。
蝗虫:顺治四年(1647)七月,“静乐飞蝗蔽天,食禾殆尽”;“长治飞蝗蔽天,集树折枝”;“灵石飞蝗蔽天,杀稼殆尽”。康熙八年(1669)八月,“海宁飞蝗蔽天而至,食稼殆尽”。
风灾: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苏州、昆山、武进大风伤禾”。嘉庆二十四年(1819),“七月初八日,平谷有怪风兼雨自南来,房舍皆摧折,禾尽偃,其平如扫”。
雨雹: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八日丁巳,滦州雨雹,大如卵,秋禾尽损”。同治四年(1865)五月,“房县大雨雹,数百里禾稼尽伤”。
霜冻:康熙三年(1664)四月,“二十三日,新城、邹平、阳信、长清、章丘、德平陨霜杀麦。二十四日,益都、博兴、高苑、宁津、东昌、庆云、鸡泽陨霜杀麦”。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武乡大雨雪,禾稼冻死;沙河大雪,平地深三尺,冻折树木无算”。
自然灾害除了对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另一严重后果是对耕地的毁坏。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洪涝、沙尘暴、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类型,对耕地的毁坏最为严重。自然灾害发生时,农田或被冲毁,或被淹没,或被沙压,既毁坏了耕地,也破坏了土质,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有的田地甚至长期不能耕种而变为荒地,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一道上谕曾说:“闻临清及陵县有经水沙压盐卤地一千余顷,屡年试种,不能垦复……”同时,自然灾害造成生态环境的改变,也会使土地资源利用受到影响,严重时,耕地受到污染,良田变为贫地。
在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对耕地的毁坏是非常严重的。如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2年,全国已耕种的耕地为12593万公顷,自然灾害毁坏耕地为5.64万公顷。另据2006年新疆《和田年鉴》载:2005年,新疆和田地区共发生了6次大的自然灾害(包括雪灾、雨灾、风雹灾、洪涝灾),共计受灾人口36.5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678.34公顷,绝收面积4538.4公顷,毁坏耕地面积155.93公顷。关于历史自然灾害的后果,学者们多着眼于人口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由灾害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则着重于探讨劳动力资源的损失、粮食作物的歉收以及正常生产秩序的恢复等问题。很少有人从耕地被破坏这个角度去论述灾害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
当然,也并非无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姚兆余对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799~1847)近50年间,青海河湟地区因灾害而受破坏的耕地面积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其间因水冲沙压而荒废的耕地,总面积达50539亩,平均每年荒废耕地1053亩。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荒废的“番地”。再如,闵宗殿曾根据《清实录》资料,对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光绪八年(1882)中,自然灾害对耕地毁坏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这107年间,因冲塌、水淹、沙压而被破坏的耕地达4万多顷。
耕地毁坏类别冲塌水淹沙压合计耕地毁坏数量(单位:顷)16511130341147341018(本表采自闵宗殿:《关于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一些统计——以〈清实录〉记载为根据》,《古今农业》,2001年第1期。)
闵宗殿之所以只统计1776年到1882年这107年间自然灾害对耕地的毁坏情况,主要是因为此前和之后《清实录》对耕地的破坏记载极少。笔者依据《清史稿》资料进行统计时,结果发现,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的100多年里,有确切数字记载的耕地被毁坏史料倒是有一部分,而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则几至阙如。现将《清史稿》所记载的这部分史料摘录如下。
顺治十年(1653)六月,“文登大雨三日,海啸,河水逆行,漂没庐舍,冲压田地二百五十余顷”。康熙十九年(1680),直隶巡抚于成龙因“宣化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疏请免除当地田赋。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岁大雨,中河决,淹清河民田数千顷”。康熙三十年(1691),“永宁河决,淹没田二百余顷”。康熙三十八年(1699),“鄞县沿海田,被水冲决一千七十余亩,(郭世隆)请永免额赋”。雍正二年(1724)七月,“泰州海水泛溢,漂没官民田八百余顷”。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常熟、昭文大水,淹没田禾四千四百八十余顷”。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介休霪雨,淹田禾六十余顷”。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介休霪雨,淹田禾八十余顷”。除了这些有确切数字记载的史料,《清史稿》中有关农田受灾害毁坏的史料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其记录多为“坏民田”、“田畴尽没”、“浮没民田”、“田庐俱损”、“坏田庐无数”、“雨土二寸许”、“坏民田庐殆尽”、“庐舍田地冲没殆尽”、“平地积沙二寸许”等。从这些历史资料所提供的信息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清代耕地因灾害而受毁坏的情况是多么严重。
根据清制,地方受灾后,朝廷对被灾地方的蠲免等救济方案,是依据地方官的审查造册(被灾田亩、被灾人口、被灾分数等)而制定。所以,地方官的奏折中一般都会提供具体的受灾田亩数以及耕地受毁坏的状况。以下再略举几例。比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福州发生水灾,十月二十九日(12月8日),刘韵珂、刘鸿翱奏报勘查结果:仅闽县一地就“被淹田园四万四千四百三十余亩……其中有被沙压泥淤者三百五十余亩……又据侯官县会同委员勘报,该县被淹田约四万九千余亩”。同年四、五月间,广东西江、北江水涨,浸淹十七州县部分田宅,其中南海、三水、高要三县灾情较重。据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程僪采在十一月的奏折中称:“南海县冲决桑园等二十四围,三水县冲决榕塞十六围,高要县冲决陈塘等十九围,高明县冲决俊洲等六围,四会县冲决白鹤等七围。各围决口自数丈至七八十丈不等……其各围淹压田亩自数顷至二三十顷不等……”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吉林珲春因河水涨溢,经额布、盛桂在九月初九日(10月28日)的奏折中称:该县八千余垧田地中,“水冲无收者六千余垧”。就是说,80%的田地被水冲毁,毫无收成。奏折中诸如此类的描述,不一而足。
清代因灾害而遭受破坏的耕地面积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作出确切的统计。但是,根据上面所列举的部分统计资料和历史信息,完全可以说明,自然灾害对清代耕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自然灾害对清代小农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表现。
二、自然灾害与清代财政
如前所述,清代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小农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特大而持久的自然灾害还会使小农经济的发展陷于停滞。另外,自然灾害对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自然灾害和国家财力,两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自然灾害发生后,国家要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粮米用于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直接导致国家财政资源的损耗;同时,自然灾害发生后,对灾区的蠲免、赈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粮食贮备在短期内呈现出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国家经济实力的削弱,一旦新的灾害发生,势必影响国家的救济能力和荒政效力的发挥,进而导致灾害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增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救灾措施,均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换而言之,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荒政能否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下面主要以“灾蠲”和“赈济”两方面的内容为切入点,探讨清代自然灾害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一)灾蠲和清代财政收入
灾蠲是指灾害发生后政府对灾民应纳赋税进行部分或全部免除。清代早在顺治二年(1645)就已经行使灾蠲,免当年直隶霸州等八县水灾额赋。但是,灾蠲定制的形成是在雍正朝,雍正六年(1728),根据顺治朝制定的被灾分数,仍将全部额赋分为十分,按田亩受灾分数进行蠲免,规定被灾“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灾情重者,率全行蠲免”。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下谕,以后被灾五分之数亦准报灾,蠲免钱粮十分之一,其他一如雍正朝旧规。以后都基本按此标准实行。灾蠲有免当年应征钱粮,又有免历年灾欠钱粮。由于清代自然灾害频仍,所以灾蠲次数非常频繁,累计灾蠲银两数目也就很高,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清代蠲免的内容主要是地丁、田粮,另有芦课、盐课等杂税。康熙三年(1664),户部上奏,凡遇灾之地,先将额赋停征十分之三,以待题免。康熙四年,“御史郝维讷请凡灾地田赋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后丁随地起,凡有灾荒,皆丁地并蠲”。康熙、乾隆两朝,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嘉庆年间,虽无普免但多灾蠲,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咸丰以后,国用浩繁,财政入不敷出,但是,凡遇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予蠲免,“若灾出非常,或连年饥馑,辄蠲赈兼施”。由于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所以清代对水旱灾害的灾蠲最多。有学者根据《清实录》中有关数据,对顺治至道光朝水旱灾害蠲、赈的州县数进行详细的统计,结果如下。
顺治朝:灾蠲1141州县,年均63州县;灾赈91州县,年均5州县。康熙朝:灾蠲4735州县,年均77州县;灾赈1298州县,年均21州县。雍正朝:灾蠲845州县,年均65州县;灾赈721州县,年均55州县。乾隆朝:灾蠲6092州县,年均101州县;灾赈6732州县,年均112州县。嘉庆朝:灾蠲1096州县,年均44州县;灾赈1433州县,年均57州县。道光朝:灾蠲1801州县,年均95州县;灾赈1039州县,年均54州县。
关于蠲免地丁的银两数目,李向军在《清代荒政研究》一书中,对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共计196年的情况做过估计。作者首先统计出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东北等19省(区)的州县数共计1522个,经过对233个有具体灾蠲州县数和钱粮数的资料的计算,其平均值为8107两,年平均免649925两,依此推测估算,“灾蠲一州县,约免银八千两,年平均灾免银约六十余万两,196年总计约一亿二千余万两”。这个数据尚不包括“蠲免积欠”。各省积欠的银两,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灾欠,即政府灾蠲之外应完纳而未缴纳、长期拖欠下来的银两,由于越积越多以致最后无力完纳,政府对这部分积欠也不得不行蠲免。如果加上蠲免灾欠的银两,清代前196年灾蠲总数大概在“1.5亿两至2亿两之间”。如果这个估测可信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196年间清代蠲免银两的年平均数:取1.5亿和2亿之间的中间值为1.75,则清代前196年的年均蠲免银两数为892557两。也就是说,期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平均要减少892557两白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一直保持着缓慢扩大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都会有所盈余,892557两白银在国家银库中也许不是大数,但如果和当时一些常例支出项目作一下比较,这部分银两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相当大的。如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公百官的薪俸为“九十余万两”,则每年蠲免的银两数几乎相当于王公百官一年的薪水,应该说这个蠲免数不是小数目。另外,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地丁银两之外,还有一大块属于实物田赋即粮米(米、麦、豆、草等)。清代前期的实物田赋数额是比较大的,如果折算成银两(按时价平均每石、束折银1两),康熙朝的实物田赋约合900万两左右,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一半强。灾蠲除了免除地丁银外,更多是蠲免粮米,蠲免粮数因受灾程度的轻重,从几万石到几十万石乃至上百万石不等。比如,康熙九年(1670),因高邮、宿迁、桃源、盐城、赣榆频岁被灾,“民重困,下部再议,免旧逋漕米三万一千石有奇”。康熙六十年(1721),“普免各省积欠,及因灾缓带银千五百五十余万两、粮三百八十余万石”。咸丰以前,政府财政基本上能够维持收入大于支出,这为因灾蠲免银粮能够切实可行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咸丰以后,战争频仍,军费开支急剧上升,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偏偏又是连岁灾荒,深受天灾人祸之害的农民根本无力完纳正赋,故出现凡“遇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予蠲免”的不得已之举。此时,灾蠲和国家财政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不断的灾蠲加上赈济,使政府财力逐渐减弱,政府财力减弱导致救灾能力下降,救灾能力下降必然加重灾荒为害的程度,而面对新的灾害又不得不行蠲免和赈济,灾蠲与赈济和国家财政之间形成一种恶性的互动影响。灾蠲、赈济本来是清代荒政中最积极、有效的举措,但在晚清时期,却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一起成为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
(二)赈济和清代财政支出
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对灾民予以赈济,赈济和蠲免是清代救灾措施中最主要的两项内容。赈济包括赈银和赈粮,在灾害频仍的情况下,赈济用银是清代财政非正常支出中最大的款项。尤其是一些大的灾害,赈银往往多达数百万两。如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七年(1742),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合在一起,江苏赈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乾隆十八年(1753),高邮运河决口,江苏受灾严重,朝廷拨银四百万两予以赈济。嘉庆初年,“山东曹、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嘉庆六年(1801),直隶发生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嘉庆十九年(1814),“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1831),拨江苏赈需银一百余万两。而在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847~1849)连续三年的时间里,先后赈河南灾银一百余万两,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尚不包括截留办赈和官绅商民捐输之银在内。光绪初,“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余万两”。直隶自光绪十六年(1890)大水至二十一年(1895)海啸之灾,“用银七百余万两”。山东自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85~1899)频年河溢,“用银七百余万两”。江苏自光绪十五年(1889)之水至二十四年(1898)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余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秦、晋之灾,政府赈济加以官捐,“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这些例证只是针对大灾的大额赈济,实际上,但凡有自然灾害发生,只要被灾在五分以上,清政府照例都要予以蠲免和赈济。由此可以推知,清代赈济用银在财政支出中,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赈济用银,李向军也作了推测,他通过对“有具体州县数和赈银数的102个数据的计算”,估计平均每次“每州县的赈济用银约近四万两,年平均支出二百二三十万两……清代196年救荒用银约为4.5亿两左右”。如果这个推测可信的话,那么,这4.5亿两白银在清代财政支出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时的财政收支状况。
根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削平“三藩”之后,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将近四千万两白银,“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岁入四千数百余万之大数”,乾隆五十六年(1791),“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嘉庆、道光时期,“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由上面几个具体数据和信息资料可以推断出,从康熙朝中期一直到道光朝的150多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年平均数应不低于四千万两白银。如果按每年四千万两计算,4.5亿两赈银则相当于清政府11年的财政收入总额,这150年间,平均每年用于赈济的银两为300万,赈银数目不可谓不大。清代财政支出岁有定例,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前期较为固定的财政支出共有12款,即祭祀之款、仪宪之款、俸食之款、科场之款、饷乾之款、驿站之款、廪膳之款、赏恤之款、修缮之款、采办之款、织造之款、公廉之款。上述“赏恤之款”中的“恤款”应该是常年对孤贫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抚恤费用,和灾荒救济款是两回事。自然灾害属于意外的“天灾”,赈银属于非正常的支出,并不在12款常例之列。如果以乾隆五十六年的财政固定支出情况来看,当年财政收入为“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支出为“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根据此前惯例(乾隆三十一年),其中大的支出项目,比如满、汉兵饷为一千七百余万两,东河、南河岁修银为三百八十余万两,文职官员的养廉银为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漕船岁用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王公百官薪俸约为九十余万两等。可以看出,年均300万的赈银竟然达到了每年兵饷的17.6%,高出王公百官薪俸3倍还要多。由此可以说明,清代赈济用银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可以说,灾荒赈济一直对清代财政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只不过是在收支相抵而有所盈余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不易凸显出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清史稿》等书中所载“岁出”,并非指国家一年所有的支出数目,而仅是能够奏销的经常性支出。如前面所举乾隆五十六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收支相抵,该年竟然余存一千一百八十二万银两。若照此计算,三、四年之后,仅库存的银两加起来,也达到了期间的年平均岁入银数四千万两。这当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未入奏销的蠲赈钱粮、河工另案等非常支出的数额也很大,而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支出并未列入“岁出”预算与统计之内,故实际支出规模应当比官方或私家文献记载的数字为大。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史书所记载的“岁入、岁出数是‘各省’或‘各直省’之额,并不包括京城的支款与户部另外的入款”,其中支出最大的款项,即一千七百余万两的满、汉兵饷,仅是各省的支出,不包括东北地区,更不包括京城。根据一些资料综合估算,单是“京城支款每年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在清代经济实力最强的康熙、乾隆两朝,财政状况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宽裕,康熙年间“每年的结余额大致在200万两左右”,“乾隆中期年节余银在400两左右,最多不会超过600万两,而不太可能像有些学者统计的那样达到一千数百万两或两千数百万两”。如前所述,清代“岁出”银并不包括用于灾荒赈济的银两,而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平均每年用于赈济的银两多达300万,如果将这部分银两算在财政开支当中,可以推断出,在一些灾荒尤其是大灾发生的年份,完全有可能出现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因为300万赈银只是150年的平均数值,而灾害的发生是不可能平均分布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家财政状况良好的清代前期,数目庞大的灾荒赈银也对清代财政收支状况产生着很大影响。清代对一些大灾的赈济,往往多至数百万银两,这必然会影响当年的财政支出和来年的财政预算。比如,乾隆七年(1742)江苏、安徽大水,各项赈济加在一起,赈银高达738万两。除了这笔大额的赈银,因为该年和上年全国各地多处遭灾,用于其他地方的灾蠲和赈济项目也很多。比如,该年四月“免河南永城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除河南洧川等十一县水冲地赋”;七月“赈湖北汉川、襄阳等州县卫水雹灾,并停征额赋”;八月“赈江西兴国水灾”;九月“赈湖北潜江等十州县水灾”,“赈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免广东崖州等二州县风灾额赋”;十月“免山东历城等十九州县旱灾额赋”;十一月“赈湖北汉川等十二州县水灾饥”,“赈浙江瑞安等县厅场、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赈山东胶州十州县卫水灾”,“赈甘肃狄道等州县水雹灾”;十二月“免直隶蓟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免山东胶州等十州县卫水灾额赋”,“拨运吉林乌拉仓粮接济齐齐哈尔等处旱灾”。该年还免除“甘肃地震处之课”。以上这些灾蠲和赈济,史料中未载具体银两数目,但可以统计出大致的州县数。除去灾蠲,单就赈济来说,赈济的州县至少有55个。如仍按照前面的计算标准,以每州县每次平均赈银四万两统计,则55个州县赈银为220万两,再加上江苏、安徽两省赈银738万两,则该年用于灾荒赈济的银两至少应有958万两。在岁入银为4000多万两的情况下,灾荒赈银就占去了24%,显而易见,一定会对当年的财政支出产生很大影响,并促使政府对来年的财政预算做出调整。
从整个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来看,总的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的层面看,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时期,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近代民族工商业经济的兴起,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急剧膨胀。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但是,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灾害频仍,战争连绵,饥荒不断,非常项支出激增,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巨”,使政府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开支,度支窘迫、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日益严重,财政收入规模相对显绌。晚清时期,除了和防灾救荒有密切关系的河工用费,单就灾荒赈济来说,其数目之大,并不亚于清代前期的赈银数。如前引《清史稿·食货志》所载,从光绪初至光绪二十七年,郑州河决、直隶大水和海啸、山东黄河决溢、江苏大水、陕西山西大旱灾,这27年间仅有数可稽的大灾赈银,就达到了2910万两。其他因各种灾害而用于赈济的银两更不知有多少。可见,晚清时期,大量的赈济和灾蠲,对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必然产生一定的冲击,这也应该是晚清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一个因素。过去一些学者在考察晚清财政的支出结构和财政吃紧的原因时,多着眼于军费开支、外债支出、战争赔款等社会方面的因素,这虽然没什么不对,但忽视自然因素比如灾荒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其考察视角毕竟不够全面。
晚清时期,是清代第二个各种自然灾害群发的时期即“清末宇宙期”,自然因素和各种社会因素的互馈影响,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变局也必然会产生影响。这里从灾荒救济的角度,探讨灾蠲、赈济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互动影响作用,但愿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审视晚清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的变迁,能够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