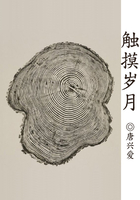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流泪,无论受了什么苦,她都独自承受。我所知道的只有两次,一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正起新房子,母亲喂养的几头年猪都无缘无故地死了,后来父亲将外祖父送的一头百来斤的壮猪背回来,又没喂多少天。那些日,母亲整天望着空空的猪槽发呆。才过了一个月,一场大风吹到了母亲那年最后的希望。狂风伴着骤雨淹没了夜晚,母亲心怀恐惧睁着眼睛望到天明。次日我们跑到地里,只见几亩正抽穗打花的苞谷大多匍匐在地,母亲站在路上失声痛哭。见我们走来,母亲马上止住了哭声,连声说,你们快回去,只倒了,扶起来就行了。说完,将断了的苞谷杆一根接一根的往上扶。可是扶了又倒下了,扶了又倒下了。“妈妈,别哭,我们回去吧!”母亲愣了一下,抱着我和哥哥,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二是大二暑假我在恩施晚报社做实习记者,由于未与家里联系上,同学们又都回去了,日子过得极其艰苦。当日在烈日下锄草的母亲听叔叔说我一个月只用了四十几块钱,天天流鼻血,晒得又黑又瘦却才写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后,她呆住了,无力的双手托着锄把立在田中,任泪水和汗水无声地低落。母亲极其难过,他责怪父亲没能及时与我联系上,又责怪自己无能,责怪那一学期都不能想出办法为我寄钱,责怪没能让我早些回来。
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只到县城去过一次。
那是去年冬天,收到哥哥的信,母亲乐坏了。哥哥在信上说,嫂子生了个女儿。当天晚上,从不愿出门的母亲收拾了半夜。她准备到县城看孙女去。天未大亮母亲就提着大袋小袋出发了。里面装的是鸡蛋、腊蹄、红枣、还有几斤白糖。父亲说有些东西不必带,在城里买更便宜。母亲执意不肯。要送她,她也不肯,孩子似的辩解道:“我好歹也认识几个字,我又不是不会问。”后来据哥哥讲,母亲进城后累得不行了,四十多里的山路走完,再在轮船上折腾四五个小时。母亲从未坐过船,甚至没有见过波涛汹涌的大江。一路晕着吐着,又累又饿,却舍不得买口水喝。
进城第二天,吃过午饭,母亲提出要给我打电话。母亲颤抖着手捧起话筒,又是紧张又是激动,好不容易拨通了,接电话的是位“嗓子脆的很”的女孩。她听了半天,弄不懂母亲的意思,急了,说,“您说普通话吧!”母亲小心翼翼地答说不会。“那么,英语呢?”这回母亲不懂了,只好挂了。
母亲在城里呆了一个星期,只在街上“玩”过一次。那天哥哥给母亲五十块钱,说您到街上散散心,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由八岁的表妹陪着,母亲上街看世界去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回来了,见哥哥问,母亲笑着说钱用完了。“用完了?”看着母亲空空如也的双手,哥哥很奇怪。还是表妹嘴快,“姑妈把钱都给别人了。”原来,母亲在街上见着有要饭的,就请一位摊主帮忙欢乐零钱,遇见一个就给一些,母亲说,他们怪可怜的。
从城里回来那天正在下雪,母亲坚决要走。她说担心楼上的谷子还有父亲的病。乡亲们问起城里,她只说城里热闹着呢,只是有些方面太浪费了,比如馒头扔得到处都是,卫生间竟嵌着瓷砖。
母亲不但是远近闻名的厨师,经常有过事的人家不愿数十里来请她主厨,而且精于女工。母亲做鞋快,做出来的鞋也是最耐看。小时候穿着母亲就着油灯做的布鞋到别人家去串门,主人家见我穿的鞋子好,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答了,他们就啧啧称赞:“怪不得,你妈大能人呐!”母亲除了给家里人做,还给娘家老人做,热天里做宽口浅底布鞋,冷天则做高帮厚底布鞋,每人一年几双。为此,母亲睡眠很少,独自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纳着鞋底,常常熬到深夜。
我读初三那年,父亲由于劳累过度,一场大病夺去了他大半劳动能力。母亲打柴、挑水、种地,用单薄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母亲头上的银丝更多了,她更憔悴了。母亲再也很少给我们做鞋,有时候,好不容易纳个鞋底又爱不释手地搁下。
考上大学后,一大早母亲将我和父亲送出门,走了几步,又像是忘了什么贵重物品似的跑进屋,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放在我手里,叫着我的小名说:“红儿,到大学了要争口气,带上这双布鞋,休息的时候穿着爽脚,听话啊!”我拿着这双做工精细,平整秀丽的黑色布鞋,想着母亲的好,眼睛随母亲身影的后移渐渐湿润了。
母亲给我做的布鞋我只穿过一次,我把它珍藏在箱子里,这表面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鞋不正像母亲呢那颗质朴的心吗?母亲用结满厚茧的双手把满腔的思念与祝福牢牢缝进游子心里,布鞋他内在蕴藏着巨大的韧性:不怕人生道路的崎岖和坎坷,经得起打磨。
我要好好保存这双鞋。上次父亲在信中说,母亲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一根细细的线已穿不到针孔里去了。
乡亲
八根大爷
八根大爷是九一年冬天去世的,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因自幼在湖南读书,我没有见过八根大爷。关于他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至今,人们在茶余饭后仍然谈得津津有味。
八根大爷的真名就叫八根。八根娘总共生了八个子女,天花病夺去了四个,闹饥荒死了两个,还有一个才生几天就被闯进村的土匪一刺刀挑走了。最后剩下八根。
八根爷命苦,妻子只跟他半年多就早逝了,他便未再娶。早年媒婆们自告奋勇地找上门,表示愿撮合好事,并且表示不收面条和鸡蛋,八根爷却性子倔,一口咬定“要为妻阿兰守节”、“阴阳相伴”,开始大家笑,后来没人笑了,也不再管他,八根爷的婚事就搁了下来,直到他八十高龄寿终正寝。他年年不忘的是“好伴儿”阿兰,各种感情从当年大胆昵称可以看出。
八根大爷读过几年书,《论语》《春秋》背过不少,当过教师。他一生中最高官职是最高指示学习小组第二副组长。文革前一天,上级传达精神:打倒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当然,揪斗任务也有八根大爷一份。他不知道当权派究竟何所指,上面派来的领导也说“目标尚不明确”。不清楚不等于不工作。最后,在工作组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当权派”就是乡党委乡政府各机关干部。
八根爷身为基层领导,为充分体现自己对毛主席的指示活学活用,从“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上展开联想。于是,花了一幅“雄鸡鸣晨图”,贴在堂屋里,每日三观而后言行,自我感觉很忠诚,很革命。然而,“当权派”的帽子很快就戴到了八根爷头上。罪因即那幅画。得到报告,揪斗组立马兴奋起来,一根绳子将他请到工作总部。八根爷一个劲地叫冤,但是领导说,你的阴谋由来已久,你想当雄鸡,领导天下反动派闹革命。批斗整整维持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七点,八根爷被押到特设的高台上站着,问一阵、吼一阵,然后下班。八根爷的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革命”、“坏分子”够不上,只好当成“右派”。定罪那晚,八根爷大骂起来,话刚出口就有几位“战士”冲上来一用劲。八根爷瘫了,倒在地上还哭着骂。
有种呢,乡亲们暗地里说。
八根爷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不过在七十八岁那年又做过一件正义的事情:教训村里的恶棍疤子。疤子卷起袖子指着老娘的鼻子痛骂,正巧被八根大爷看见,丢下拐棍,跳上去就是几个猛巴掌,揍得疤子咬牙切齿,却始终未敢还手。
祖父说,八根大爷百年那天精神特别好,坐在床上不停地念叨:“我没有背叛毛主席,我没有……”后来,就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八根大爷的丧失特别隆重。
微笑“的哥”
陪朋友辉满街寻“的哥”,辉使用的是基本方法:看见有齐兴出租车驶来,他就拦。停了不打的,却只奔车头。
“不是,对不起!”
有时候拦停了,不见“的哥”,却是“的姐”。有一位大胡子的“的哥”被戏弄了三回,终于怒不可遏,“你到底是要搞么子?再烦,烦,烦……”还是离去了。
不知拦过多少辆出租车,不知被骂过多少回“神经病”。回有些气馁了,他说只知道的哥开的车是齐兴出租车公司的,还有“的哥”剪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的笑。
事情,还得从上周六说起。这天,辉借来一辆自行车学骑,学了约两个小时,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并不太差,便大胆上街。然而,对于刚学会上路的辉来说,在土桥坝骑车无疑是伟大的创举,行进途中充满惊险,远没有院子里独来独往镇定自若。果然,只几分钟,辉的自行车就鬼使神差地扑上一辆的士的车头。辉被弹下来,额头上开了一条口子,手、腿等多处擦伤。他却顾不了痛,他最担心的是司机凶神恶煞地下车,理直气壮地抓住他威胁说:“不给钱别想给老子走路。”
只听门“砰”地一声开了,跳下一位身材魁梧的“的哥”。
“宰就宰,老子认命了!”辉准备着,只是心存侥幸:可别漫天要价,五百、八百的。
但是,“的哥”只嚷了一句:“怎么搞的?”就拉辉上了车,再后来就去了医院。
辉很清楚地听的哥说了一声:“医生帮忙看一下,他摔伤了。”然后问辉有没有钱,辉连说:“有,有。”
待辉回过神来,才发现的哥早走了。辉说:“我太蠢,满脑子充满恐怖的’宰’,竟忘了问人家的姓名。”不过,他永远记得:他留着板寸头,总是一脸温和地笑。
“的哥”袁也
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时,一些宾馆、舞厅或学校门前,各色各类的出租车就纷沓而来。“的哥”“的姐”们都自觉将车停在台阶下,依次排开。也许,你会偶尔发现,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总是不愿呆久,猫一般溜来溜去。没错,开车的准是袁也,他讲过,他总是有股跑的冲动。
袁也不姓袁本姓张,只是因为魁梧的身体上面生了一个圆大脑袋,更主要的是他专科毕业又到湖南锑都武术院修炼了两年,回来后却与比他大八岁的笔友小燕结了婚,大家都替他惋惜。有好友曾叹曰“冤也”,其后日渐演变,逐成袁也。袁也先是在家乡宜昌跑出租,干了七八年,前些年恩施兴起出租车,袁也立马携妻回娘家,成为一位地道的山城的哥。
老袁活了四十几岁,拥有一绝:跑车。老袁勤勤恳恳地挣,妻子也就小心谨慎地花,辛苦经营十几年,去年在土桥坝买下一栋小楼房,购置了“现代化”。老袁让妻子在家享福,自己仍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啪嗒响的破皮鞋。
两口子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就有人在背后嘀咕推论,说他在宜昌肯定有“前科”,而且昧了不少黑心钱,现在才这么谦虚。老袁听了就发急,求求你了好兄弟,别开这种国际玩笑,咱姓张的可是世代良民呀,干不好那事的。
见老袁面相宽厚,年纪又大了点,有些人就打起了坏主意。某日夜里,老袁载三个年轻人到后山湾,三青年下了车不给车钱,反要“烟钱”。老袁不给,他们就动起手来。习武出身的老袁哪肯吃素,三拳两脚,歹徒们就趴在地上喘着粗气讨饶叫大哥。
老远从不玩手脚敲诈客人,当交的费用也是老老实实地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开车”。
袁也跑出租,一路泥泞一路歌。
王老汉“打的”
王老汉是宜恩县会口乡苦草坪村人,五十多岁了,为人“古怪”。
据王老汉自己说,他还是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恩施那年到过州城,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读过几年书的王老汉是知道妇女节的,3月7日那天,王老汉浪漫地算计开了:妇女节进城给老伴买牦牛壮骨粉去。王老汉想,老伴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现在落了个腰酸背痛的病,听电视上讲得玄乎,咱也给老婆子买几盒试试。
因为有个侄子在恩施市三孔桥做生意,王老汉计划先去那里看看,就用袋子装了一块腊肉,还揣上女儿从北京带回来的两包“红塔山”香烟。
走了近三十里山路,转了两道车,约五个小时后,王老汉在舞阳坝车站下了车。然而,面对车来车往的崭新世界,王老汉不知所措了。他没问过侄子的电话号码,不能让他来接,无奈,他就问旁边的人:“到三孔桥前两百米怎么走?”一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笑着说:“您可以打的呀。”
于是王老汉就喊:“打的!”惹了一阵笑,但是马上就有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到他的面前。“您去哪里?”“到三孔桥前两百米。”王老汉笑答。开车的小伙子一笑,启动车子。
王老汉上车心里就忐忑起来,他问这位自称“小杨”的伙子:“要好多钱吧?”小杨说不贵,就收三元。“啊?这么贵!”王老汉吵着要下车,说什么也不坐了。他说他早就清楚城里人,他宁愿走到三孔桥去。小杨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说:“算了算了,不收您的钱。”到了三孔桥,王老汉下车了却磨磨蹭蹭不肯走。终于掏出了那两包烟,塞在小杨手里说:“你这娃心好,抽抽这个吧。”小杨急了,说:“您给侄子拿去拿去。”
王老汉却转身不见了,从巷子里传出一句话:“我还有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