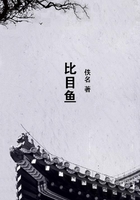K想找些理由,却被他一下子噎了回去。他接着说:“此外,你说得很对,法院对我很信赖。”他停顿了片刻,似乎想给K一点时间,用来回味他说的这番话。眼下门外又传来女孩们发出的声音了。她们似乎正聚集在钥匙孔附近,或许她们可以透过门缝看清房间内发生的事。K抛弃了一切为自己辩解的念头,因为他不想让谈话离题,也不想使画家自以为是,以至使人难以接近。因而他问:“你的职务是正式任命的吗?”
“不是。”画家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打断了他的思路。K急于让他说下去,便说:“哦,这种不被人承认的职务往往比正式职务更有影响力。”
“我的情况就是如此,”画家皱起眉峰,点点头说,“厂主昨天跟我谈起了你的案子,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助你绵薄之力,我对他说:‘让那人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一趟。’我很高兴见到你这么快便来了。看来你还是非常关心此案,这自然一点也不奇怪。你想把大衣脱掉吗?”
虽然K不想在这儿久留,但这个建议一样受到了他的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感到房间里闷热的空气了;他有几次惊奇地看见,角落里有一个小铁炉,虽然没有点火,房间里却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脱掉大衣,解开上衣扣子。画家抱歉地说:“我需要暖和点。这儿顶暖和,对不对?我在这里感到很舒服。”
K听了这话,一语未发;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热,而是那种沉默壅闭、令人窒息的气氛;房间里肯定很久没有流通新鲜空气了。当他被画家请坐到床上去的时候,他感到更不好受了;画家坐在画架边的一把椅子上,房间里只有这么一把椅子。迪托蕾里看来也不理解K为什么仅仅是坐在床沿上,他请K坐得舒服点,并把满心不情愿的K推到毯子、床单和枕头中间。然后他重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向K提出第一个严肃的问题,使K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
“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
“是的。”K说。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因为他只和画家一个人在谈话,没必要顾忌后果。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坦率地问过他。为了使自己更加愉快,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完全无辜冤枉的。”
“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着头,好像在思索。突然,他扬起头说:“倘若你清白无辜,那事情就很简单。”K的眼睛暗淡了:这个自称受到法院信任的人讲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
“我清白无辜,并不能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摇着头,说:“法院里有数不清的阴谋诡计,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他们到后来会无中生有,给你编造出一大堆罪状来。”
“对,对,自然,”画家说,好像K根本没有必要打断他的思路,“不过,你反正是清白无辜的,是不是?”
“自然,这用不着问。”K说。
“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
他没有被K所说服,虽然他讲得斩钉截铁,但K仍然不明白,他说这话到底是出于真的相信还是权作敷衍。K为了弄清这一点,于是便说道:“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这是肯定的;我仅仅是从三教九流那儿听说一点关于法院的情况,别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他们倒是一致认为,起诉不是轻率作出的,法院一旦对某人起诉,就认定被告有罪,要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简直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画家说,他的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法院永远不会改变这种信念。倘若我把所有法官都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张画布前就本案进行申诉,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一些。”
“我知道。”K喃喃自语,他忘了他仅仅是想让画家吐露一些情况。
一个女孩的声音从门口又传来:“迪托蕾里,他一会儿就走吗?”
“别闹,乖点!”画家转过头来叫,“你们不知道我正跟这位先生说话吗?”但是女孩并不罢休,又问:“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回答。她接着说:“请你别给他画像,他太难看了。”其他女孩叽叽咕咕一阵,表示认同。画家一步串到门口,开了一条缝——K看见了女孩们伸出的一双双交叉紧握着的、苦苦哀求的手——,对他们说:“你们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们全推到楼下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安静点。”她们看来没有马上服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静谧。
“请谅解。”画家再次回到K的身边,对K说。
K没有心情向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向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轻声说话,即便在这时,K也几乎纹丝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女孩子们就听不到了:“这些女孩们也是属于法院的。”
“什么?”K叫着,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
可是迪托蕾里又坐到椅子上,半戏谑半解释地说:“你要明白,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
“我此前不清楚这些。”K简捷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综括声明使刚才说的“女孩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K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循规蹈矩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女孩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缓缓地上下移动。
“对于法院的整体情况,看来你还不了解。”画家说。他向前叉开两条腿,用脚跟击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大可不必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
“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K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
“法院仅仅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K竟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惊奇。“但倘若在幕后活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抑或,举个具体例子吧,就在这间画室里。”
K彻底相信了画家现在说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的确是有希望的。倘若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轻易地会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低估。K已在自己周围找到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K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目前,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迪托蕾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K身上有怎样的效果,之后稍有不安地说:“你或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说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因此变成了这样。我从而得到了很多益处,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也丧失了很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
“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K问,他想先赢得画家的信任,之后再把画家列入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
“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无法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可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全部画,我一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但是,即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和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K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喽?”
“对,无可替代,”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
“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K问,似乎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迪托蕾里不让K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
画家再次提到K的无辜,K觉得有些不耐烦了。有时K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价值了。然而,K只是在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上却没说出来,而是听任画家一味地说下去。他已经打定主意,不想拒绝迪托蕾里的帮助。画家和律师都一样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他更愿意接受画家的帮助,因为画家的提议更诚恳、更坦率。
迪托蕾里将椅子拽到床边,压低调门,继续说:“我忘了先问一句,你想得到哪种形式的无罪开释处理。有三种可能性,就是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自然,彻底宣判无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这种判决是我无法插手,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的。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可以促使他们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大概是被告的清白无辜。既然你是无辜的,你自然可以把自己的无辜作为在本案中为自己辩护的根据。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就无需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了。”
一开始,K对这种理性的分析感到惊讶,但然后,他却用同样轻微的声音回答画家:“我认为你有些自相矛盾。”
“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他回以微笑,把身体向后仰去。K对画家的微笑心下怀疑不已,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说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不过他并未灰心,还是接着往下说:“你刚才说过,法院不理会证词,后来你又说,那种说法只适用于法院公审时;而你现在却以为,在法院里,一个无辜的人根本无需别人的帮助。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此外,你开始时说过,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你却否认个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称之为彻底宣判无罪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
“这些矛盾很易于解释,”画家说,“我们需要把两样东西区别开来: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你不可以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在法典中——我得承认我不曾看过——一定写着无辜者应无罪开释,那上面不会指出法官可以被影响。我的经验则与此截然相反。我不曾看到过任何一桩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彻底宣判无罪,但我却见过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干涉判决的例子。自然,也可能在我所了解的这些案子中,没有哪一个被告是真正无辜的。然而,这真的可能吗?那么多案件中,竟然没有一个被告是无辜的吗?我小时候就很用心聆听父亲说他听闻的那些案件;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要说起法院里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事实上是唯一的谈资。我自己开始为法官画像后,也尽可能利用了这种好处,了解到无以数计的案件在最关键阶段的情况;我还尽可能留意这些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然而——我得承认——我从不曾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
“这么说,没有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开释,”K说,他似乎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冀说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形成的看法:从各种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所有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
“你不可以把这种情况普遍化,”画家不快地说,“我仅仅是说了我的个人经验。”
“这也足够了,”K说,“你以前听说过无罪开释的事吗?”
“据说,”画家回答道,“曾经有过这种无罪开释的例子。可是,要证实这点却极其困难。法院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作记录,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细。所以,提到过去的案例,我们只能依靠传闻。这些传闻一定提供了宣判无罪的案例,实际上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无罪开释;这些传闻可以相信,但不可以证实。无论怎么说,不可以全然置这些传闻于不顾,其中总有些部分是属实的;此外,里面有些情节很动人。我自己就根据类似的传闻画过几幅画。”
“仅仅是传闻不可以改变我的看法,”K说,“我想,人们总不可能在法庭面前求助于这些传闻吧?”
画家笑了起来。“不可以,不可以那样做。”他说。
“那谈论这些传闻就没有用处了。”K说。他当时想要接受画家的看法,即便这些看法看上去也许很荒唐、抑或跟K以前听说的有矛盾也没有什么妨碍。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调查画家说的话是否完全属实,更不想反驳;他只希望画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便得不到什么结果也没关系。于是他说:“那咱们就不谈彻底宣判无罪了,你刚才还提到过其他两种可能性呢!”
“诡称宣判无罪和延缓审理。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在你我接下去谈话之前,你是否可以把上衣脱掉?你似乎很热。”
“好的。”K说。他刚才一心听画家说话,把其他事情全忘了;眼下经画家一提,他才发觉这房间里真是闷热,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满汗珠。
“简直热得难受。”画家点点头,好像他非常理解K的不舒服感觉。
“咱们不可以开窗吗?”K问。
“不行,”画家回答,“那上面只有一块玻璃,固定在房间顶上,没法打开。”
K这时才明白,他刚才一直盼着他自己抑或画家会突然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只要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哪怕同时吞进几口烟雾也行。与新鲜空气完全隔绝的感觉使他顿时头昏脑涨起来。他把手掌平放在羽毛褥垫上,用微弱的声音说:“这既不舒服,也不卫生。”
“哦,不对,”画家为自己的窗子辩护,“它是密封的,虽然只有一层玻璃,却比双层玻璃更保暖。倘若我想透透空气——这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墙缝全透风——,只需要开一扇门,抑或把两扇门全打开就可以了。”
听了这个解释,K略微安心了,立刻扫了四周一眼,寻找第二扇门。画家猜出了K在干什么,便说道:“在你后面,我不得不用床把它顶上了。”K这时才发现墙上有个小门。
“这间房间子作为画室实在太小了,”画家说,好像他知道K会发表评论,于是便抢先说了一句,“我尽量作了安排,床紧挨着门,自然摆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现在正给他画像的那位法官来说,他总是从这道门进来;我得把钥匙交给他,这样的话,倘若我不在画室里,他可以自己先进来等我。他嘛,一般总是早晨来,我还睡着呢。自然,无论我睡得多热,只要床后面的这扇门一打开,我就会醒过来。他一早就从我床上爬过来,倘若你能听见我怎么用骂声欢迎他,你就会失去对法官的一切崇敬心理。我自然可以从他那儿取回钥匙,但是只能使事情更糟。撞开这里的任何一扇门都很容易。”
他们在交谈时,K一直在考虑是否把上衣脱掉,最后他明白了,倘若上衣不脱掉,他就无法在房间里再待下去;于是他脱掉上衣,搁在膝盖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谈话结束后,再穿起来就省时间了。他刚脱下上衣,一个女孩就叫道:“现在他把上衣脱掉了。”他知道,现在她们全挤在门口,想透过门缝亲眼看看。
“女孩们以为,”画家说,“现在我要给你画像了,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脱外衣的。”
“我明白了。”K说,他并不觉得多么有趣;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却比刚才舒服不了多少。他闷闷不乐地问道:“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什么?”他已经忘掉这两种可能性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