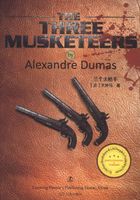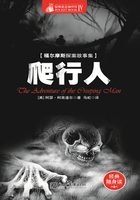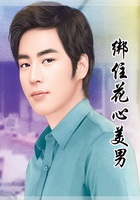漫长的冬天又冷又硬,像一块冰凉的磨刀石。
北风像是从磨刀石和刀刃:之间摩擦而出,把村庄里土路上的尘土落叶搅和得不得安生。在北风的尖唳中,常常夹杂着一种像冬天一样粗糙沙哑的嗓音:磨剪子嘞,戗菜刀一幽远而悠长。
这声音在年终那几天甚至能将北风的势头压下去。那时,我和伙伴们在北风里追逐着那些飞扬的树叶狂奔。我们远远地看着一个背着条凳的老头走进村庄。他在村头就吆喝起来:磨剪子嘞,戗菜刀——我们踩着他的吆喝声朝家里奔跑。我在门外就喊:“爹,磨刀的来了!”我爹便拎着钝菜刀走出院门,寻着声音走去。
磨刀老头把条凳放在村子的一个十字路口,扯着嗓子喊两声。他的喊声似一块磁铁,将村里的一把把钝菜刀吸了过去。十字路口是磨刀老头儿的工作场所——人们邀他到避风遮雪的屋里,他总是笑笑,婉拒了‘。于是人们也围着老头站在风雪中。
老头给我的印象是磨刀,而不是戗。他的条凳上固定着一块磨刀石,残角的。他先往磨刀石上洒些水,然后在条凳一端坐定,接过一把刀,右手执刀柄,左手握刀背,双臂往复伸曲,身子也来回运动,就像奏着一首舒缓的曲子。而人们则沉醉在那首悦耳的曲子里,盯着在磨刀石上来回奔跑的菜刀发怔。刀刃在磨刀石上锵锵地奔驰,似乎把冬天削得更薄更利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像揣了一个冰块似的发抖。然而,我却愿意哆嗦着看他在风中潇洒自如地将一把把钝刀磨得贼亮,亮光似乎照彻了整个冬天。
磨刀老头隔些日子就来一趟,不避风雪。他踩着北风的头颅呼啸而来,骑着飞雪的背脊款款而来。那时候,他身材魁梧,步履矫健,整个冬天都是他的王朝。我们在村庄土路上狂奔着,不时朝村头望去,期待着他走进村庄时的几声吆喝。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大人们也从没问过他是哪里人。他们把刀递给他时,往往只是说:“来了?”
老头嘴角一动,说:“有些日子没过来了。你们的刀都钝了吧?”
大人们笑笑说:“就等着你来呢!”
老头已经坐在条凳上了。他接过刀,立刻绷起脸,不再说话。
多年后的一天,老头在磨刀时说话了。我记得那个冬天雪花飞扬。老头在村头吆喝了几声,我爹就让我拎着刀出去了。我看见他走进村庄的时候在路口摔了一跤,他肩上的条凳甩出去很远。没等我走过去,他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把条凳搭在了肩膀上。然后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吆喝起来:
磨剪子嘞,戗菜刀——声音像雪花一样随风颤抖。我看到他的左臂在不停地打战。我走过去,对他说:“你没事吧?”他乜斜了我一眼,微微点点头,没吭声。不少人已经拎着刀走了过来。老头在条凳上坐下,接过了我的刀。我看到刀刃在渐渐变亮。谁说了一句:“今天雪太大了,到屋里去吧?”
老头低着头,说:“雪确实挺大的!”然后他的左臂突然抖了一下,左手滑到了刀刃下,鲜血立刻汩汩而出。人们怔怔地站着,竟然不知所措。
老头扯出一块破布,缠在左手上,说:“乡亲们,实在是对不住,今天磨不了啦!”人们纷纷说:“到家包扎一下吧!”老头摆摆手拒绝了。然后他单用右手收拾起家什,挂在条凳一头,肩起条凳,缓缓走进了茫茫遮天的大雪中。
那年的刀实在太钝,我爹只得凑合着在水缸上磨了两下。第二年冬天,我和爹在村外遇见了磨刀老头。老头伛偻着背,肩着条凳说正要去我们村。我爹回到家立刻让我出去磨刀。可我在十字路口等了好半天,也没见老头来。我支起耳朵,只听见北风放肆的尖叫。
多少年,人们一到冬天就开始盼着磨刀的老头吆喝着走进村庄,在十字路口为我们磨刀。但老头像被风刮跑了似的,再没来过我们村。人们开始自己买磨刀石,在自家院里把整个冬天磨得刷刷响。
那一年,我爹老去,我的儿子也开始和小伙伴们在村里追逐着雪花疯跑。那时,我正在家磨刀,儿子突然奔进院子,叫喊道:“爸,磨刀的来了!”儿子声音的尾巴上是一声响亮而悠长的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
我忙跑了出去。我看到一个中年人正在十字路口摆条凳。我走了过去。中年人看到我手里拎着刀,朝我笑笑,说:“磨刀?”我也笑了笑,把刀递给了他。他接过我的刀:放在一边。然后往一块残角的磨刀:石上洒了些水,就坐在条凳一头,磨起我的钝刀。他的双臂往复伸曲,身子也来回运动,就像在奏一首舒缓的曲子。
中年人把刀递给我时,还没有第二个人来磨刀。他对着大街喊了两嗓子,仍旧没有人出来。他收拾起物什,肩起条凳朝村外走去。我愣在那儿,怔怔地望着他。他走出很远,仍在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一一暴君似的北风总是试图将这个不和谐的声音斩断,可它却倔强地清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