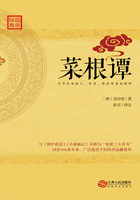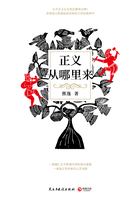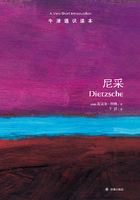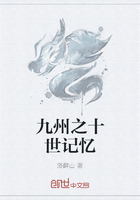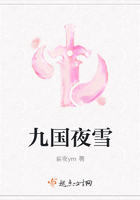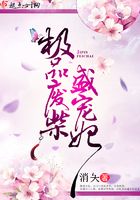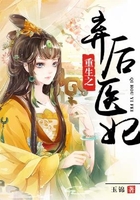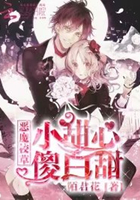下面是一个有趣的提示:在这两个案例中,我的反应就好像肉体论和人格论是脱节的,因为两个人的身体都保持原位不动,而人格被置换了。但是有可能这并不正确。毕竟,我之前曾提议说最好的肉体论版本可能是大脑论,在这个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躯体发生了什么,而是大脑发生了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当疯狂的科学家把我的人格装进琳达的身体时,他必须调整琳达的大脑,让它更像我的大脑。那么,搞不好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真的是我的大脑在那边,在琳达的体内!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格论和肉体论(至少是肉体论的大脑版本)应该一致认为我会在那边醒来,带着我的人格和大脑一起。那么,这可能给我们以理由去支持如下的结论:我在两种案例中都移动了——因为在两种案例中我的大脑和人格都被移动了——这证明了两种直观反应中,第一个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提示说明当我思考第二个案例的时候,我过于在意我躯体的位置,对大脑的位置关注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不再考虑第二个案例中产生的直观反应。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趣的提示。但是我认为它是错的!我认为说我的大脑被移动了,这并不正确。假若你问我:置换意识之后,谢利·卡根的双腿在哪儿?它们仍在这儿。我的心在哪里?还在这儿。那么同样,我的大脑在哪儿?也还在这儿。毕竟,疯狂科学家做的并非是打开我的颅骨,把我的大脑取出来。不是的,整个过程是电子传输的。他没有换掉琳达的大脑,他只是改变了它的程序。
下面这个类比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想一想计算机和保存在该计算机上的程序及文件之间的区别。某个人的人格有点像某种特殊的程序和数据文档。疯狂科学家做的实际上是完全清除了琳达硬盘上的内容,然后从谢利·卡根的电脑上下载了各种程序和文件,但是中央处理器和硬盘不变。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当然,在传输之后,琳达的大脑确实在某些重要的方式上跟谢利·卡根的大脑(传输前)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我们问谢利·卡根的大脑最后会在哪儿,答案仍旧是在这儿,它一直在的地方,而不是在那儿。
因此,在我们的故事里,身体的确是原地不动的(包括大脑),而人格是移动的。因此,两种个人同一性的理论,即肉体论和人格论,在关于哪个最终产物是我的问题上的确有分歧。但问题是,当我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确切来说,这取决于我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尽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二者看起来完全是同一个故事。
结果是这样的。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思考这“对”案例并非真的那么有帮助。如果我们要在肉体论和人格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不同的论证。
复制
如果要在对立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另一个独辟蹊径的方法是以反驳人格论开始的。这个观点认为人格论似乎存在某种我们无法接受的含义。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舍弃人格论,转而接受肉体论。
反驳如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根据人格论,某个人是我取决于他是否有我的信仰、记忆等。比如,我相信我是谢利·卡根,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当然,我并不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那么让我们戏剧化一点儿,来想一下拿破仑。或许你读过这种故事:时不时就会有个疯子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想象一下,现在密歇根精神病院里有个人有了这个想法:“我是拿破仑。”那么,反驳观点是:显然这个人只不过是疯了,对吗?他不是拿破仑。他是大卫·史密斯,在底特律长大,疯狂地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但是,根据人格论的说法,他真的就是拿破仑,他有着拿破仑的信仰和人格。所以,这一反驳的结论是:因为这样说很明显是不对的(他不是拿破仑),我们应该否定人格论。
别那么快下结论。人格论并没有说一旦某个人拥有我全部人格里的一个元素就是我,拥有同一个信仰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你看,我们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这不足以让别人成为我。当然,相信“我是拿破仑”是一个更少有的想法。我假定你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当然也没有。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这么想,密歇根的大卫·史密斯也这么想。但是,那又怎样呢?根据人格论,一个想法,甚至一个非常罕见的想法,也不足以让某人成为拿破仑。要成为拿破仑,你必须要有完全相同的全部人格,也就是一个非常大且复杂的想法、欲望、野心和记忆的合集。
大卫·史密斯没有那样的合集。密歇根精神病院里的大卫·史密斯没有当皇帝的记忆,没有征服欧洲的记忆,也没有战败、流亡厄尔巴岛的记忆。他完全没有这些记忆。而且,拿破仑说法语,可大卫·史密斯不是!诸如此类,拿破仑所有其他的记忆、信仰、欲望、目标和打算他都没有。简而言之,大卫·史密斯并非真的拥有拿破仑的人格。
大卫·史密斯的案例并没带来麻烦,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格论反例。因为人格论说的是,要成为拿破仑,你必须得有拿破仑的人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大卫·史密斯认为自己是拿破仑,他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甚至人格论的支持者也能同意此结论。所以,这个例子并没有对人格论造成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改进这个例子。有些人格论的否定者可能会让我们想象,密歇根的那个疯子现在的确有了拿破仑的人格。他有加冕为帝、征服欧洲、战败等记忆;他讲着流利的法语,拥有所有拿破仑的想法、欲望、目标和恐惧。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设想的时候,既然在努力想象这个人真的有拿破仑的人格,而不是拿破仑和大卫·史密斯二者人格的奇怪混合体,那么最好也假设精神病院的那个人没有任何大卫·史密斯原先的记忆、野心或者目标。比如,他不记得自己长在底特律等。(拿破仑怎么可能会有长在底特律的记忆?拿破仑是在法国长大的!)那么,反驳观点会说,即使这个人的确拥有和拿破仑一模一样的人格,他仍旧不是拿破仑。所以,人格论是错误的。
这次,我们正确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次,人格论确实必须得说这个人就是拿破仑。然而,我现在不那么确定这样说就是不对的了。
让我们从拿破仑的角度来想象这个情况。在19世纪,他被加冕成为皇帝,征服了欧洲,最终战败。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死在圣·海伦娜。真的拿破仑拥有所有这些生病和病入膏肓的记忆。光线渐渐暗淡,他失去了意识,然后他醒了过来——或者至少我们试着这么来描述——他在密歇根醒来。他想:“你好。我是拿破仑!”剩下的思想活动我将用英语写,但请想象他这么想的时候用的都是法语:“我是拿破仑!我在密歇根领土上做什么呢?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病得很重,在圣·海伦娜岛的床上睡觉。我怎么会到这儿?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重组我的军队,然后征服世界。”
你能想象出这个场景吧。我们接着加入如下的细节:有个人在密歇根,但是现在他获得了一个人格,完全与拿破仑的人格连贯重合。
如果真是那样,我压根就不清楚说“他是拿破仑”是否不对了!我的意思是,那多奇怪呀。这样的事并不会真的发生,但我怀疑如果类似的事的确发生了,我们也许会说拿破仑以某种方式重生或转世了。通过某种“附身”的过程(我们可能这么说),拿破仑接管了大卫·史密斯的身体。以前它是大卫·史密斯,现在它是拿破仑。我发现自己觉得这么说可能是对的。
当然,这时候,有人可能担心我们操之过急。比如,这个人真的有拿破仑的记忆吗?这难以说清。毕竟,拿破仑——真正的拿破仑——经历过加冕,但这个人并没有。也许我们应当说他以为他记得登基为皇帝的经历,但那是假的记忆。其实那是幻觉,或者可能是错觉——是类记忆(a quasi-memory),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但是不管怎样,他并非有真的记忆。要想有真的记忆,他必须得真正是那个加冕称帝之人。但他不是,拿破仑才是。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能会说的,但在我们认定他不是拿破仑之前,还不应该这么说。毕竟,如果他真的是拿破仑,这些就不仅仅是类记忆,而是真正的记忆。如果你笃信它们不是真记忆,而是幻觉,那一定是因为你不认为他是真的拿破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相信人格论。(但是谨慎起见,也许我们应该从类记忆的角度来阐释人格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先确定某个人是谁,然后决定他是否有相关的人格。)
为什么他不是真正的拿破仑?如果你认为他不过是个被迷惑的冒充者,而不是真的拿破仑,一定是因为你认为关键在于他没有拿破仑的肉体。至少,这是肉体论者希望你说的。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制造像拿破仑一样的人格,但这并不能达到目的。要想成为拿破仑,你得拥有拿破仑的肉体。
正如我所说,我不确定那样说是不是对的。假如密歇根的那个家伙有一个记忆(或者类记忆,如果你更愿意有所保留地如此表达),这个记忆来自拿破仑的生活,但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此事,也从未在日记里写下过,也没有在任何讲话里提及。密歇根的那个人想:“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法国玩耍,我埋藏了自己的玩具小军刀。”假如我们开始在法国挖掘这个军刀,且肯定的是,找到了那把军刀!假如这个人熟知各种只有拿破仑自己才知道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在想,这样的话,他就可能真的是拿破仑。
或者,假如像拿破仑这样的案例每天发生。每隔几天,就有人被“附身”了,一个新的人格取而代之,原有的人格了无踪迹,且这个过程从未逆转。想象一下,若对于这整件事做出某种详细的物理解释,我们会说什么呢?如果这种事发生得足够频繁,我想我们很有可能会说一个“新”人——这个人的人格现已就位——已经接管了之前由另一个人占据的身体。我怀疑我们就不会追踪肉体,我们支持的是人格论。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拿破仑的例子有力地反驳了人格论。老实讲,基于各种直观反应我准备接受人格论,但我对这些直观反应并无十足的把握。尽管如此,思考这个案例也不会让我完全摒弃人格论。
但我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拿破仑的例子!以前法国有个拿破仑,有他自己的记忆、信仰等。死神来了,他失去了意识。之前我讲了一个他在密歇根醒来的故事,或者至少他的人格以某种方式传输到了密歇根。但是,如果这种事可以在密歇根发生,我想它也能在纽约发生;如果既可以在纽约也可以在密歇根发生,我想这种情况在纽约和密歇根都可以发生。因此,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有两个人都有了拿破仑的人格,其中一个在密歇根,另一个在纽约。
呀!那么我们现在该说些什么呢?人格论对此又怎么讲?
我认为画图有助于我们厘清自己的选择。让我们画一幅拿破仑的人格来到密歇根的图,仅到密歇根。我完全不确定如何画人格,所以实际上画了一种小棒人;不过我所指的是人格阶段,而不是身体阶段(见图7.1)。在图的左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时不断发展的人格。让我们假设,就在这条线的左侧,拿破仑的人格跟死前别无两样。然后在线的右侧,拿破仑的人格得以继续,只不过现在我们发现它到了密歇根!
我可能应该在此提及一个观点,因为之前我对此不是很明确。就在线的右侧,当拿破仑的人格首次出现在密歇根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人格当然跟线左侧的那个阶段非常相似,也就是死前的人格,其记忆、信仰、目标等几乎会完全一样,这两个阶段的人格将完全“吻合”。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人格当然会继续改变和发展。身在密歇根的那个人将继续学习新的事物,获得新的记忆,树立新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身在密歇根的那个人的人格阶段与身处欧洲的拿破仑的人格阶段,两者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但是,这对线右侧那个身在密歇根的人是且一直是拿破仑的主张,不构成任何威胁,很多支持人格论的人都赞同这个说法。毕竟,历史上真正的拿破仑其人格也是不断发展的。当然,需要记住的是,我们要把人格视为可以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可以允许它改变,只要不是特别突兀,有着相似的重合和延续模式。
既然我们想象,我们讨论的例子里确实有这种重合和延续模式,那么线右侧身在密歇根的人和线左侧的拿破仑有着相同的不断发展的人格,这种说法就是恰当的。当然,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纳了人格论,不仅线左侧的,而且线右侧的也确实是拿破仑。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所有不同的人格阶段,不管是线的左侧还是右侧,都用一个圈圈起来,以此来标注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一个人,即拿破仑。
下面,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新版本的拿破仑案例,除了密歇根的某人有了拿破仑的人格,纽约的某人也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见图7.2)。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当然,如果没有密歇根的那个家伙,我——如果我支持人格论的话——就会在身处欧洲和纽约的不同人格阶段周围画一个圈,以标明在线的两侧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不断发展的人格。我会说:“哦,看呐,拿破仑在纽约转世了。”这就是基于人格论的说法,如果纽约的那个人是唯一在今天仍拥有拿破仑人格的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