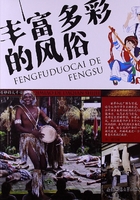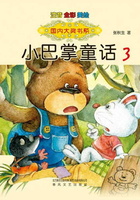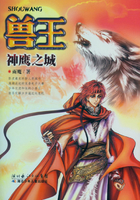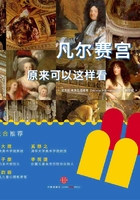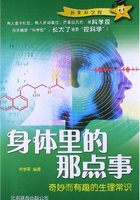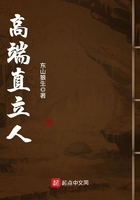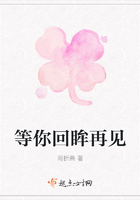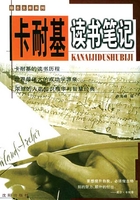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从哪儿知道安徒生这个名字,如何读到了他的这些童话作品。
想起来真是奇怪,那时候全社会都把外国文学作品视为妖魅,藏着掖着也会被人揭发,以至于写检讨、挨批斗,我一个小小城镇上的普通教师的孩子,是如何读到了《海的女儿》和《丑小鸭》?努力回想,依旧茫然。
能够解释的只有一点:人类需要审美和想象,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总会有野花不屈不挠地开出,总会有阳光的香味丝丝扣扣散发。
第一次完整地阅读安徒生,已经是“文革”结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我读中文,又是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安徒生自然必读。
可怜那时候外国文学作品还没有被允许出版,我只能在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去图书馆外国文学阅览室排队抢位。
排一个小时,能换到最多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坐在灯光雪亮的狭小空间里,手中翻着稍不注意就碎的发黄的书页,鼻子里充满了纸张年久生霉的气味,目光机械地、匆匆生还是竖排版。
不过也许是错觉。
人的记忆实在最不可靠。
学在中国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文学作品印数最多、销量最大的时代。
几乎从女儿满月开始,我就蚂蚁搬家样地从新华书店搬回各种童话的文字本、绘图本、拼音本、缩略本。
非常清楚记得的一幕,是女儿睡在床上,我倚在枕上,给她读《海的女儿》。
读着读着,她的小嘴巴一扁一扁,晶亮晶亮的泪珠儿就慢慢地涌出来,溢满了眼眶,又噙住不散。
那时候女儿不过三四岁。
至多三四岁。
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为安徒生着迷、伤感和哽咽,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不凡。
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去年还写过一本《中国童话》。
每次把自己的作品交到编章手中时,我很得意,因为我的文字怎么读都是一个顺畅。
每次翻开安徒生的作品再对照自己,我又沮丧,明白丹麦的大师的确是一座高山,今生今世要想翻过山去,很难很难。
四十五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买《安徒生童话》,是译林版的精装本。
四十八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读安徒生童话,是叶君健的译文。
不不,不能说“最后”,只能说“最近”,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还会再买再读。
我读着,不是在北大时的疯狂吞咽,是饱食之后的反刍,细细的,悠悠的,丝一样绵长和阳光一样温暖的。
这样的阅读,是生命中无以企及的享受。
感谢安徒生。
有了他,我们才有了童年,有了梦想,有了忧郁、感恩和伤情。
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孩子们有了快乐。
走过的路
写作就是写作,并不经常停下来想:我为什么要写?如果真这样做,要么是故作高深,要么就是在我们中间将出现一个黑格尔或者马恩列斯毛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必须时时思考诸如此类的形而上的命题。
写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东西,从生命中抽出来的一根细细的丝,总也抽不尽,甚至不抽也会自动地游出来。
如果不将它及时地捺到纸上成为文字,它就要像放赖一样地纠缠住我们,裹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颈,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总之让你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行动。
你想安安生生睡个觉吗?不行,它偏要撑住你的眼皮,让你失眠,或者梦里只见它一个;你想装扮整齐去歌厅舞厅潇洒潇洒?也不行,它盘缠在你的耳朵里大声地叫呢,你的耳道不可能绕开它专心听音乐;去旅行?怎么可以把它长时间地丢在家中孤独一个!去交易大厅看看股票是升是降?更不妙了,它生起气来会把你的心情搅得一塌糊涂。
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讨厌的小东西。
但是,只要你安安静静坐下来,耐着性子把它丝丝缕缕地捺在白纸上,一切就变得美妙了。
它有着金子一样的延展性,愿意拉长或者缩短,它随你。
它又有着橡皮泥那样的黏性,捏猫成猫捏狗成狗,乖得叫你不好意思。
你只要把弄它,花时间盘玩它,它就高兴。
至于你能够把它弄成个什么模样,这是你的水平,与它无关。
这就是我对写作这玩意儿的认识。
当初怎么被它缠上了身子的呢?说起来更不好意思,几乎没有半点“我愿意”的成分。
我父亲年轻时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至于水平怎么样,我不好枉自评说,因为我几乎没看过他发表的作品,“文革”开始时一把火统统烧掉了。
父学的文学情结却始终深植在他心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根深蒂固地繁茂成一棵大树。
到我长至十七八岁时,中年的父亲知道自己圆梦无望,遂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卸到我的肩上,望女成凤地期盼我在文学上有点出息。
我的第一篇习作其实是一篇作文,父亲指导我如何在作文的基础上增加虚构的成分,使之发展成一篇小说。
一九七二年,我的这一篇又像作文又像小说的东西,出人意料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朝霞》丛刊创刊号上发表。
拿到出版社挂号寄来的杂志,我几乎不敢相信。
至于这篇作品如何流落到上海,又如何进入“丛刊”编章部,这是又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总之绝非我或我父亲的自觉投稿。
在父亲,恐怕是深知投稿的艰难而不敢轻举妄动;在我,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投稿”这么一说。
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说总是发表了。
父亲欣喜若狂,我估计他比发表自己的作品还要开心十倍。
父亲勤快地督促我再接再厉创作第二篇作品。
上帝保佑,小说很快又在省报发表,占据了副刊整整一个版面。
我仍然不太知道庆幸。
那时候我的状态,准确地说是“少女无知”,或者“懵里懵懂”,冥冥之中是上帝之手在安排我的一切。
对写作这么一件事,我心里既不甜也不苦,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大饼到了嘴边,张口就吃下去,就那么一种感觉。
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
“文革”后期,真正的作家们还没有开始动笔写作,以至于我这样歪打正着的稚嫩小儿得以成了一点气候。
虽说那年头发表作品没有稿费,在家乡人心目中还是受到敬重和赏识的。
这是写作之外得到的最大愉快。
七四年我下乡插队。
父亲认为我日后离开农村的唯一道路就是写作。
此言一出,我深感拯救自己的努力任重道远,从此勤勤恳恳不敢有丝毫懈怠。
夏天是掖好了蚊帐门趴在草席上写,冬天哆嗦着坐在油灯下,一夜到天明两个鼻孔熏得乌黑。
说实话我仍然没有感受到写作的乐趣所在,我拼命地鞭打自己勉励自己,只为着饭碗和生存的需要。
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恐怕十有八九出于跟我同样的功利目的。
写作没有什么神圣,它就是一架天梯,缘着它一级级地攀上去,可望能看到世间最美的风景。
对于写作,无所谓痴迷,更无所谓疯狂,有的倒是清醒,是算好了尺寸一步步走过去的冷静。
七七年考入北大,由写作找出路的功利目的算是解除了。
班上喜爱写作的同学很多,便商量着成立了文学社,我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大学四年,主课不敢马虎,业余活动又不肯错过,只好把背外语单词的时间统统用在写作上,以至于我的英语水平一直停留在小学阶段。
回想那时候笔耕不辍的原因,四分之一出于习惯,四分之一出于争强好胜,四分之一出于喜欢,最后的四分之一仅仅是想挣钱,拿点稿费贴补生活。
二十多岁的我实在羞于向父母伸手要钱买饭票菜票。
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精力最充沛的一段时间,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一段时间,读书最系统也最贪婪的一段时间,因而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领悟。
我非常感谢北大四年。
八四年,我从江苏省外事办公室调入江苏作协,任专业作家。
那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我们的创作组称为“青年创作组”。
组员们个个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大有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自豪。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走过中年,正在一步步地迈向老年。
我们读了很多书,行了很多路,也写了很多作品,但是距离自己当初的目标始终遥远。
未来尚有时日,无奈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之所以依然在写,纯粹是出于迷醉:对文字的迷醉,对笔下人物和故事的迷醉,对孤独的写作状态的迷醉。
如此,我的写作从被迫状态进入到自由状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几乎跟我个人生命的成长形成同步。
先是被人拽着我的手走,再是被裹挟着走,然后是不服气跟人比赛着走,最后才是心平气和、自由自在地步入辉煌,看到了文学殿堂里种种绮丽的景象,在心里轻叹一声:多亏没有半途而废!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还时常羡慕别人的职业:广告人、DJ、主持人、时装设计师、公关经理……心想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些尝试机会,如果有,恐怕十之八九我不会当一个作家。
四十岁以后我不再怀疑当初的选择,因为写作已经成了我的生命,世间再没有比它更吸引我、适合我的职业,它的的确确是从我心里抽出来的一根丝,细细的,长长的,连绵不断的。
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愿意选择当作家。
替生命做一点安慰
我的写作状态常常是这样:每当我结束了前一部作品的写作时,我的下一次灾难就紧接着开始。
我会陷入一种深不见底的黑暗,一种阶段性的忧郁症,不愿说话更不愿出门。
我坐着,或者躺着,闭上眼睛,与世隔绝。
然后,黑暗在我的身边游走,飘移,许许多多钻石一样的光亮倏忽即逝。
某些光亮爆发得比较长久,会持续几秒钟的灿烂,像节日之夜的一朵焰火。
它就在我的心里驻下来了,慢慢地凝聚起周围更多的火花。
黑暗越来越快地消失,花朵般的火焰遍地燃烧,让我的血液和思维跟着燃烧起来。
这样,最先从黑暗中浮出来的光点就成了我下一部作品的内容。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心跳着在书桌前坐下来,迫不及待打开电脑时,我的脑子里其实只有一团颤动的光亮,并没有清晰的人物和故事。
我只有在进入十分具体的写作过程时,才能让那一团混沌逐渐成形。
《枕上的花朵》,我写到一半的时候还在迟疑,反反复复询问自己:我写的是什么呀?我心里想说的到底是什么?一直到三分之二的篇幅过去,我写到在墨尔本的公交车站看见华人老太太跟白人司机争吵,一方操广东话,一方操英语,双方根本不可能沟通,却照样你来我往吵得不可开交时,心里面咯噔地响了一下,蓦然间透亮起来。
我知道我这篇小说的全部内容其实只表达了两个字:错位。
语言的错位,认识的错位,爱情的错位,生活的错位。
从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卷进时代浪潮之中,沉沉浮浮,寻寻觅觅,得到的和想要的总是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生活永远都不可能把完美的一面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只能是悲剧。
小说中“我”和女儿的无法沟通;余爱华对王强的一厢情愿;她和杰克父子的纠缠不清的状态;以及王强和他妻子、“我”和杰克、女儿和余爱华、余爱华和“我”、吵架的华人老太太和司机……所有这些两两相成的人物关系,都呈现着荒诞和混乱的状态,因其混乱而显出原生态的真实。
《玫瑰灰的毛衣》,写作的起因非常简单:有一次看一部外国电影,镜头里女主人公穿着一条玫瑰灰的长裙,从楼梯上款款走下。
那种颜色真是特别,比玫瑰红淡雅高贵,又比普通的灰色多了梦幻和华美。
我从此记住了那种颜色,从颜色又引发开许多的念头。
那段时间我正好想写一部中篇,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折腾自己,如何在社会中艰难寻找自己的位置,一点一点地将自己删削、变形,最后嵌入一个不大不小的规整空间的。
他们的学识,抱负,能力,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忍受日常生活的平静和平庸。
他们永远期待着前面有更好的风景,永远不满意身边周围凡俗的现状。
直待他们在花样百出的折腾中把多余的精力释殆尽,弄出一副头破血流、身心俱疲的悲惨模样,生命才能从喧哗归于沉寂。
我的脑子里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人物的轮廓和故事,“玫瑰灰”的意象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它们,使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开端,最后成就了这部作品。
《梦逍遥》写的是一个男人的性幻想。
实际上,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梦幻。
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婚姻生活百分之一百的满意,很多隐秘的念头是不可告人也不得被人而知的,它们是盘缠在身体中的蛇,不断地游走扭曲,咝咝作响,间或还要抬起头来四处窥探。
人类拥有性幻想是一件好事,生命会因此而多了一种期待,一种充满奇迹的向往,一种激动人心的美妙。
如果失去这样的想象,日子能够一眼看到头,活着也真没有什么意思了。
《玫瑰房间》和《危险游戏》写得比较早一点,前者写于八十年代末期,后者的发表距今也差不多快有十年了。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写悲剧,所有我钟爱的人物在作品最后都是以死亡终结。
我曾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出了毛病。
其实不是,是我的生活太过风平浪静,潜意识里就总是盼望制造出惊心动魄的突变。
两部中篇,表面看都是“爱情小说”,可我的初衷却不为写爱情。
《玫瑰房间》写的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危险游戏》写的是婚姻生活里普遍存在的“厌倦”感。
以爱情做主戏,仅仅为了方便构架故事,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罢了。
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自己认为小说是精神鸦片,它能使人短暂地愉悦和兴奋,却永远都是于事无补。
就像我写到的“枕上的花朵”一样,可以看着,欣赏。
你不能指望它变成真实的存在,有触觉,有香味。
但是我们又希望看到这些美丽的“花朵”,哪怕只能够每天枕着入梦,也是对我们脆弱生命的安慰。
为心灵点起一盏灯
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字迷。
在渴望读书实际上又无书可读的“文革”年代里,邻居家糊墙壁的报纸都能够让我独自面壁快乐许久。
十七岁,我在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处女作《补考》。
十八岁,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他们又长大了》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这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始。
上个世纪的八零年前后,我曾经集中写作了一大批儿童短篇和中篇作品,先后结集为《小船,小船》等四本小书。
之后,我转向了成人文学写作,跟儿童文学界完全没有了联系,似乎已经是“挥挥手说再见”的状态。
然而,在伴随自己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的快乐许多的苦恼许多的焦虑积攒在心,忽然有一天爆发成了一个决定:我要为我的女儿写一本书,记录下她在小学六年级这一年中真实的生活。
这样,有了江苏少儿社在九六年底出版的那本《我要做好孩子》。
短短一个月的快乐写作,耗尽了我十多年中养在心口的一脉血气,却也重新勾起了我写儿童作品的瘾头。
休养生息两年之后,我写出了《今天我是升旗手》。
二零零二年,再出新书《我飞了》。
再之后,是今年刚刚推出的《中国童话》。
我承认我的一大半精力和时间还是花在成人文学的写作上,儿童作品的数量不多,平均两三年才写一部。
这是因为我对儿童作品的写作慎之又慎,我不敢让我的编者失望,更不敢让我的小读者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