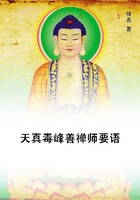这是福尔摩斯所经历的冒险中最突然、最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了。我很长时间没看见他了,也不知他近来在忙些什么,这一天早上他兴致极好,他刚好一边让我坐在壁炉旁的旧沙发上,一边衔着烟斗坐在对面,这时就有人来了。用一头发狂的公牛来形容来者一点都不过分。门“咚”的一声被冲开,闯进一个高大的黑人。若非面目狰狞,他会给人一种很滑稽的感觉。他穿着一身鲜艳的灰格西装,系着一条橙红色领带。他那宽脸庞和扁鼻子向前方使劲探着,两只阴沉的黑眼睛冒着熊熊怒火,不住地打量着我们两人。
“你们两位谁叫福尔摩斯?”他问道。福尔摩斯懒洋洋地举了一下烟斗。“哈,原来就是你呀!”这位来访者说着,以一种令人不悦的鬼鬼祟祟的轻步子绕过桌子。“听着,福尔摩斯先生,你不要多管闲事,大家各干各的。你明白吗?”“继续说,”福尔摩斯说道,“我很感兴趣。”“哈,你觉得有意思,对不对?”来人吼叫着,“等我收拾你之后你就绝对不会觉得有意思了,对付你这种人,一经收拾便老实多了。你看这是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他伸出一只硕大无比的拳头在福尔摩斯鼻子底下示威性地晃了晃。福尔摩斯颇为好奇地看了看他的拳头。“你天生就这个样子吗?”他问道,“还是后来慢慢练出来的呢?”也许是由于我朋友的镇静,也许是我抄起了拨火棒的缘故,总之一句话,这位来访者的态度突然间变得不那么趾高气扬了。
“总之我已经警告你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对哈罗那边的事很感兴趣,你知道我说是的是什么意思吧,他不希望你插手。明白了?我不是法律,你也不是法律,要是你再多管闲事,我可就不客气了。记住我的话对你只有好处。”“百闻不如一见啊,”福尔摩斯说,“我不让你坐了,因为我讨厌你身上的气味。你不就是那个搞拳击的斯蒂夫·迪克西吗?”“这正是我的大名,你说话最好客气些,否则我的双拳可不饶你。”“那倒不必,”福尔摩斯死死地盯着那位客人丑陋不堪的嘴巴说,“说说你在赫尔本酒吧外头杀死小伙子珀金斯的事。嗨!你别走哇。”这个黑人倒退了几步,面呈灰色。“少跟我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道,“珀金斯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小子死的时候我正在伯明翰斗牛场训练。”
“说得不错,这种话你还是对法官说吧,斯蒂夫,”福尔摩斯说,“我一直在注意你跟巴内·斯托克代尔的行径……”
“天哪!福尔摩斯先生……”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等我该说的时候再说。”“那再见吧,福尔摩斯先生。你不会计较我今天的举动吧?”
“但你得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那还用问吗,福尔摩斯先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他又是受谁指使的呢?”“老天,这我可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他就跟我说:‘斯蒂夫,你去找福尔摩斯先生,告诉他如果他去哈罗,生命就岌岌可危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的全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没等再问他别的问题,这位客人就一溜烟跑出去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福尔摩斯一面暗笑,一面磕去烟斗里的灰。
“华生,幸好你没用拨火棒敲破他那结实的脑袋。他实际上不碍事,别看浑身肌肉,其实是个蠢货,吓唬小孩子,很容易被镇住,就像刚才那样。他是斯宾塞·约翰流氓集团的一员,最近参与了一些无耻的勾当,我现在没时间对付他们,以后再说。他的顶头上司巴内却狡猾得很。他们专门袭击、威胁他人。我想知道的是,谁是这件事的幕后操纵者。”
“他们为什么要来威胁你呢?”“是因为哈罗森林案件。他们这么做反而增强了我侦查此案的决心,既然有许多人出动,来头必定不小。”“到底怎么回事?”“方才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闹剧就发生了。你看看麦伯利太太的信。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往,咱们就给她拍一个电报,立刻动身。”
我接过来,信上这样写着:
福尔摩斯先生:我最近遇到一系列怪事,都与我的住宅有关,热切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如您明日前来,我将全天在家恭候。本宅即在哈罗车站附近。我已故的丈夫莫提梅·麦伯利是您的早期顾客之一。
玛丽·麦伯利谨启
住址是:三角墙山庄,哈罗森林。“你瞧,就是这样,”福尔摩斯说,“你如果有时间,咱们就可以出发了。”我们乘了一段短途火车,又坐了一阵马车之后,终于到达了三角墙山庄。这是一座砖瓦木料的别墅,周围有一英亩天然草原的园地。上层窗子上面有三小垛尖形的山墙,算是“三角墙山庄”这个名称的标志。屋后有一丛半大的郁郁葱葱的松树。这地方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窒闷的,萧瑟的。室内的家具倒是颇为讲究,接待我们的也是一位风度翩翩岁数很大的夫人,言谈举止中显出她的良好的教养和文化。
“我对您的丈夫至今记忆犹新,”福尔摩斯说,“尽管从我为他办一件小事到现在已有许多年了。”“或许您熟悉我儿子道格拉斯的名字吧?”福尔摩斯非常有兴致地看着她。
“什么!难道您就是道格拉斯·麦伯利的母亲吗?他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不过,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实在是一位英俊、有魅力的男子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唉,死了,福尔摩斯先生,他死了!他是驻罗马的参赞,上个月患肺炎在罗马死了。”“真遗憾!谁又能想到他这样一个人会和死联系在一起呢?他是我见过的精力最为充沛饱满的人,生命力极其顽强。”“顽强得太过分了,反而毁了他的一生,夺去了他的性命。福尔摩斯先生,你印象中的他总是那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你根本无法想像他变得忧郁少言的情形,他伤透了心,一个月之间,我目睹他由一个优雅高贵的孩子变成一个失魂落魄的可怜人。”“是爱情,因为一个女人吗?”“一个女魔鬼。好了,我此次请你前来可不是为了谈论我的儿子,福尔摩斯先生。”
“华生和我都会尽力帮您的,请说吧。”“近来发生的事情极其古怪。我搬到这座房子里已经一年多了,我一直幽处独居,闭门谢客,过着清静的太平日子,所以同邻居极少来往。三天前我会见了一个来访者,他自称是经营房地产的商人,还说我家被他的一个主顾相中了,如果我愿意卖掉,价钱不成问题。我很不解,因为附近在出售的几处房产与我的条件大体相当,但是我自然对他的提议还是感兴趣的。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价格,比我买房时的价钱高出五百镑。交易一拍即合,但他又说他主顾连家具也想买,让我再说一个价儿。这儿有些家具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你可以看出那是极上等的家具,于是我就要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他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我本来就打算去国外看看,而这次交易我可以赚到不少钱,看来我往后的日子也很宽裕,不会有问题了。”
“昨天这个人带来了写好的合同。多亏我先让我的律师苏特罗先生看了一下,他也在哈罗居住。他对我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合同。如果你签了字,你就无权把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拿走,包括你的私人用品。’当天晚上那个人再次来的时候,我说了这一点,并言明我只卖家具。‘不,不只家具,而是一切。’他说。‘那我的衣服首饰怎么办?’‘放心,当然会考虑到你的私人用品。但是所有物品需经检查才能携出房外。我的主顾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但是他有他的癖好和习惯。对他来说,要不就全买,否则就不买。’‘既然如此,我不卖了。’我说,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儿实在稀奇古怪,我担心……”这当儿出现了意外。
福尔摩斯抬起手来打住了谈话,只见他大步抢到房间另一端“呼”地把门打开,抓住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的两肩,把她揪进房间。这女人拼命挣扎着,极不情愿地被揪进了屋,然后她开始像一只被抓出鸡笼的小鸡一样高声乱叫。“放开我!你要干吗?”她尖叫着。“苏珊?你怎么了?”“太太,我正要进来问客人是否留下用饭,这个人就扑上来了。”“她躲在门外偷听至少已经有五分钟了,但我没有打断您有意思的叙述。苏珊,你有点气喘吧?你干这事可有点不适合,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苏珊愤愤不平地但是惊讶地转向捉住她的人。“你到底是谁?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对待我?”“我只是想当面问你几个问题。麦伯利太太,您对谁提过您要给我写信,找我帮忙?”“没有,福尔摩斯先生。”“谁替您寄的信?”“苏珊。”“这就对了。苏珊,你把你家主人要找我的事对谁汇报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根本没报信。”“苏珊,气喘的人往往短命,而说谎的人下场更是不妙。你究竟告诉谁了?”“苏珊!”她的女主人大声说道,“你这个狡猾的坏女人!我想起来了,你曾在篱边和一个男人说过话。”“那是我自己的事。”苏珊生气地回答。“如果我告诉你,我知道那个和你说话的人是巴内,你会怎样?”“你知道了?”“本来我还不能完全确定,现在可以了。好吧,苏珊,如果你告诉我是谁指使巴内,我会给你十英镑。”
“十英镑算什么,别人经常给我好几千呢!”“这么说,是一个很有钱的男人?不对,你笑了,那一定是个富有的女人。直到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你何不说出名字?这现成的十镑马上就归你。”“我倒宁愿看你下地狱!”“说的什么话!苏珊!”麦伯利太太喊道。“我不干了,我受够了,明天就叫人来取我的箱子。”说着她拂袖而去。“再见,苏珊。别忘了用樟脑阿片酊……那么,”福尔摩斯等门一关上立刻又严肃起来,“这个集团对这桩案子多认真。你发现没有,他们的行动很紧凑。你给我的信上邮戳是上午十点。苏珊马上向巴内报信,巴内又刻不容缓地去请示他的主子,而这位主子,他,或她,我看很可能是女主子,因为苏珊一定是因为我说错了才笑了的,她下达了命令。黑人斯蒂夫被找了来,到次日上午十一点时斯蒂夫已经找到了我。你看,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他们有什么目的?”“这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你以前谁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一位姓弗格森的退休的海军上校。”“这个人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没听说。”
“开始我寻思他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虽然现在人们总是把金子存进邮政银行,但世上总存在着一些古怪的人,没有他们,生活该是多么单调无味啊。最初我设想是埋了珍宝,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要你的家具又有什么用呢?你总不会有什么拉斐尔原作或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而自己却丝毫不知吧?”“没有,我只有一套王室德比茶具,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值钱的珍品了。”“这种茶具是不值得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再说,他们完全可以公开说明嘛,如果要你的茶具,直接出高价买就可以了,何必包括一切呢?不过,依我推测,你家里一定是有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一旦知道你是决不会放手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道。“既然华生都同意了,那就一定是。”“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好,咱们尝试一下用逻辑分析能否界定一个最小范围。你在这里住了一年了?”“快两年了。”“很好。这个时间很长了,但此间从来没有人向你索要什么东西。突然间,在这三四天之内,出现了一个急切的需求者。你看这怎么解释呢?”“那只能说明,”我说道,“不管这东西是什么,它一定是刚刚进入住宅的,时间绝不会长。”
“说的很有道理。”福尔摩斯说,“那么,麦伯利太太,最近新买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今年我没买什么新东西。”“是吗!那就更令人费解了。好吧,我需要观察事态的进展,以便取得充足的资料。你的律师能力如何?苏特罗先生能力很强,办事精明。”“你还有其他女仆吗?不止是苏珊一个吧?”“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仆。”
“你最好留苏特罗在这座宅子里住一两夜,你可能需要某种保护。”“危险从何而来呢?”“这我不敢下定论,目前案子还很模糊。既然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我只好从他处着手,找到幕后人。这个自称房产经纪商的人留下住址了吗?”“只留下姓名和职业。海恩斯·约翰逊,拍卖商兼估价商。”“看来想通过电话簿找到他是没希望了,一般的商人绝不隐瞒营业地址。今天就这样吧,如果有新情况,随时通知我,我已经接手你的案子,一定会办好。”路过门厅的时候,福尔摩斯那观察细微透视一切的目光落在角落里堆着的几个箱子上面。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海关标签。
“‘米兰’,‘卢塞恩’,从意大利来的。”“这是我可怜的儿子道格拉斯的东西。”“还没打开看吧?到达多长时间了?”“上周刚到。”“但是你刚才却说……咳,这可能就是线索。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这怎么可能,福尔摩斯先生,道格拉斯只有工资和一小笔年薪,他怎么能买得起贵重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