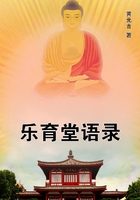爱,构成了灵魂的本身。爱与灵魂是同根的。它与灵魂一样,是神圣的火星;它与灵魂一样,是不可腐蚀的、不可分割的、不会湮灭的。它是一个火种,它燃烧在我们心中,永无尽期,永无止境,不受任何局限。人们感得到它,感到它一直燃烧到骨髓,感到它一直照向天际。
啊,爱情!啊,倾慕!两情相知,两心相印,两目相视,这就是快乐!这就是陶醉!你会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吗,幸福!清静中两两并肩散步!美满的日子!光辉的岁月!我有时梦见,时间离开了天使的生命,它下到尘世,在伴随人的命运。
上帝除非给予相爱者以无限的时光,否则,他没有别的办法增加他们的幸福。在爱的一生之后,会出现爱的永生,那是爱的延伸。而在此生此世便增加爱给灵魂带来的那种无可形容的强度,那是办不到的。上帝也办不到。上帝,乃是上界之饱和;爱,乃是世间之饱和。
你望一颗星,出于两种动机,一因它发出光芒,二因它深不可测。在你身边就是这样的一颗星。它神秘,但那是她。
无论我们是谁,都需要呼吸的物质。假使我们缺了它,我们会不能呼,也不会吸,我们就会死亡。我们不能因缺爱情而死亡。假使缺了爱情,我们的灵魂就会窒息。
当爱把两个人熔化掉,然后掺合起来构成极乐的、神圣的一体时,他们才称得上得到了人生的奥秘,他们方可构成同一命运的两极,变成一体的两翼。爱吧!飞翔吧!
有一天,一个女人向你走来,一边走着,一边发着光。这下你便陷入了,你便爱了。从这一刻起,你便只有一事好做,那就是集中全力去思念她,同时让她也思念你。
爱所开始的,只能由上帝来完成。真正的爱,会由于失去一只手套或由于找到一块手帕而懊恼,也可因此而陶醉,并且需要实现忠诚和希望的永恒。它既由无限大构成,又由无限小构成。假如你是石,你就要做磁石;假如你是草,你就要做含羞草。假如你是人,你就当作意中人。
爱是不知足的,有了幸福,想要乐园,有了乐园,想着天堂。
啊!爱中的你,你的一切便全在爱中。爱要靠你自己寻找。爱,对天,是仰慕;对地,是欢情。
“她还会来卢森堡公园吗?”“不会了,先生。”“她还到这礼拜堂来做弥撒吗?”“不来了,先生。”“她还在这房子里住吗?”“不在了,先生。”
“她搬到了哪里?”“她没有说,先生。”
啊!多凄惨哪!他竟找不到了自己的灵魂。
爱情带有稚气,其他感情带有小气。使人变得渺小的感情可耻,使人变成孩子的感情可贵。
出现了一种怪事,你晓得吗?我处在黑暗中。因为有人离开我时那天空也被带走了。
啊!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共同睡在一个坟穴里,黑暗中,彼此不时地抚摸着对方的手指,这已使我永远满足了。
为爱而苦,那就让爱来得更多吧;为爱而死,那就是为爱而生。
爱吧!苦境之中会闪现改观的星光。极苦之中有极乐。
啊!鸟儿快乐,那是因为它们有巢可栖,有歌好唱。
爱,是在呼吸天堂至上之气。
深邃的心灵,贞洁的精神,照上帝的安排接受生命吧!这是一种长久的考验,是一种未知的命运难以预测的预演。这种命运,这种真实的命运,是从人们踏出坟穴的第一步开始的。生命一旦开始,便有一种东西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便可分辨它是否属于确定之事。对“确定之事”这个词,务请你好生思考一番。活着的人只可望见无极,而“确定之事”,只有死了的人才可望见。在等待的时刻,爱吧!忍耐吧!要为爱而忍痛,要为希望而向往。冥想吧!唉!那些只爱躯壳、形体、表象的人是可怜的。因为这一切都会随着死亡而消失。应当知道去爱那灵魂,因为日后你总能找到它。
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被爱折磨着的穷青年。他的帽子是旧的,他的衣服是破的,袖子已经磨出了洞,鞋底被水浸透,但星光却照亮了他的灵魂。
被爱,是何等的大事!爱,这是何等的大事!心由于感情的激昂而变得壮烈起来。除了纯洁的东西以外,心里再也没有什么了;除了崇高和伟大之外,心再也无所依靠了。邪恶的思想再也无法在其中滋长,正如荨麻不得植于冰山。欲念和庸俗所不能攀缘的崇高的、宁静的灵魂踞于青天。它镇住人间的乌云、黑影,抑制住疯狂、虚伪、仇恨、虚荣和卑贱,所感到的,是来自命运之下深深的震撼,犹如山峰感知地震。
人间假使没有爱情,太阳也会熄灭。
五、珂赛特看信之后
珂赛特读着读着,渐入梦境。当她看完最后一行,抬起头来时,正好看见那个英俊的军官仰着脸从铁栏门前走过。珂赛特觉得他丑恶得不堪入目。
她再次低下头来,细细体味那些信。字迹异常秀美。它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从前,她受教育时,经常接触到灵魂,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爱情。那像是只谈炽炭而不谈火光。这15张纸上的随笔,把爱情、痛苦、命运、生命、永恒、开始、终止都一股脑儿温情脉脉地向她揭示了。那犹如一只张开的手,突然向她抛出了一把光明。它仿佛是一封天使致贞女的书柬。是世外的幽期密约,是孤魂给鬼影的情书。这简直是一个悲观绝望、准备安安静静地死去的陌生男子,把自己命运的秘密、把自己生命的钥匙、把自己的全部爱,寄给了一个陌生的女子。那是一只脚踏在坟墓里,手指伸在天空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那些字,那些一一落于纸上的墨迹,可以称之为滴滴的灵魂。
对于这样一沓没有写明收信人地址和姓名的信,珂赛特不产生任何疑问。她坚信,信是他写的,一定是他的。
想到这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啊!他给我写信了!他一定到过这儿!当自己快要把他遗忘的时候,他居然又一次出现了。那一沓纸,犹如从另外一个灵魂里燃着的炽热的炭块爆将出来、落在她的火中的火星,她感到,一场大火又在她心中燃起。那随笔里的每一个字她深深领悟:“是啊!我深深领悟到了一切!这完完全全是我往日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过的东西。”
当她把那手迹读到第三遍的时候,忒阿杜勒中尉又打那铁栏门前走了回来。他踏着街心的石块路面,靴上的马刺响作一片。这使珂赛特不得不抬起眼睛来望他一下。刹那间,她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实在是太丑陋了,不仅庸俗、笨拙、愚蠢,而且无用、轻率、无礼。
她迅速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反复阅读那几篇随笔,想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读了很多遍,她才亲了它一下,恋恋不舍地把信小心翼翼地塞在衬衣的口袋里。
就这样,珂赛特再次深陷于仙境般的爱慕之中。神仙洞府之深渊再向她开放。
一整天,珂赛特都处在如痴如醉的状态下,心里很乱,几乎什么也想不下去,只是一味地期待着。
六、好在老人走得及时
黄昏时冉阿让出门了。珂赛特开始梳妆。她的头发被梳成了最时髦的式样。一件裙袍穿在身上。那上衣的领口,曾有意多剪了一刀,这样,颈窝露出来了。她拼命地修饰着,自己也不晓得为了什么。天黑下来,她下了楼,到了园里。她来到了那条凳前。那块石头还在那里。
她坐下来,伸出一只白嫩的小手,把它放在那石头上,似乎要抚摸它,感谢它。
忽然,她产生了一种感觉:身后站着一个人——不必看,她感觉到了。
她转过头,随后站了起来。果然是他。
他没有帽子,脸色十分苍白,也瘦了许多。他的俊美的脸在晚间微光的照射下显得发青,两只眼睛隐于黑影之中。一层无比柔和的暮霭围绕着他,给了他一种类似幽灵和黑夜的意味。
珂赛特几乎要倒下去。但她没有喊,她感到,自己被吸引着。她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感到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说不上来的难以表达的忧伤的东西。
珂赛特退到一棵树前,便把身子靠在树上。要不是那棵树,或许她要摔倒了。
她听到了他的说话声。他吞吞吐吐,那声音比起树叶颤动的声音响不了许多。
“请原谅我的鲁莽,”他说,“不过,我实在太苦闷了。我简直没法活下去了。您看到我写的那信了吧,放在这石凳上的?您不要怕。您能理解我吗?假使……您知道!我崇拜您,我!请您原谅,我和您说话。兴许,我惹得您生气了。您生气了吗?”
听了他的表白,珂赛特整个身子瘫软了。他连忙过来将她搀住。她仍在下坠。他只得用手臂将她抱紧,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踉踉跄跄,觉得自己满脑子里烟雾缭绕。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一项宗教行为,却不知是犯了亵渎神明的罪。他怀里抱着这个动人的女郎,已感到自己的胸脯贴近了她的身体。他实在是被爱情弄得有些发昏了。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他感到了藏在那里面的那沓纸。他怯生生地问:
“您爱我吗?”“不用问,你应该是知道的。”珂赛特的声音宛若轻风。
她的脸羞得通红。随后,她把脸藏在了那个绝妙的、陶醉着的青年的怀里。
他们已经感觉不到晚间的凉意,也感觉不到石凳的冰冷、泥土的潮湿、青草的露寒。就这样,他们相互望着,思绪满怀,不知不觉之中,两只手又紧紧握在一起。
开始时,珂赛特偶尔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两句话。她的灵魂,犹如花上的一滴露珠,正在她的唇上抖颤。
后来,他们谈了起来。表示情真意酣的沉默已被衷肠的倾诉所代替。他们亲热的程度是无可再增添了。他们隐于内心的秘密是越说越多了。仅仅一个小时的工夫,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地沟通了;互相渗透了,互相陶醉了,互相照耀了。
当他们谈完时,当他们倾吐完毕时,珂赛特的头靠在了他的肩上,问:
“您叫什么名字?”
“马吕斯,”他回答,“您呢?”
“珂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