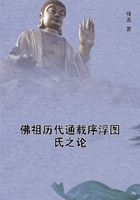她回想起少女时代在华特·司各特作品中读到过的那个场景。她仿佛听到苏格兰风笛声穿过浓雾在杜鹃丛中反复回荡。由于她对小说的记忆使得她很容易听懂台词。同时,一个个化解不掉的思绪很快消散在音乐旋风里。她完全陶醉在美妙的旋律里,感到有种整个身心的震颤,犹如小提琴的弓在她的神经上拉着。那些服装、布景、人物,一有人走路就直摇晃的道具树,令她目不暇接;那些丝绒软帽、大氅和长剑,所有设计奇妙的东西,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时有个年轻女子走向台前,她扔了个钱袋给一名年轻的骑士侍从。只有她一个人在舞台上,笛子吹奏出潺潺流水或小鸟啁啾的声音,她就是吕茜。吕茜神色庄重地唱起她的G 大调卡代蒂那。她悲叹爱情,渴望生出双翅。爱玛和她一样,想逃避现实生活,从包围中飞走。突然,埃德加·拉加尔蒂出场了。
他皮肤白皙,神采奕奕,给南方人的热情加上某种大理石雕像的威严感。他强健的身躯紧紧裹在一件棕色的短上衣里,一把镂花小匕首挂在他左腿上,他表现出忧郁的神情,露出洁白的牙齿。据说,一天晚上,他在比亚里茨海滩检修小艇,一边唱着歌。一位波兰公主听着他的歌声爱上了他,为了他不惜牺牲一切。他却抛弃她去追别的女人。这些风流轶事,更提高了他在艺术上的知名度。这个华而不实的骗子擅长交际,总忘不了在海报里加一些诗般的语言,夸赞他迷人的外表,聪敏的心灵。一副好嗓子,冷静沉着的风度,体格强壮但智商不高,善用夸张的言词,居然大大提高了这位混有理发师和斗牛士气质的江湖艺人的卖座率。
从他一出场就引起观众的轰动。他搂住吕茜,离开她,然后又回来,似乎感到绝望。他的声音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如嘶哑的悲鸣,显得无限凄婉。爱玛朝前探出身子看着他,手指甲紧紧地抠进包厢里的丝绒。那哀怨的歌声在大提琴的伴奏下更显得修长凄厉,就像喧闹的风暴声中溺水者的呼喊,一声声充斥着她的灵魂。她熟悉其中的种种痴迷和焦虑,就曾差点为此丧命。那女演员的歌声,与她的心灵产生共鸣,而令她着迷的幻想是她生命的某个构成部分。可是人世间没有一个人给过她这样的温暖。最后那晚,当他们在月光下互道“明天见,明天见!……”时,她并未像埃德加那样哭泣。剧场里爆响起喝彩声,他们把最后那段又重新唱了一遍,这对情人唱到他们坟头的鲜花、山盟海誓、远走高飞、厄运和希望,当他们唱到最后的诀别时,爱玛发出一声尖叫,融入了乐曲结尾的颤声。
“这位爵爷,”包法利问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她?”
“他怎么会是折磨她,”爱玛答道,“他是她的情人。”“可他发誓要向她的家人复仇,而刚才上场的那个说得好:‘我爱吕茜,我相信她也爱我。’再说,他和她父亲是挽手走的。那个帽子上插了根公鸡毛,相貌挺丑的小老头,一定是她父亲,对不?”
虽然爱玛一直给他解释,当吉尔贝向他东家阿斯东讲出他恶毒的阴谋,两人唱起二重宣叙调的时候,夏尔把那个欺骗吕茜的假订婚戒指,当作是埃德加送给她的爱情信物。他承认他看不明白,因为对话都是在音乐的伴奏下唱出来的。
“那有什么?”爱玛说,“安静点!”“这你是知道的,”他俯在她耳边说,“我想把事情弄明白。”
“安静点!安静点!”爱玛不耐烦了。吕茜由侍女们轻轻扶着走上台,头上戴着橘树花冠,脸色比她身上穿的白缎袍还苍白。爱玛回忆起结婚的那天,她仿佛又看到自己沿着麦田间的小路,和大家一起走向教堂。她为什么她当时没像吕茜这样抗拒、哀求呢?相反,倒是挺快乐,没想到自己正走向深渊……啊!如果她还是个美丽的姑娘,就能找到一个值得她托付终身的人,把贞操和柔情、享乐和职责寄予他一人之身,她也就不会做出伤风败俗的私通行为,而落到如今这个地步。然而,这种幸福全是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谎言。现在她明白了这种经过艺术夸张的爱情是那么一文不值。她竭力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只把台上的戏剧作为愉悦眼睛的多彩幻想,所以当一个身披黑色大氅的男子从舞台深处撩开丝绒门帘出来的时候,她的脸上甚至挂着轻蔑和怜悯的微笑。
那男子摘下他的西班牙式大帽子,这时乐队齐奏,演员们唱起了六重唱。埃德加无比愤怒,嘹亮的声音压倒所有的歌手,阿斯东用低沉的单调恶毒地伤害他的心,吕茜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怨诉,亚瑟在一边唱的是抑扬的中音,牧师的男低音像风琴的声音,侍女们合唱重复他的歌词,唱得美妙动听。他们边唱边做着手势,愤怒、报复、妒忌、惊恐、怜悯和诧异同时从他们半张开的嘴里吐出来。遭到侮辱的情人挥舞着他的宝剑,他的镂空花边绉领随着胸部急剧起伏,他穿着脚踝处开叉的软皮靴迈开大步左右走动,镀金的银马刺碰到地板上咔咔作响。爱玛在想,这个人大概有无穷无尽的爱,才会将那么多的热情洒向观众。她在人物诗意的呼吸下,心里所有的不满都消失了。角色的光辉引导她对演员本人产生了兴趣。她试着想像他的生活,这种让人议论纷纷的不平凡的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的。假如机缘巧合,她也能过上那种生活,他们也许会相识,他们还可能相爱!她可能和他一起游历欧洲所有的王国,从一个京城跑到另一个京城,分担他的疲劳,分享他的荣誉,拾起人们抛给他的鲜花,亲自为他的戏装绣花。然后,晚上,她坐在包厢的金色的栅栏后,屏息聆听这只为她一个歌唱的心灵的倾诉,他边唱边望着她!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想法,以为他正等着她,肯定是这样!她真想跑上去,扑进他怀里,请求他的保护,好像他就是爱情的化身,她要对他说,对他大喊:“带我走吧,带上我远走高飞!我要把我一切都奉献给你!”
幕落下了。煤气灯味和人的气息混合在一起,使人感到窒息。
爱玛想出去,但过道里挤满了人,她感到一阵心悸,倒进她的椅子里。夏尔怕她又晕过去,急忙跑到酒吧去给她买巴旦杏仁茶。
他回来时很费劲,因为他手里端着饮料,每走一步手肘都会被人撞到,他差点把大半杯饮料泼到一个穿短袖衣的卢昂女人肩上。那女人感到冰凉的液体流到腰部,发出一声叫喊,好像被人杀了一刀。她丈夫是个纱厂厂主,见状对这笨拙的家伙大发怒火。就在女人掏出手绢,擦干她那件漂亮的樱桃红连衣裙上的水渍时,男的就在一边气乎乎地嘀咕,说这条裙子值多少多少钱,要赔。夏尔好不容易回到妻子身边,大口喘着气地说:
“说实在的,我还以为我回不来了!那么多人!……挤死!……”
他又加了一句:“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列翁先生!”“列翁?”“正是他!他很快就过来问候你。”刚说完,永镇的原书记员已进了包厢。
他一副绅士派头潇洒地伸出手来,包法利夫人也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无疑折服于一股更加强大的吸引力。自从那个春天的夜晚,濛濛细雨中,他俩在窗边告别后,她再也没有碰到过这只手。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一咬牙把自己从回忆中拉出来,结结巴巴地匆匆说道:
“啊!您好……啊!您也来了?”“安静!”正厅有人在喊,因为第三幕开始了。“哦,您就在卢昂?”
“是的。”“什么时候来卢昂的?”“出去说!出去说!”有人看着他们,他们赶紧住嘴。
但从此时起,她再也不去听台上的唱词了。乐队的演奏,宾客们的合唱,阿斯东和他仆人的那场戏,大段的D 大调二重唱,台上的一切似乎都离她那么遥远,因为她想起在药房老板家的牌局,想起那次去奶妈家,想起葡萄棚下的那几次朗读,火炉边的喁喁长谈,如此谨慎和微妙,却被她抛置在脑后。他为什么回来了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又走进她的生活?他就站在她背后,肩靠着隔板;她不时微微地战栗,因为他鼻孔里呼出的热气息冲进了她的头发。
“您喜欢这个戏吗?”列翁问道,他俯下身子,和她离得那么近,以致小胡子尖都擦到了她的脸颊。
她随便地答道:“哦!我的天,不!不怎么喜欢!”
于是,他提议到剧院外找个地方去喝点冷饮。“啊!现在不行!再看一阵!”包法利说,“她的头发都散开了,看来要出现惨剧。”但爱玛对这场疯狂的戏失去了兴趣,她嫌女演员的表演太过于夸张。“她叫得太大声了。”她转身向正专心聆听的夏尔说。“是的……也许……有一点吧。”他答得吞吐,因为他正看得很投入,可又怕得罪夫人。列翁叹气道:
“这里真热……”“热死人了!真的。”“您感到难受吗?”包利法问道。“是的,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走吧。”
列翁先生体贴地给爱玛披上花边大方巾,他们走到码头边,坐在一家咖啡馆橱窗外的露天。夏尔立即提到爱玛大病一场,爱玛不时想打断他的话,她说,她怕列翁先生听了厌烦。列翁说他这次要在卢昂一家大事务所干两年,以便熟悉这里的业务,因为诺曼底处理这些事务的方式与巴黎迥然不同。然后,他问起贝尔特,郝梅一家和勒弗朗索瓦大娘的情况。由于有夏尔在场,他们就不想再说话了,很快就都安静下来。
剧院里散场了,人们走过人行道的时候不是低声哼哼,就是怪声大叫:“美丽的天使啊,我的吕茜!”于是列翁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谈起了音乐。他听过唐布里尼、吕比尼、佩尔夏尼、格里西等人的演唱,拉加尔蒂虽然很红,但无法和这些有名的歌剧演员相提并论。“可是,”夏尔细细地品着他的朗姆酒冰冻果汁,打断他的话说,“听说最后一幕非常精彩,我觉得不能看到结局总是遗憾的,我刚刚看出点味道!”“没关系,”书记员说,“他不久还会再演一场的。”可夏尔说,他们第二天就得回永镇了。“要不,”他转身对他的妻子说,“你想一个人留下也行,我的宝贝。”这个意外的机会令年轻人惊喜,他立即改变策略,称赞拉加尔蒂在最后一幕中的演技极佳,非同凡响。夏尔听后,执意要妻子留下:
“你星期天再回去吧。行了,你就别想多了!这样有利于你的身心健康。”
这时,四周的人渐渐稀疏了。一个侍者走过来静静地站在他们身边,夏尔明白他的来意,掏出了钱包。书记员拦住他的手,抢先付了钱,还另给了两枚银币,丢在大理石桌面上丁当做响。
“真不好意思,”包法利喃喃说道,“还让您请客……”列翁打了个不必客气的手势,随即拿起帽子表示他的诚意说:“是不是就这样说好了,明晚六点钟?”
夏尔又重复道他不能离开太久,但爱玛不妨……“只是……”爱玛奇怪地微笑,吞吞吐吐地说,“我不太明白……”“你再考虑一下吧,过一夜再做决定……”然后,他对列翁说:“您现在离永镇不远了,希望您常过来吃个便饭?”书记员肯定地说他少不了要打扰他们,何况,他还得去永镇给事务所办事。11点半钟,他们在圣赫尔伯兰巷前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