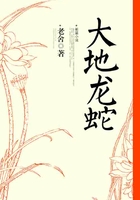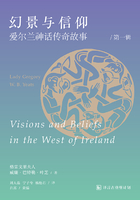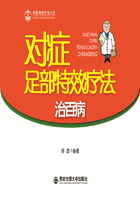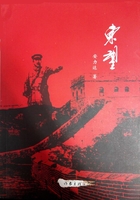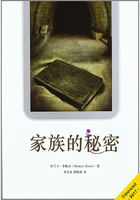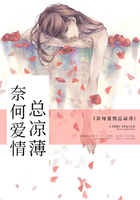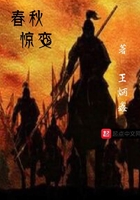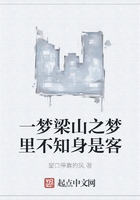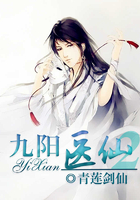这篇文章的名字引自清朝袁大才子枚的一首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诗里描绘的北方私塾简陋如同猪窝,圣贤书中的道理是几个竖童滚在里面扯着脖子喊出来的,这应该是当时乡下常见的情形。
最近市面流行的话题是童年的消失,意思是大人现在变得越来越老成世故,特会装蒜,连儿童都越来越假正经,一些学者瞎着急,郑重其事写了好些书,说这全是现代生活惹的祸。看袁才子诗不由得胡想到,童年消失和装蒜流行大概与我们都不会扯脖子把圣贤话喊出来这事有关,时髦说法叫作失语。
台湾的张倩仪女士写了本好看的小书,就叫《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副题是“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里面传达的都是叹惋怀恋童年消逝的意思。书中引了不少名人童年的回忆,乡村私塾经常被描写成隐在一片竹林或梅树中,透过高亢琅琅的书声,路过的人才知道私塾的方位。名人回忆当然也少不了家塾周围“有山,有水,有亭台,有池榭,有藏书楼”之类的怀旧话,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私塾里用“喊”来教化儿童的那些事。
比如赵元任说起自己念书总是打起腔来念的。读书好像唱歌,念书的调不但一处和另一处不同,念不同的书,调也不一样,四书有四书的调,诗有诗的调,古文有古文的调。赵元任回忆父亲第一次教他念《左传》,回想起来简直就是唱出来的一般,可自己小孩时听个起头哼哼儿的,却被吓哭了。
由此可以想象,各地私塾里飘出的南腔北调,有的喊着“人之初”,有的高喊“天地玄黄”,再加上先生自己打起腔来念书,满屋哇啦哇啦的声音,真是热闹得不行。读书不但要打腔喊叫,还须摇头摆脑地晃动身体,郁达夫比喻得好,像自鸣钟的摆,上身摆到左边,屁股跷到右边,上身摆到右边,屁股跷到左边。蒋梦麟说把书喊到几百遍,先生耳朵灵敏到能听出他到底明白了多少,有点像交响乐指挥擅辨音色的本领。有一次他在楼下读苏子《六国论》,父亲在楼上辨音听意,悄声告诉他母亲,只有这次读对了。可见“喊”出的味道是能被辨别的,绝不是没脑子地瞎叫唤。
张倩仪说,过去给小孩子读的蒙学书都是有韵脚连缀起来的,《三字经》《千字文》清一色的韵语短句,编《千字文》的妙处在一千个字不重复。汉代的《急就篇》已是三、四、七言的韵语,唐代蒙学书《蒙求》更是充满对偶、押韵的短句,儿童可以琅琅上口地记背,由于有强烈的节奏感,带有游戏的意味,似乎不显枯燥。
汉语与西语的拼音字不同,拼音字学完字母,就可以上手认字阅读,边学边认。学汉语先要认清足够多的方块字,没有一定积累根本没法读书。汉字造字规律明显,有很多合体字、形声字,集中识字靠背诵是最快速的方法,透过整齐的韵语朗读,潜移默化地领会古人做人的道理。
古人讲究“诗教”,就与教化儿童课本中出现韵律节奏有关。《诗》在六经中的地位重要,在于它提供一种独特的语感教学法,韵律被有节奏地喊出,易于让儿童接受。据张恨水的回忆,他自小没有好塾师,引不起读古书的兴趣,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地爱上《千家诗》,先生虽无一字讲解,自己竟念得津津有味。凡“诗”都要大声朗诵出来,不仅有助记忆,也有助理解。中国诗也向来偏于抒情短小,易于儿童记忆吸收。唐代以后印刷术发明,文字流播大盛,打破了韵语独尊的局面,但唐以后,面对不识字的人群,韵语高诵仍是“诗教”的主旨之一。宋明的那些“圣人”都是用口语体写作,看《传习录》就知道,贩夫走卒为什么都跑到那些大师门下,如果一点听不懂,还傻乎乎站在那里,岂不是白费工夫?《明儒学案》里记有挑担背柴的劳动人民听王阳明或他的弟子演讲,不知不觉放下担子,听入迷的故事。王大师估计不会像邪教教主那样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或懂什么“肚里传音”的武功秘法,无非是奉行“诗教”的一种,后人记下这些圣贤的传道语言,都是既通俗上口,又韵味十足。“诗教”与“母教”也有渊源,中国母亲读书少,但诗总是读一点,除个别才女以写诗闻名于世外,一般家庭中的母亲多当了儿童“诗教”的蒙师。
清末新政,学塾被废,田间坊里渐渐听不到私塾传出节奏低回的“喊声”,蒙学课本中的短句韵语快速消失,或短暂出现在《地球韵言》《时务三字经》这类新派教材中,偶尔可能会出现萧乾所说的情景,课本换成新式的装帧,可以嗅出油墨香气,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可没过多久,现代学校全部模仿拼音文字国家,死念不喊地教授汉语,儿童普遍染上了“失声”的毛病。
现在已很难估计汉语教学拉丁化的严重后果,五四前后很多人嚷嚷着废汉字,汉字没废成,那韵语喊叫的习惯倒是真给废了。随着岁月流逝,私塾老人渐趋稀缺,那弥漫乡野城镇的喊声很快成为绝响。我曾亲耳听到我的老师,上过私塾的清史名家戴逸先生,用他特有的常州腔吟诵了一段《赤壁赋》,在现今也真算是绝唱了。
废除传统声音对人身心的控制一直是近代革命的一个主题。在“革命者”看来,私塾中荡漾着的琅琅书声,扩散的不仅是一种震颤乡间的声响,还被贬斥为古锈思想的延续和复活,是应该绝杀禁锢的。驯化的逻辑不仅关乎文字,而且涉及声音的禁忌和筛选。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本谈声音变化的精彩著作,叫《大地的钟声》,作者是法国人,声称专门讨论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他给自己的研究对象起了个学名叫“感官文化”。在他看来,敲钟可不是一种简单的声响扩散,而是人们日常身份的一种确认,凭借钟声人们能够各自寻找出自己的位置。每天人们听着钟声作息,宗教靠钟声灌输信仰,乡民享受的是美妙频率的散播和渗透,甚至节律的紧缓能够改造人们从小培养出的听觉习惯。革命党意识到声响控制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后,就开始疯狂抢夺对钟声的垄断,他们觉得那些村民的听觉弱了,信教的敏感度也就弱了。革命是场改造听觉的运动,两拨人常常打架斗殴,传统乡民要钟声延续习惯的敲法,革命党却要把钟声换成鼓点,用革命的正宗声音压倒旧势力。于是抢钟绳、藏钥匙,直到砸钟铸铁造兵器,到处乱哄哄繁忙一片,那蓬勃的干劲无处释放,有点像中国“大跃进”里大炼钢铁般的气势。由钟声节奏凝成的乡村宁静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田间声音的消逝就像场传染病,各种替代品开始覆盖人们的听觉。媒体图像的出现变成了文字的克星,文字须凭借朗读强化印象,加深记忆。图像的介入被配制的声音充满,成为单项灌输,割断了自我主动朗读与文字的亲密关系。
说到图像带给我们的变化,《娱乐至死》的作者勾画出的是另一幅图画,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他讲到,电视上每个镜头出现的平均时间是三点五秒,眼睛根本无法得到休息,大脑来不及思考就移向下一个画面。画面不是展示思考,而是展现瞬间印象。作者最讨厌的就是新闻播音员的口头禅“好……现在”,这句话提示你对上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观看者应该转移注意力到下一个画面。再残忍的谋杀,再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再可怕的地震灾难,都应该在头脑中被迅速切换。因为每段画面拼接出的一段故事,按指定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四十五秒钟,否则电视公司就会遭受亏损。很难想象,图像的丰富带来的却是思想的短路。
在课堂上,教化“声音”也是呈加速度消失的。每当给本科生上课,我总是不止一次被问到:“老师,今儿有电影看吗?”或不断被“今儿有什么好看的画片”的嘟囔声所包围,似乎没有人到课堂来是真想“听”什么的。在这种反复暗示下,你的心情马上会变得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在积极主动地放弃思考带来的乐趣。你如果故作高深地夸夸其谈,在渴望被图像震撼的“儿童”面前就会像一个傻子。我猜想不止一位老师有这种经验,每次上课不带PPT教具,自己就会感到内疚。一旦这种心理变成常态,老师站在PPT播放的画面前就仿佛变成为一位新闻播音员,他扮演的角色犹如影像衔接的剪辑师,他不敢说或无法说他就是影像内涵的权威解释人,因为当他一站上讲台,往往就已经认定自己不过是即将上演的异彩纷呈图像的配角。长此以往,教师的尊严在画面的高速转换中一点点流失,因为画面不需要解释,学生更不需要枯燥的说理。面对经典,学生们不但喊不出来,而且也读不进去。事到如今,“儿童”终于成熟到了跑步进入另一种不假思索的“纯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