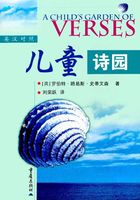我气呼呼地趴在炕头,两只手抠着炕席花,翘起的腿不停地撞,六神无主地睨视她们,但却很仔细地听她俩说话。看到带子为我求情,我心中暗喜,眯缝着眼睛看她窃笑。带子也是个孩子,可比我懂事多了,从不赘脚,守在家里,姥姥很听她话,今天又被她说服了。最后姥姥冲我说:“跟腚虫,你又赢了。”还用手捏着我鼻子头补充一句——“就这一次!”我根本没想以后,只图满足眼前快乐。这何止是能跟着姥姥,还渴望看外面的“西洋景”。当时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一看到外部世界的“热闹”,就都说成是“西洋景”。其实,当时能看到的仅仅是“东”洋土景,而且也只能是坐井观天的“景”。
前几天,一直飘着清雪。灰蒙蒙的天空,玉尘般的雪粒洋洋洒洒落下来,使原来的雪地更晶莹、透明和光亮。这清雪小冰粒,又叫霰。没想到腊七晚上,竟转成鹅毛大雪。片片雪花悠悠缓缓地在空中飞舞,当呼啸的西北风一刮来,雪片如棉絮在空中打转,转到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漩涡。清晨起来,见院子里形成很多雪窝,奇形怪状,美极了。风小了,雪还在下着,今天我们肯定在雪中行了。
北大荒人腊八出行,是毫不含糊的。这次二姨姥家出车和赶车的。车老板的防寒服武装到了牙齿,头顶狐狸皮帽子,还戴着耳包保护着下巴,身穿羊皮大衣,脚蹬牛皮靰鞡,手褪在皮套袖里,连赶车的缰绳和鞭杆都是从套袖中伸出来的。车上铺了很厚的谷草和麦秸,姥姥加上狗皮褥子,上面又加了毛口袋。让我脸朝车尾坐着,用大棉被从头到脚把我包起来,并用布带系牢。我身上本已穿成棉球,这一包,真是“很暖和”,可她说“别看现在暖和”,“风钻进去冻透了”就该冷了。她与媒姑也都穿着皮大衣,戴皮帽子,围巾只能溜溜缝,双手褪在衣袖里。她们是借常外出的男人的光,皮衣又肥又长,能护着双腿。她们分别坐在我两侧,面朝车尾,只有赶车老板必迎北风而坐。
长鞭一甩,车上路了。天空、大地、树木和村庄都披着鹅绒。我们走上一程,车马和人也都成了活动的雪雕。抖下身上的雪,不一会还披上白斗篷。这时才后悔出发时没带个扫帚。车上的大人不停地聊天,我望着无边无际的雪地和飘飘洒洒的雪片,可说是心猿意马。想象野兔和大灰狼突然出现该多有趣,也巴望路旁树上的鸟巢里,乌鸦或喜鹊意外飞出来,发出嘎嘎叫声,哪怕有几只小麻雀在眼前蹦蹦跳跳觅食,也比只听这车轱辘压雪发出的扎扎声好玩。
姥姥不时地摸摸我的手凉热,问身上冷不冷,腿麻不麻,让我在被里轻微活动身子。大人们很少说话了,只有车夫驱使车马行走的驾驭声和鞭声,单调乏味的旅途上,没有遇上车辆和行人。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躺在了姥姥的怀里。她说人在外面睡着了,最容易出冻伤。所以,她把我的棉鞋脱了,用手捂着小脚,不时地摸摸手和耳朵,脸也用被罩上,就这样仍旧担心冻伤。
三十多里雪路,马怕滑,跑不起来,走了小半天,快近晌午时总算到了,雪也停了,天开始放晴。姑娘家早有准备,再说媒人就是这家的姑奶奶,亲人相见,亲上加亲,气氛自然和谐。下车前姥姥唤醒我,男主人把我抱到热炕头上,我睡眼惺忪地看着屋里的陌生人忙里忙外的,却没有年轻的,悄声问姥姥:“要相看的姑娘在哪呀?”她笑了笑对媒姑说:“快让姑娘过来吧,我外孙女都着急了。”那年头也没有照片,凭媒姑说啥样就信啥样,眼见为实。只有主角上场了,才能唱这台戏。
姑娘妈唤女儿过来,媒姑挎着姑娘胳膊走进屋,神情很紧张,虽然面带微笑。姑娘穿得干净利落,确实长得很像姑妈,个子不高不矮,模样不丑,眼睛不大,皮肤不黑,体型不胖,梳着长辫。她向姥姥深深鞠了躬,叫声“姑姑好”。媒姑立刻插嘴,我也是你姑姑,不能这么称呼,要叫“姑婆”,姑娘的脸“唰”一下红了,马上补充说“姑婆好”,根本没理睬我这个小孩伢。可我一直好奇地瞅着她,甚至替她紧张。
接着,姥姥把小红绸包拆开,拿出闪闪发光的银镯子,说这是长庚侄给姑娘买的信物,让姑娘伸出手,她很郑重地给戴到手上。屋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姑娘的手上,鸦雀无声。只有媒姑在一旁对姑娘说:“这镯子戴在你手上,李家就永远把你套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啦!”姑娘的父母和兄嫂也随声附和说:“跑不了啦,拴住了。”
姥姥马上又拿出银耳坠子,面对大伙说:“让我外孙女给舅母戴上吧。”她小声跟我说:“别急,她的耳眼很大。”意思是让我别害怕戴不上。我一点也没有忸怩,大大方方地站到炕沿上,姑娘在地上,高低位置正好,不用扬脸抬胳膊,我把坠子稳稳地捏在大拇指和食指间,姥姥已把坠子的接口拉宽,并告诉我,从耳前往后戴,让接口在耳后,我很轻松地给姥姥戴上了两个耳环。当人们都注意姑娘耳朵时,媒姑又发言了:“戴上耳坠子是福气。过门后耳朵要听婆家人的话”。并指着姥姥说:“这姑婆就是婆家人。还要听丈夫的话,好好过日子。”姑娘笑得很害羞,她的亲人都心满意足地看着。
这个简单的仪式后,姥姥如数家珍般,把各样布匹的数量一一说清。其实按习俗,要用大红纸当面写份礼单的。一是小门小户人家订亲礼薄,二是出于信任就免了这程序。最后相商明年开春办婚事,双方再择个吉日。
媒姑没有和我们一起离开。下午我们去长庚舅舅那。姥姥同侄子说了很久的话,都是跟娶亲有关的。他家屋里特别地冷,火炕也不热,原想第二天早返回,可姥姥担心这一夜会很难过,决定早点吃饭,天黑前上路。临走时,她嘱咐长庚舅,过大年前,要去姑娘家拜年请安。
天上的三星高照,我们就到家了,折腾得人困马乏。用带子的话说,不冻个好歹,也得累出病来。第二天姥姥果然又烧又咳,我倒安然无恙。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姥姥的烧退了,但咳得很厉害。我们正准备躺下睡觉,并到了往常她“上课”的点,她拉我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说:
“跟腚虫呀,以后姥姥出门,特别是出远门,你能不能不跟了?”她把“跟”音说得很重。
我望着她不吱声,但眼睛在替自己揆情度理地发问“为什么”。她看得出,所以接着说,也是回答“疑问”:
“为了你好,也为了姥姥好。”她咳了一通继续说:
“你看这次来回路上,我只顾你,就顾不上自己了,冻病了,你不心疼吗!”因为阵咳,她的话又中断了。
带子立刻插嘴帮腔:
“哪也不如家享福。以后跟我在家玩,别赘脚了!都五岁了,多羞!”
她与带子说的这些,似乎都触痛了我心上的神经,她们的话在我心里,具有无上的权威,我突然开窍似的,当即答应“那行吧”。
从此,真的结束了与她寸步不离的日子。
开始看姥姥不在家,我有点像刚断奶的孩子,寻寻觅觅地无着无落,怕她不在家,更怕她出远门。
带子很高兴我在家,我原本就是她的玩伴,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即便姥姥不在家,我不找也不问。相反,有时却很在意她啥时回来,因为我和带子“密谋”要干的事,掏家雀窝呀,扣麻雀呀等等,常要瞒着她,才觉得神秘有趣和踏实,甚至盼她出门和晚归。
我渐渐地巩固了与带子之间的亲密感情。我俩在家整日忙个不停,各种有趣的玩法毫不间断,那些最简单的淘气的“娱乐”,足以使我们开心。姥姥对我们虽很放任,但我们从不放任自己,幼小的年龄基本是自己管束自己。
注 释
[1].带子是姥姥在十字街上收养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