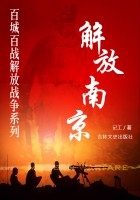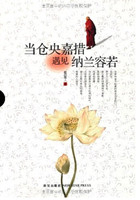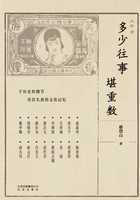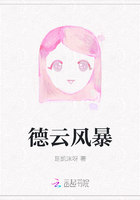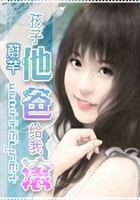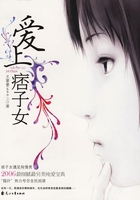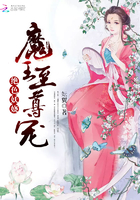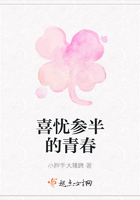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记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罹难史和心灵史。“一九五七”仿佛是一支嵌入回忆的锈迹斑斑的钉子,被尤凤伟硬生生地拉了出来,粘挂着内心的隐痛、耻辱与血迹。还不止于此,这里的潜台词(或者说是整个文本的)似乎是:时光,凝固吧。把苦难砸入意识,拒绝漠视与遗忘……
现代人是善于遗忘的。希望与隐忧总是悬缀在未来的天幕上,让人或欢欣,或黯然。于是,当下被将来所吞噬,一切都义无反顾地朝着虚幻的未来涌入和敞开……而在《中国一九五七》里,所有的事件与人物都在向着过去陷落。对于周文祥、李戍孟等人而言,不存在什么将来,过去永远在延续,它塑造了现在,进而也自然会弥漫至将来。一切不过是以往的余震与回响,历史成了真正的不落的太阳,尽管惨白而严酷,却也点亮、成就了“我”的“帝国”。
这种情感基调决定了小说的笔触必然是徜徉、舒徐的,其叙述带着难以自抑的倾诉欲望。于是,周文祥化身为叙述者“我”,以第一人称的抒情特质从容、油然地融入过去——历史的尘埃在“我”的目击、亲历中起落升沉。过去萦绕着“我”,进而吸附、压迫、撕裂着“我”,“我”与过去打成一片,写“我”即是在追溯历史。而且,“我”的血肉之躯乃至缠绵、苦痛赋予了历史鲜活的个性,在“我”的诗性话语中,“一九五七”那僵硬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
应该讲,以“我”作为掘进历史深层维度的切入方式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它隐含着心灵对历史异化的反抗,《中国一九五七》同样如此。但后者的特殊性在于:“我”这个人物(即周文祥)从一开始就是完成的,“我”所秉具的对苦难的感悟以及对人性的批判意识在灾难降临之时就已完全成型,是天然自足的。小说中存在大量议论式的句子,诸如:
我将冯俐的信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
在去往屠宰场的路上我一边膨胀着对猪的愤恨,一边告诫着自己无所畏惧地将破烂躯壳里的人性改换成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过年宰猪是我的一次“凤凰涅盘”……
“践踏”、“凤凰涅盘”之类反讽式的字眼加重了痛楚的砝码,但不容回避的是:这种意义的丰蕴并非产生于事件发生的“彼时”,而是经历了时光的沉淀,于现时的“回味”与追认,某种意义上讲,是情感的重新定位。当过去成为现在与将来的定影液时,再现过去便成了命中使然般的生活状态。以现时去诠释过去:哪怕当初再荒唐,也遵于理性;去丰满过去:即使以往再荒芜,也有意义存焉;去修饰过去:即便只有一星半点的光彩,也能与日月争辉斗艳。“我”的过去一派黑暗,但黑得有质感;虽然痛楚,但痛得有内容,有理由,够劲,够彻底。甚至连灵魂的自剖与忏悔也变得堂堂正正,凛然不可逼视。
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的语言,而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却巧妙地以反讽达到了英语中现在完成时的效果,即过去的一切都密切地关涉着当下:过去的神只同化、解构着现在,犹如一声悲愤的长啸,贯通、响彻时间的走廊;而历史在今天含情脉脉的追溯与叨念中被强化、增值,进而被活生生地再造、颠覆与背叛……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矗立的“五七”历史十字架,尽管肃穆庄严,其根基却不那么牢靠,有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嫌疑。“我”只是一个虚拟的设置,被尤凤伟作为一发强力子弹,射进了历史坚硬的心脏。
为了揭示“我”的虚拟性,我们不妨回到文本。小说分四部,变换了四个场景:草庙子胡同监狱、清水塘农场、兴湖农场、我乐岭农场,其共有的特征是时空的高度封闭与浓缩。这里没有事件,只有重复的“生活”。时间在逼仄的范围内蠕动:一天、一周、一年,甚至整个的生命。对于犯人而言,一天从来不是一天,一年不是一年,一生不是一生。日子的意义仅在于重复:相同的生活场景、同样的谈话主题、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语言……人仿佛成了一棵树,生命的横断面上徒增着年轮。在这种环境下,以常理推断,哪怕再润泽的心灵也会被榨干,麻痹与枯萎是精神能够存在的唯一状态。这里没有美,甚至连文学的要素也无从寻觅。“生活”一词退回到它最本源的意义:生了,活着。而小说中的“我”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发达的痛感神经,更不用说那百折不挠的理性批判与自剖意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除了用虚拟来解释外,别无他法。于是,客观的历史与文学之间出现了危险的裂隙与断层,说到底,历史拒绝一切表现。
《中国一九五七》中呈现的历史是文学化了的,这里有一个隐秘的置换:即通过“我”这样一个虚拟的设置,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人性史,人性的逻辑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于是,在监狱、农场浑浑噩噩捱时光的囚徒被呈示得立体、丰满,心灵不再是一片空白,而变得九曲回廊,别有洞天。在此,文学化的真正企图是拒绝历史的平庸,不能容忍、姑息心灵的无动于衷,而要把灵魂放置在理性批判的炉火上翻炒、煎熬,炸出或猥琐、或光彩的人性大餐。“我”的抒情、“我”的独语,说穿了不过是文学的发嗲。通过有血有肉的“我”,文学向历史频送秋波。表面看来,文学已将历史拥入怀中,难分难解,事实上一切只是在做戏,是小说的骚动而已。最终还是要各就各位:文学,历史,不搭界的。
除了上述常理的推断,“我”的虚拟特质亦可从书中后记里得到印证。作者说他采访过一个有右派经历的大学教授,建议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却摇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永远难以复原,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这与小说中的李戍孟,一个在狱中、农场不懈书写的奇特人物的表白不谋而合。后者曾说:“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由此可见,作为老右派周文祥的“我”也应该是不具备超然的理性的。“我”之所以能够担当起叙述者的重负,之所以能够冷静地观察、批判乃至自我剖析,是因为作者给“我”灌注了“高贵与骄傲”的底气。前文所讲的“我”一出场就是一个完成了的人物便是这种底气使然。
这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叙述者“我”与作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作者显然不相信“我”能单枪匹马地揭示历史,完成故事,认为没有他的精神指导与支撑,“我”将陷入历史的泥淖而无所作为;同时,他又不能把“我”统得太紧,某些时候还要放纵一下“我”的本性,借助于“我”的懵懂与纯真来充当叙述的伪装和故事的润滑剂,以达到一种自然的虚拟,虚拟的自然。但总的来说,作者是“我”的灵魂,他超越了“我”,升华了“我”,我们比双子星座、连体婴儿还要亲密无间、相濡以沫,“我”爱他、崇拜他,哪怕陷入自相矛盾、人格分裂也在所不惜,“我”愿意做他的俘虏与傀儡。
于是,“我”的身上便具有了巴赫金所讲的“镜中人”的特质:“在自己与自己的相互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透露出虚伪和谎言……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这里没有内在和外在相结合的那种幼稚的完整性……我没有从外部看自己的视点,我没有办法接近自己内心的形象,是他人的眼睛透过我的眼睛来观察。”这“他人的眼睛”具体到《中国一九五七》中便是作者。这是“我”放逐、舍弃本性后的必然代价,“我”以人格的分裂乃至灵魂的阙如换来了外在(即文本中)的超然与独立。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愈是振振有词,痛定思痛,历史愈是变得颤动不定、模棱两可。纵观整部小说,除了“我”,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种沉溺性,仿佛是被叙述者“我”硬生生地从黑暗中拽出来的。“我”就像是一只冒失的刺猬,支棱着锐利的理性之刺,且注定要撞上某个人,于是崔老、吴启都等人先后出现了。他们的话语虽然内容各异,但大都由“我”“招惹”而起,带着同样的知识分子腔。而且,不管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都不加引号。这在形式上造成了一种“浮现”感,即所有的对话都是应“我”的召唤而来的,犹如空穴来风,带着缥缈的回音。根据巴赫金的理论,不加引号的话语较之打在引号里的话语(即令人感到并用作他人的话语),在他性的程度上(或被掌握的程度上)微妙地加强了。由此,叙述者“我”拉开了与他人的距离,从而为理性的审视与逼近提供了从容的空间。
这种人物之间的牵制与关联如果用一个形象化的图形来表示,似乎是一个封闭的圆,“我”成了圆心。所有的人物都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在“我”的视野星空上闪现、起落、浮沉。是“我”照亮了他们的存在,“我”以“我”的倾诉,“我”的洞察、理性乃至逻辑的力量构筑了“我”的世界。
然而,这个“圆”只是文本呈现的表面状态,因为圆的存在依赖于圆心,即“我”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但事实上,“我”的超然也是装出来的。在“我”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本能驱使着“我”与他人一道沉沦,一起浑浑噩噩、没心没肺,但“我”最终是被作者操纵着,强打精神。很多时候,“我”滔滔不绝,却言不由衷,“我”被作者拎着,成了暗盒里的提琴。
这样一来,人物间的关系构图发生了质变,出现了两个圆心,两个焦点!圆被挤压成了椭圆。所谓椭圆,是指当平面上的动点P(他人)到两定点F1(叙述者“我”)、F2(作者)的距离和为常数时,点P的轨迹称为椭圆,F1、F2称为焦点。
“我”和作者共同去发掘、点亮他人,其结果是“我”的独语变成了两种声音和意识的盘旋、交错与缠绕。当“我”与他人的距离靠近,即“我”本来的声音加强时,作者的声音便弱了,反之亦然。“我”代表一种内在的视角,其趋向是亲和的沉沦,即在描述的同时,融化进背景,进而在一种略嫌残酷的抒情中消解自我;而作者则是一种外在的理性的力量,代表了观照一切、统摄一切的诉求。这种双焦点的对峙使得“我”永远不能恢复自己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永远不能和他人打成一片,即便是他人走到了离“我”(F1)最近的地方(近焦处),也时时能感受到作者(F2)那强大的不在场的注视。
于是,“我”不再是“我”了。“我”和作者共同虚拟、塑造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如果我们把《中国一九五七》当作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来读倒也罢了,但若想通过它来窥得历史的真面目,并获取某种深远悠长的意义就未免可笑了,至少作者的责任感和愿望是落空的。他理性与道义的针线并没有将历史与文学缝为一体,而是捉襟见肘,内里现出了破绽。说到底,以文学的方式去复现、描述历史,单单凭借了理性是远远不够的。福克纳之所以在《喧哗与骚动》中把朝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户定位在一个白痴的意识上,便是隐含着对理性深深的怀疑与忧惧。在福克纳看来,理性的分析是对故事的横加干涉,它会破坏小说独立自主的理想,而暴露出它依附于某人、某物的局限和对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偶发性和派生性的依恋。事实上,理性的洞察、推理连同道义的评判除了提供一个现成、省心的视角、立场外,别无其他,而且弄不好,极易沦为繁衍虚拟的一面之词,表现在文本上便是自说自话,自我感动与陶醉。在《中国一九五七》里,强大的理性贯穿始终,“我”只是作为一个虚拟的设置,在理性的支配下游走奔波。结果,小说在精致的自圆其说中背离了历史的轨迹。理性不但没有引领我们走近历史,反而成了误导与障碍。历史在理性的呈现中,在经过温情的道义重新抚摸、装点后,丧失了它原本冷酷、粗糙但却是丰蕴、自在的内涵。
这种缺陷在小说的构思之初便注定了它的存在。前文说过,“在《中国一九五七》里,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都在向着过去陷落”,结果,历史成了存放所谓深刻与意外的储藏室,而当下沦落为过去的注脚。一切都可以在现时的“回味”中翻倒重来,在“反思”中变平庸为不俗,化腐朽为神奇。这种重塑历史的愿望(暗含着为当事人讨个说法的动机)使得虚拟成了孤注一掷的逻辑冒险、文学游戏。在我看来,如果将过去和现在并列为两个独立的时空,以容纳叙述者“我”不同的话语和思考,效果会好得多。即:在追溯历史时,尽量使用客观的笔调,以凸现当时的一潭死水状。与之相应,彼时的“我”是心灰意冷、麻木不仁的;而在描述现在时,“我”清醒了,浑浑噩噩的历史成了“我”进入当下的严重的心理障碍。“我”在历史与现实的漩涡中徘徊、挣扎,往日的一派死寂、一鳞半爪回想起来是那么触目惊心,以至于对于记忆本身“我”都开始怀疑。于是,过去的历史与当下记忆中的历史相互碰撞、挤压、排斥,再穿插配以今天的物是人非,小说叙述的弹性与张力会大大地增强,使得主题的表达更具力度。而且,叙述者“我”在人格上也会趋于独立,变得自然、真实、可信,而不仅仅是虚拟的设置,理性的棋子。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一首名为《1979年3月》的诗中写道:“厌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我走向白雪覆盖的岛屿/荒野没有词/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我触到雪地里鹿蹄的痕迹/是语言而不是词”。托马斯在此幽深、细致地表达了一种对于历史的敬畏感,伴之而来的是难以回归与追溯的痛楚。如果将诗名改为《中国一九五七》,两个“一九五七”境界的高下便不言而喻了。对于历史,我们缺少的不是煞有介事的理性,而恰恰是被理性遮蔽了很久的、藏匿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敬畏之情。它其实一直在那儿,只是我们浑然不觉罢了。敬畏使我们感觉难以言说,却又不得不去表达,于是,在小心翼翼的陈说中,我们的语言变得更为纯粹,更加接近它的本源。也只有敬畏,才能消除理性的偏执,才能弥合文学与历史的鸿沟,使得文学的书写与虚拟即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