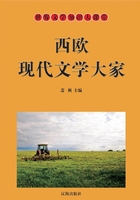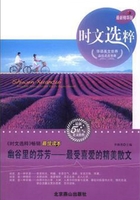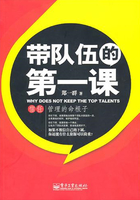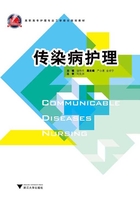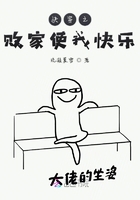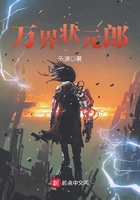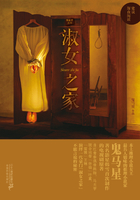1.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
引言:我与“三剑客”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黄钟大吕的音响报道了新军旅文学最早的潮汛,同时也昭告着一代军旅文学新人的迅速崛起。旋即,这批年轻的军旅文学弄潮儿和老一辈军旅作家一起开始向新时期文学大潮集团“冲浪”。一时间,军旅文学大纛下战将如云,捷报频飞。
整整十年过去了。
而今,军旅文坛虽然并未偃旗息鼓,但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闹猛;它和整个新时期文学一样,都渐由凌厉浮躁转向了沉静平和。当初那支大呼猛进的文学新军也由一个大致整齐的“方阵”而拉成了一条“散兵线”。就像马拉松长跑进入了艰苦相持的中程阶段,少数真正具有潜力和素质的顶尖选手脱颖而出,成了一马当先的佼佼者。而在这中间,莫言、周涛、朱苏进无疑是最为人瞩目的三位翘楚。
我称莫言、周涛、朱苏进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均速行进,占据了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而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而去而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住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总之,各有各的绝招,却都以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创作实绩先后跃上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巅峰,并且毫无愧色地步人了当代中国优秀作家的行列,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他们三人的创作又非常巧合地涵盖了几种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和诗歌。或者再扩大一点视界,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三人也各有其典型性:莫言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新浪漫主义者;朱苏进则是新型军官阶层理想的代言人;而周涛呢,他可说是马背民族与汉民族双重文化背景熏陶出来的歌手。因此,选定他们三位进行一番平行展开式的比较研究,做一点传记和心理批评,探讨一下他们的创作道路、个性及风格,客观公允地评价其过去,心平气和地分析其现状,实事求是地指出各自的优长和局限,其意义恐怕就不拘囿于“三剑客”本身或者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乃至一般军旅文学运动的范畴了。
当然,我之所以比较自信地敢来评说他们三位,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即作为朋友,我对他们都比较熟悉——我和朱苏进同为原福州军区的炮兵,相识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莫言成名前后,我们同窗两年,也可算得是朝夕相处了;与周涛见面最晚(1986年),却也是气味相投,一拍即合,倾盖如故,相见恨迟——“熟知”就带来了解和关注,睹其文思其人,见其人想其文,互为观照和印证,就有可能做到像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譬如,据我观察,这三位的个性都是卓尔不群而又迥然有异,周涛是直率狂放,朱苏进是孤傲矜持,莫言则奇诡莫测……
举一个小例子。
约五年前,当我最初认定“三剑客”时,有一次亲口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涛。他听完之后,立马眼放精光,郑重地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尖上方一点一顿地说——“我非常赞成你这个看法!”当即令我心中大呼:“除了周涛,谁能这样?若不这样,又怎是周涛?”
我没有就“三剑客”问题和莫言、朱苏进交换过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推测一下他们的“即兴反应”——
莫言可能会撇一撇嘴,撇下两个字:“狗屎!”
朱苏进则有两种可能,或者矜持地笑而不语,或者舌尖轻轻一弹,吐出一个反问:“是吗?”
——是吗?信不信由你。
但是,你却尽可以据此回忆一下你所认识的“三剑客”其人,或者你所曾读过的“三剑客”其文和那字里行间蹿动着的那一股子“精气神”。
现在我想的是,面对这样的“三剑客”,我们的讨论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件既富于意义而又不乏情趣的事情呢?
试试看吧。
“三剑客”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朱苏进: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
朱苏进是幸运的。他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时年二十岁),与年长他七岁的周涛同时,比小他两岁的莫言早了十年。而他二十四岁便当上了专业作家这一点,即便是在全军范围内也无人可比。虽然差不多过了十年他才写出真正让文坛认可的成名作《射天狼》,但他前此阶段几乎全部的练笔之作都得以顺利发表(其中还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长篇《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无疑是激发他创作热情的助燃剂,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他的文学自信心,而且客观上把他推向了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的最佳起跑线。
1982年,《射天狼》的发表和在当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中得奖的意义是双重的。对朱苏进个人来说,这是一部转捩之作,它一方面挣脱了以往深重的政治文学的阴影,显得清峻而脱俗;另一方面开始显露了作家的个性,显示出一种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审美风范。而对新时期之初的整个军旅文学运动来说,这也是一部扛鼎之作,它不仅和《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鼎足而立,使军旅文学蔚成气候,更具意义的是,它无意中以独到的题材选择开辟了一条反映当代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重要战线,与由《西线轶事》和《花环》开辟的当代战争(南线)的另一重要战线成犄角之势,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的最初格局。因为《射天狼》,朱苏进和李存葆成为此一阶段青年军旅作家群中的双璧。
朱苏进没有辜负军旅生活和军旅文学对他的厚爱与滋养。他和梦绕魂牵于北中国那片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的莫言不一样,他和纵马啸吟于大西北长天阔地中的周涛也不一样,他将展示自己全部才情的舞台牢牢限定在脚下这方绿色的军营之中,他决心就在这里打一口“深井”。狭义地讲,他是最“正宗”的一位军旅文学作家。继《射天狼》之后,他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速度连续推出中篇小说《引而不发》(1983年)、《凝眸》(1984年)、《战后就结婚》(1986年)、《第三只眼》(1986年)、《欲飞》(1987年)、《绝望中诞生》(1989年)、《金色叶片》(1990年)和长篇《炮群》(1991年)。作品数量虽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但这恰恰说明了朱苏进创作态度的严肃和审慎。他作品的少而精向来就有很好的口碑,在军中被视为这一方面的楷模,常与张承志、阿城等少数几位极为严谨的作家一道被人谈论。80年代中,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几乎是一篇一个水准,一部一个台阶,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征兆和十分显见的幅度不断地迈向更加雄阔和深邃的艺术大境界(《炮群》开笔于1989年,完成于1990年,亦可视为其80年代创作的一个总结。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发生了一些比较新鲜而复杂的变化,这一点我留待最后来谈)。而且,朱苏进的“迈进”主要不表现在形式结构的探索或技术操作的更新等方面,即便在小说文体革命最具轰动效应的80年代中期,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孜孜矻矻于当代军人内涵的表现与挖掘;从最初提出当代和平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一系列军人的职业矛盾,到经由这样的层面突进和逼近人的本体、人性的内核以及人的根本的生存困境等哲学思考,最终又超越了军人职业,超越了社会政治、文化的一般价值判断,从而不断走向开阔和永恒。就此而言,朱苏进实在是军队作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思想者。在关于和平时期职业军人命题的形而上思考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因此,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或者说都给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供不少军中写手去吞噬、去消化。而要突破这个标高,又往往只能期待他本人来完成了。
与朱苏进在“形而上”(提炼思想)方面达到的高度成正比的是,他在“形而下”(还原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深度完全与之相当。也就是说,以他天生的军人气质、血缘,对军人职业的酷爱和七年扎扎实实的连队炮兵的生命体验,他可以毫不做作毫不费力地写出枪炮的脉搏和呼吸,他的笔尖自然流淌出来的就是军人的劲道、气韵和风骨。而要把这一切做得同样漂亮,舍朱苏进其谁?“形而下”的深度升华支撑了“形而上”的高度,而“形而上”的高度又反过来照亮和推进了“形而下”的深度,二者在两个方向上拉开的距离越大,由此形成的艺术场所产生的张力就越强。朱苏进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极富磁性的艺术场之中央,在当代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绿色王国里做着“金鸡独唱”式的小说操练表演。
说他“金鸡独唱”也并不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别的声音,而是说由于他的声音特别高亢、嘹亮、尖锐而富于穿透力;也并不是没有人想仿效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实在是太难以仿效了。在军旅文坛上,从来关于朱苏进的议论、讨论和争论难道还少吗?大家对他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又有几人能得其精髓甚至得其皮毛呢?名家都是善于仿效的,但名家并不都是适合被仿效的。朱苏进就难以被仿效(相比较而言,莫言倒是一个更易于被仿效的对象)。朱苏进难以被仿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深刻(关于他“深刻”的成因,我将在下一节展开分析)。他对中国当代和平时期职业军人的体验、把握与理想传达的深度,甚至都影响了他的作品被接受和认可的广度。也就是说那些缺乏军旅生活磨炼的非军人和不抱职业军人理想的普通军人,要完全进入朱苏进的世界必须是有一个过程的。现实地看,朱苏进笔下的军人世界也许是太超前了,太过于个人化和理想化了;但是审美地看,它又是极其典型化和风格化的。朱苏进的军旅文学世界创造是一位“缓释胶囊”,它的药性和力量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久地渐渐地释放出来。
周涛:神山中放飞的稀世之鸟
《稀世之鸟》是周涛1990年出版、1992年获全国性奖的那部散文集的书名,但用它来比喻周涛的整个散文创作却更为恰切——周涛的散文就是一只翱翔并雄视当今中国散文世界的珍奇的大鸟。这只鸟既来自西部边陲那些银光闪烁充满神性和神喻的“神山”,也来自以《种山》为代表的周涛的全部诗歌创造。“稀世之鸟”是站在“神山”的峰巅上起飞的,它因了“神山”的托举和映衬才飞得如此高远,也显得更加“稀世”。
今天我们来谈周涛,当然主要应该谈周涛的散文,但是谈周涛的散文又不能不先谈周涛的诗歌,而且这样来谈丝毫不舍有轻视周涛诗歌的意味。相反,我高度评价周涛对“新边塞诗”尤其是对新军旅诗的重要贡献。《神山》获1984年全国优秀诗集奖,既为新军旅诗在新时期诗歌格局中争得了一席位置,同时也奠定了周涛作为继李瑛之后对青年军旅诗人产生广泛影响的承前启后的醒豁地位。但是,即便我们如此充分地估计诗人周涛的意义,顶多也还只能说他是西北重镇或军旅干城,而放置于整个新诗潮运动中加以考察,他显然还难以进入最具影响力的个位数行列,只能跻身于二位数的队伍。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他精神上的超然与飘逸使他不大善于敏感、深刻而强烈地反映出某种时代情绪。通观他的诗作,几乎没有一首能像北岛(如《墓志铭》)、江河(如《纪念碑》)、舒婷(如《致橡树》)、杨炼(如《诺日朗》)甚至包括杨牧(如《我是青年》)们的一些名篇那样激荡出浩大的反响和共鸣而成为众口相传的代表作。二是他骨子里的散漫与闲适使他疏懒于诗歌形式的创新,或者说比较缺乏形式创造的激情,以至于在这方面表现中平,既不如同时的顾城、杨炼等人,更不如稍后的后新诗潮先锋们,甚至也不会像比他年长的昌耀那样能将现代诗艺与古典诗风熔于一炉而自成一格。而以上两点要求又恰是新诗潮运动得以腾飞的双翼,同时也反映了诗歌本质精神的或一侧面——前者凸出了诗歌内容的现实精神,后者则强调了诗歌艺术的先锋精神。周涛在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地成为启发和驱动他此后旋即转向散文创作的潜在因素和反动力。
还有,到了80年代中期,周涛诗歌艺术的生长与发展已经遇到了一种显在的来自自身的挑战。譬如,他的擅长哲思且精于将这种哲思提炼成格言式的警句并以此来统摄照亮全篇的思路开始成为一种模式。如何打破既定模式开创新局面?或者说如何将那些哲思警句化解成一串意象、一片意境,使之景境交溶、情理互渗,在具象中自然升腾起抽象,让人只觉其美而不觉其理,受其警示而不见警句,从而进入那种羚羊挂角不落言荃的大美境界?诸如此类的问题像悄然蔓延的青藤爬满周涛的大脑,交织成一个网络,纠缠出一片困惑,使周涛对自己诗艺的前景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几许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