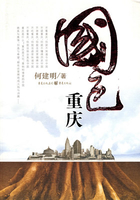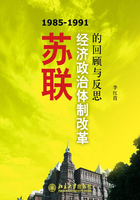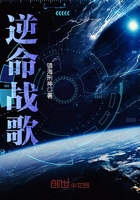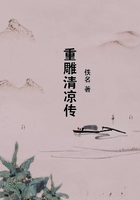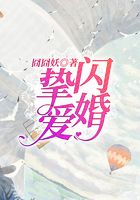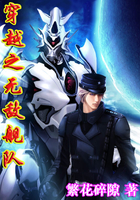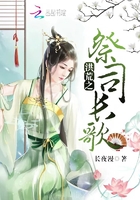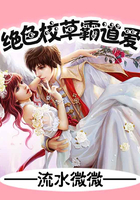1.关于鲁迅的“多疑而易怒”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于艺术形式规范的不同,同样一个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的想像中会有不同的样子。例如,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诗人白居易看来是永恒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的是强烈的爱情不受空间限制,不管上天下地,都不会发生变化;“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是真挚的爱情不受时间限制。这和苏格兰诗人彭斯在《一朵鲜红的玫瑰》中说的爱到“沙子石头都熔化,海都枯干了”,是一样的意思。我在那篇文章里强调的是在诗人看来,情人所说的话都是真诚的,故“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其语义的表层和深层是一致的,这种表层与深层语义的统一,是诗的概括性(对人的热情的概括)决定的,与诗的形式规范是一种对位,所以是动人的。但是在小说里就不同,如果作家让他的人物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心口没有误差,就不但没有性格,而且连场面都很沉闷了。
现代小说家强调对话和潜对话,演员强调台词和潜台词,人物的口头语言和其内心动机都要有错位才能动人。因此,鲁迅当年一度想创作李隆基、杨贵妃的长篇故事时,就认为:
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暧昧)关系?所议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这是鲁迅亲口对郁达夫说的,郁达夫记录在《历史小说论》中。
在我看来是小说形式规范,尤其是小说对话的艺术法则推动着鲁迅作出对人物这样的理解。
近日读王晓明教授在上海和台湾先后出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其第九章中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王晓明认为这是因为生活逼得鲁迅先生“多疑而易怒”,对李、杨之事,他也是如此。鲁迅在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曾说:“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王晓明这样评论鲁迅的这一论断:
对人心阴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厉害了。我以前读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这种特别“毒”的眼光,有时候甚至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练出这样的本事。可我现在觉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这副特别的眼力正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表明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王晓明认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望和五四运动的分化。“他对现实的改革越来越不抱希望”,对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有“戒心”。与周作人反目,又使他“不会再轻信骨肉之亲”。“他甚至将母爱视为一种累赘”,因为这种爱给了他一个既没有情感,又没有肉体关系的妻子(朱安女士)。“在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这正是《野草》写作时期,这一章就叫做“从观到虚无”。
王晓明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才三十几岁。我不由得惊叹,他从哪里练出这种老辣的文章和无情的洞察力!
但我又不得不有所保留,他至少不太全面,忽略了鲁迅在思想批判和启蒙方面的伟大业绩;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王晓明忽略了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的特殊艺术眼光。如果他像诗人白居易那样去理解长生殿夜间密语,作为小说家,那不是太天真、太浅薄了吗?如果我们以为他这样看太阴冷,太多疑,不信任何人,那么在《阿Q正传》中不是更阴冷吗?都绑赴刑场了,还是那么麻木,还要出风头喊什么“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这不是更绝望了吗?但是决定阿Q这样想,这样感觉,这样喊叫的,不完全取决于现实生活,也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思想,还取决于喜剧性的形式感。
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结局(把枪毙叫做“大团圆”)有一个不可须臾忘却的原则,那就是以悲为喜,用荒谬绝伦的特殊逻辑把人物推向可笑的极点。
如果不让阿Q可笑,非得像祥林嫂那样不胜悲戚,孤独地死去不可,不是在艺术上自我禁锢吗?至于李隆基与杨贵妃的关系,在白居易的抒情诗中,情感是永恒的。归根到底;艺术之美不同于哲学之真的地方就在于不仅仅是主客观的直线对称关系,而是主客观和形式的三角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处理是有难度的,就是大艺术家一不小心也难免有败笔。
2.诗人眼光和小说家眼光的交织
我想,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研究不但在他为文的当年是相当深刻的,他的眼光和见地即使在今天也使年轻的研究生们惊叹。但是今天我之所以重读《历史小说论》,并非为了他的论点,而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一条很值得重视的材料。他说:
朋友的L先生(指鲁迅)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
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
这条材料所说的事实,在冯雪峰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提到过,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有过类似的意思,大意是:1924年因为想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一到西安去了一次。可见,鲁迅这个念头动了很久,创作的冲动很强烈,很可惜。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而且连带着这条重要的思想材料也被研究者们忽略了。
从这条材料看来,鲁迅对于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恋爱关系的看法和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大相径庭。粗粗看来,这仅仅是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所致,但仔细研究其间的差别,则不然。在白居易看来那最富诗意的是生生死死、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永恒不变的爱情;可是在鲁迅的眼中恰恰是爱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已经死亡了,而且在关键时刻被出卖了的表现。至于后来的天上人间的寻觅,只不过是神经病和催眠术(骗术)而已。很显然,在诗人白居易眼光中,以情感的永恒来强调诗意的地方,在鲁迅看来恰恰是情感走向反面、绝对杀风景、毫无诗意可言的地方。
白居易和鲁迅对同一题材的不同理解,恰恰是诗意和反诗意的、追求诗意和逃避诗意的矛盾,在诗人看来感情的永恒,是令人震惊的,叫人感动的;可是在小说家看来,一见钟情,心心相印,不但毫无性格可言,就是连情节也无从发展。如果两个人不闹别扭,不发生摩擦,则永远是心灵的表层现象,两人的性格恰恰是潜藏在深层之中。
形式主义者斯克洛夫斯基分析了一系列小说之后,提出一个爱情小说的模式:当A爱上B时,B觉得她并不爱A;在A经过努力,使B终于感到她已经爱A时,A却觉得不爱B了。这不是心心相印,而是心心相错,不但可在成熟的古典小说中,而且可在现代、当代的小说中得到广泛的印证。它不但可以解释安娜.卡列尼娜与伏伦斯基的关系,而且可以解释美国的小说《飘》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说起来有点奇怪,那些写得越好的爱情小说,男女主人公往往越是陷于互相折磨的恶性循环之中。相反,如果男女主人公一点矛盾也没有,没有心口误差,没有动摇和变态,小说就没有什么看头了。然而在诗中,特别是在古典诗歌中,情形则恰恰相反,所以在诗人白居易看来,唐玄宗在“七月七日长生殿”讲的话是心口如一的:这一辈子爱不够,下一辈子再爱。可是在小说家看来,这只是情感的表层(如容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其深层的意思则是:宣布今生甚至永远爱情的死亡。在汉堡,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一个已经加入了德国籍的朋友听。他认为鲁迅比白居易深刻,白居易骗人,但骗得人很舒服,鲁迅不骗人,可人觉得不舒服。他年轻的儿子却说今天在西方已经没爱情,因为谁也保不定谁在什么时候会变,所以德国青年不想结婚的越来越多。他们就是怕固定的婚姻把情感变幻的自由束缚了。当然在德国仍然有人在结婚,这说明,他们仍然相信情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些不愿结婚的是属于小说家类型的,而愿意结婚的则是属于诗人类型的。据说在德国二者各占其半。
就我而言,我倾向于小说家的眼光。如果感情真是永恒不变的,那又何必要结婚呢?结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契约;契约就是用法律的强制来束缚感情的,在非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放任情感的变化,一旦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同时要准备付出代价。
3.关于鲁迅内心的“绝望”和“虚无”
长期以来,我对大陆的鲁迅研究有偏见,这大概源出于我病态的自尊,总觉得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明星还是圣人,代价太过昂贵。同时,又有点扭曲的自卑,极不愿以研究巨人而抬高自己。再说,论材料,连日记和书信都早已公开发表了;论观念,虽然五花八门,但都逃不了对他的赞美和崇敬。
我自然十分崇敬鲁迅,大家一窝蜂地赞美他,已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合唱,我就觉得少我一个也无妨。最近听说有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写的,还列入有关部门推荐给“希望工程”的中小学生阅读的100本书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关于鲁迅的传记,已经见过好几本,不乏和鲁迅同时代的当事人或晚于鲁迅的前辈参加编写的权威本,为何都不能人选,偏选中这个在鲁迅死了差不多20年才出世的年轻人的作品?
一看那序言就有点震动:他立意“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鲁迅的形象向来是与耀眼的光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王晓明却暂时撇开人所共知的外部的光华,去细致地解剖他内心的“痛苦”。这不是一部我们习惯了的社会学的传记,而是一部充分个人化的精神的“苦难的历程”。王晓明在《阿Q正传》中看到的是“痛苦”、“居高临下的批判”和“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而鲁迅自己的呐喊,如一箭射人大海,不能激起浪花的“悲哀”。在“他对历代专制统治的轻蔑背后”,有的是“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而在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魏连殳、吕纬甫一类颓唐者的批判中渗透着“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在他“斗士”的姿态中有隐藏得很深的“文人习气”。在王晓明看来,鲁迅一生始终没有摆脱过对未来的怀疑,对希望的“绝望”,乃至“虚无”。甚至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运动能起多大作用仍持悲观的估计。他在1920年给朋友的信中说:“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本不是什么秘密,明明白白地写在《呐喊》的《自序》之中。他和金心异(钱玄同)的争论,集中于希望的有无,他本以为醒了,“铁屋子”不一定会打破,徒然增加醒者的痛苦。而金心异则以为,既然有人醒了,就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最后他妥协了,对于希望之有无,他内心保留着,而在行动上,他则遵奉先驱者的将令呐喊。“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所以王晓明写五四时期的鲁迅这一章的标题就是《戴着面具的呐喊》。
王晓明虽身为新派评论家却不像另一个“晓明”(陈晓明)那么锋芒毕露。他作心理的微观分析,许多为僵化的流行观念所掩盖的奥秘为他犀利的目光所洞察。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历史的文化心理的还原方法,与我常用的审美感知和价值的还原方法有一点不同。正因为这样,他对历史人物深层潜在心理的洞察,往往令我有发现的喜悦。这部著作无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有关鲁迅的学术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虽然书出版在1993年底,但至今仍未引起争议,这颇令我纳闷。也许自《废都》出版以后,我国学术研究的宽容度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些把不同学术观念的争论上升为政治批判的做法已经没有市场了。
我倒是认为王晓明的著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首先,他对鲁迅的思想艺术成就的分析就不很充分。他过分着重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把那《野草》式的“怀疑”、“绝望”、“虚无”充分加以强调,我们固然不可否认其确凿性,但是这并非鲁迅的全部。
其次,他的价值取向似也有偏颇之处。他在序中强调:写下所理解的鲁迅的一生,“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这就有点“我的批评就是(表现)我”的味道。
王晓明对于鲁迅当年的“绝望”和“怀疑”以为是出于“愤激”,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一种对不能实现的崇高的人生追求和对现实、未来的超前性的焦虑。
听说此书台湾已出版,日后如能弄到,比较其中的异同,一定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