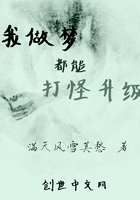唐敬宗于治国无丝毫建树,却是不折不扣的玩乐天才。敬宗马球技艺精湛,又喜爱观赏摔跤、拔河、龙舟竞渡等游戏,宫中宦官、宫女皆其玩具。但他毕竟少年无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愈加恣意狂妄,动辄就将宫人流配、籍没,许多宦官只因小错,轻则辱骂,重则捶挞,人人满怀畏惧、心中怨愤。宦官许遂振、李少端、鱼弘志等还因为与敬宗“打夜狐”配合不佳而被削职。敬宗这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末路。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日,唐敬宗生平最后一次去“打夜狐”。深夜回宫后,敬宗仍不尽兴,又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饮到痛快处,敬宗入室更衣。此时,大殿上灯烛忽然熄灭,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一拥而上,将敬宗勒死。两日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又指挥神策军入宫,杀死刘克明和他欲拥立的绛王李悟,立穆宗次子江王李昂为帝,改年号为大和,是为唐文宗。
享年十八岁的唐敬宗得了个不甚体面的“睿武昭愍”谥号,被草草埋入了庄陵中。后世的史官们评价道,“穆宗生性骄诞,敬宗肖之,固其宜也”。宝历短短两年,国统几绝,之所以尚未亡国,幸赖裴度复为宰辅,大唐国祚才得苟延。区区昏童,误国误己,若非得据君位,何值史书一笔?
唐文宗在宫廷刀光剑影中被宦官扶上帝位,时时事事皆不离宦官掌控;朝中虽有裴度苦力支撑,却不及李宗闵之辈勾结宦官,熏天权势之下,裴度亦无可奈何。白居易回洛阳不久后,被征为秘书监而去长安,刘禹锡在洛阳困居半年,得一主客郎中分司东都的闲职,百无聊赖的生活便在亲朋唱和与迎来送往之中继续蹉跎,这与他在二十三年沉沦生涯中日夜期盼的归乡生活有天壤之别。刘禹锡曾有《罢郡归洛阳闲居》之诗,将赋闲中的苦闷与自励尽抒其中: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归心。及此西还日,空成东武吟。
花间数盏酒,月下一张琴。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
——《罢郡归洛阳闲居》
大和元年(827)七月某日,刘禹锡府上忽有客人到访。来人不通报姓名,只让刘禹锡亲自来迎便知。刘禹锡心生疑惑,果然亲至府门。一见来人面目,刘禹锡登时惊喜,继而嚎啕不止。来者亦不堪悲情,二人抱头痛哭。
能令刘禹锡大喜大悲交相碰撞者,天下唯韩泰一人。文宗登基后,韩泰方从漳州征还长安,新授湖州刺史。闻刘禹锡在洛阳,韩泰上任途中特来探望。大和元年时,永贞革新后同获罪的八司马中,已仅剩刘禹锡与韩泰二人。自柳宗元去世后,韩泰便是最与刘禹锡志同道合而又能同病相怜之人。
刘禹锡呼唤仆人置酒摆宴,与韩泰携手进府。刹那之间,刘禹锡忽然感觉回到了永贞元年那段青春飞扬的岁月。那时,革新集团群英荟萃,上朝退朝群集影从,时人瞩目,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可是再看现实,昔日同行相伴之人,仅剩沧桑憔悴的韩泰而已。两人对面长叹,泪比话多,丰盛的酒菜几乎成为祭奠那段峥嵘岁月的贡品。自元和十年(815)在长安匆匆见过一面后,两人又是十数年未见,其间虽隔千山万水,而升沉之势相近。此次韩泰短暂回京,旋又出为湖州刺史,仍旧不得重归郎署,反倒羡慕刘禹锡能在家乡赋闲。
两人彻夜长谈,只用紧锁数十载的腹心之言送酒,直喝尽了刘府存酒,却仍能令醉意冲淡百感交集的苦涩。当两人同榻而卧时,方才明白:他们这一生的骄傲与艰辛,其实不用相互叙述,是非曲直、恩怨情仇,自有青史可证。
翌日清晨,韩泰将登路程。两人俱已五十多岁,如此年纪作千里之别,几成诀别。刘禹锡不忍离别悲情,只将韩泰送出街外,不敢远送。临别时,刘禹锡口占五首,既有怀念故旧之谊,又有为韩泰湖州新任之祝愿:
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
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
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
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
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
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
骆驼桥上风起,鹦鹉杯中箬下春。
水碧山青知好处,开颜一笑向何人。
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
韩泰挥泪告别,二人果真再未相见。大和五年(831),韩泰卒于任所。
刘禹锡见到韩泰,心中终归是充满欢喜的。宪宗去世已久,当年恩怨已泯,而刘、韩岿然尚存,焉知无有晚达之期?刘禹锡独自登上池上亭,望着远方风物,暗自吟诵: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
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
——《昼居池上亭独吟》
在恬静幽雅、孤独闲适的闲居中,刘禹锡师蜂自励,修德至勤,在表现“身闲志不闲”高尚情操的同时,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其内心之不平,在于心系社稷。
又过一年,刘禹锡果然看到了重归大唐权力中枢的曙光。大和二年(828)春,在宰相裴度、窦易直和淮南节度使段文昌的极力举荐下,刘禹锡调回京城,任主客郎中。
再度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刘禹锡心中横生孤傲。他笑了,他笑那多灾多难的命运最终被他制服,踩在脚下。那些曾经对他恶语相加、造谣中伤之徒,还有几人能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主客郎中虽然官非枢要,但已有力地宣告,刘禹锡不屈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刘禹锡快马加鞭,赶赴京城。但他到达京城的第一站,既非投宿馆驿,亦非向郎署报到,却是去了玄都观。
元和十年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让刘禹锡复官梦碎,令他始终不能释怀。他曾无数次梦见玄都观中的桃花,他发誓有生之年必要再到玄都观,再写一首咏桃花之诗。
可是刘禹锡失望了。大和二年春天的玄都观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百亩桃花。昔年春游胜地,今日已成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宪宗、穆宗两代皇帝皆因服食金丹而暴毙,玄都观受到牵连,道士们被驱遣一空。无人照料之下,桃花、道观何能独存?
失望过后,刘禹锡却又仰面大笑:这玄都观中的桃花,看来果真与他有缘!当年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引发轩然大波,而今不仅桃花都不见,连种桃树的道士也都没了踪影,岂不恰好暗喻了奸邪小人们失势灭亡的命运吗?满目的荒凉在刘禹锡眼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无意于幸灾乐祸,但绝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嘲讽: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然而,玄都观似乎是刘禹锡命中的煞地。命运便是如此荒唐,刘禹锡第二次在玄都观题诗,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意外的挫折。
得两位宰相和藩镇重臣保荐,大和二年(828)秋,刘禹锡旋又升任集贤殿学士。时裴度在中书省,有令禹锡知制诰之意。白居易时任刑部侍郎,闻知喜讯,来诗称贺道:
暂留春殿多称屈,合入纶闱即可知。
从此摩霄去非晚,鬓间未有一茎丝……
——《和集贤刘学士早朝作》
刘禹锡亦从裴度处得到消息。按常理,刘禹锡知制诰后,便可正拜舍人,渐有入相之望。禹锡以为仕途果然从此豁然开朗,亦在《早秋集贤院即事》中将沉沦多年后重登要津的深切感慨一展无余:
金数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树含秋露晓,阁倚碧天秋。
灰琯应新律,铜壶添夜筹。商飙从朔塞,爽气入神州。
蕙草香书殿,槐花点御沟。山明真色见,水净浊烟收。
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幸依群玉府,有路尚瀛洲。
可惜,刘禹锡刚刚望见的通往瀛洲之路,迅即被李宗闵之辈拦断了。《再游玄都观》一诗中透露出的桀骜之气和对新贵们的不屑之情,刺痛了李宗闵的神经。他指使言官上书弹劾,请托宦官屡进谗言,无所不用其极,硬是令裴度欲使刘禹锡知制诰的计划胎死腹中。
未能如愿知制诰,刘禹锡难免失落。裴度虽有同情之心,却无再擢之力,只能尽其心力,助刘禹锡在大和三年(829)除礼部郎中,仍兼集贤殿学士,每日与古今典籍为伴,兼管判别从天下州道送来的各种祥瑞呈报。数年之中,刘禹锡在长安除编纂书册外,只能常随朝中阁老们饮宴游乐,做些应景唱和文章,虽然博得虚名无数,但他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身体枯萎的声音,这象征着生命之火将要燃尽的声音不断敦促着他,一定还要为社稷做些实在的贡献。
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中,从不拉帮结派的裴度终于发现自己无法战胜李宗闵、牛僧孺之朋党。大和四年(830),裴度守司徒、兼侍中,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离开了京城的政治漩涡。失去了裴度的庇佑,刘禹锡知道京城已无立足之地,求分司东都未果。又经一年,刘禹锡将所编两千余册典籍进奉内廷后,终得外调之令,出为苏州刺史。
大和六年(832)初,在京数年时光,竟无半点建树,刘禹锡再次怀揣失望之情离开了长安。在洛阳,刘禹锡再次见到了白居易。大和三年时,白居易已求得分司东都闲职,安心过起了不问世事的恬逸生活。当他看到刘禹锡仍在为仕途宏愿而奔波时,他把送到嘴边的劝说咽了回去:如果刘禹锡也甘愿在家养老,那还是刘禹锡吗?白居易不再多言,只将苏州情形尽皆告知,聊作一臂之力,然后只顾劝酒,尽情欢乐。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明水秀、风物清嘉的苏州是江南之冠,素来是唐代诗人的向往之地。加之,刘禹锡出生地离此不远,自幼在江南生活,任苏州刺史无疑使刘禹锡有归来之感。上任伊始,恰逢苏州水灾,刘禹锡为民请命,开仓赈饥,免赋减役,拯苏州百姓于水火。水灾过后,刘禹锡走入市井,探问农耕,教泽市民,安抚百姓。数月之后,苏州已复灾前繁盛之状。
曾任浙东观察使的李绅途经苏州,仰慕刘禹锡之名,着人持名札邀刘禹锡赴宴。席间,李绅邀舞女助兴,并着数个歌妓作陪。酒至半酣,刘禹锡见作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诗的李绅如此奢靡,不由诗道:
高髻云鬓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赠李司空妓》
诗意李绅花天酒地,习以为常,而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从此不胫而走。
对权贵,刘禹锡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百姓,其倡导“功利存乎人民”。无论身居何处,刘禹锡皆能守正不阿,重土爱民,兴教重学,其执政能力终于在苏州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与褒扬。浙西观察使王璠在苏州看到刘禹锡杰出的政绩后,在考课中将刘禹锡列为“政最”——这是和平时期大唐地方官员极少能得到的荣誉。朝廷特加褒奖,赐予刘禹锡紫袍、金鱼袋,以示荣宠。
获得紫金鱼袋的奖励,无疑是刘禹锡官场生涯中值得骄傲的篇章。刘禹锡明白,这也许就是他能在官场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穿上华美异常的紫袍,佩上贵气不凡的金鱼袋,刘禹锡却泪如雨下,虽知文宗皇帝只是宦官傀儡,亦将满腹冤屈与感恩尽书于《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中: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书,加臣赐紫金鱼袋,馀如故者。恩降重霄,荣沾陋质。虚黩陟明之典,恐兴彼己之诗。宠过若惊,喜深生惧。臣某中谢。臣起自书生,业文入仕。德宗朝为御史,以孤直在台;顺宗朝为郎官,以缘累出省;宪宗皇帝后知其冤,特降敕书,追赴京国。缘有虚称,恐居清班。务进者争先,上封者潜毁。巧言易信,孤愤难申。俄复一麾,外转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滞淹,哀臣宿旧,猥见收拾。职兼书殿,官忝仪曹。微劳未宣,薄命多故。又离省署,重领郡符。延英面辞,亲承教诲。衔命即路,星言载驰。到任之初,便逢灾疫。奉宣圣泽,恭守诏条。上禀睿谋,下求人瘼。才术虽短,忧劳则深。幸免流离,渐臻完复。皆承圣化所及,遂使人心获安,岂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亲党,家本孤贫。年衰无酒色之娱,性拙无博奕之艺。自领大郡,又逢时灾。昼夜苦心,寝食忘味。曾经诬毁,每事防虞。惟托神明,更无媒援。岂期片善,上达宸聪。回日月之重光,烛江湖之下国。丝纶褒异,苦节既彰。印绶炜煌,老容如少。望云天而拜舞,岂尽丹诚?视环玦以徘徊,空嗟白首。无任感激屏营之至。
与朝廷所加紫金鱼袋相比,苏州百姓对刘禹锡的爱戴,才是令他最为欣慰的奖赏。大和八年(834),刘禹锡在苏州百姓夹道相送的哭声中,在“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的不舍和惆怅中,调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使后。此后,苏州百姓自发地建起“三贤祠”,以供奉曾为苏州做出巨大贡献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千年以降,香火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