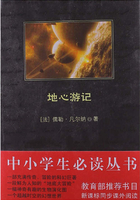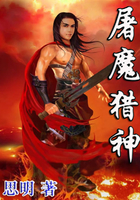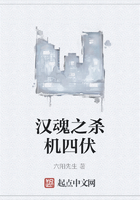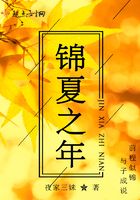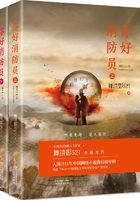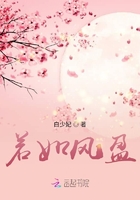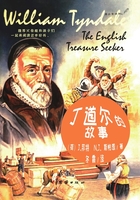上文提到,在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围绕印第安文学的性质与功用的派系纷争贯穿于学术评判和知识建构的整个过程,构成了持久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美学与政治的历史纠缠,也反映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迫于主流社会的政治压力,身份建构肩负着民族主义的沉重使命,但在以文化杂糅为基调的当代社会,身份话语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困,而近年来土著研究中民族主义的悄然兴起又使得“文化批评与文化政治”的矛盾愈加尖锐,一如后殖民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所说,“正当文化批评使过去成为现在手上的玩物时,过去的包袱却在对文化身份的重申中缠绕着当代政治”。
所谓“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民族主义”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印第安文学批评与身份话语密切相关,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问题盘根错节,缠绕着知识建构和学术评判的过程,使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其次,民族主义反映了土著社会的现代性张力,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有效范式,但是,随着土著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身份话语呈现出复杂的谱系,民族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界需要重新审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诸多问题。最后,随着土著文学的成熟及其疆域的扩大,在跨民族政治(transnational politics)语境下重新定位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性质与功用具有了紧迫性。跨民族视域注重文学批评的国际化资源,既可以提供一种清晰的“抵抗”模式,还可以参与“全球主义与地域想象”的政治架构,超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元模式。本章通过梳理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切入其中的主要论争和核心问题,以期把握印第安文学的总体发展态势。
民族主义的历史成因
土著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与这些已达目的或正在纷争之中的旨在独立建国的民族运动有所不同的是,当今世界的土著民族运动应该说是民族运动中的一股强劲势头。土著民族问题是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造成的直接后果。在美洲,15世纪以来,西欧国家在美洲大陆的大规模殖民扩张,驱赶和屠杀了大批原住民族。在几百年的殖民化过程中,美洲和大洋洲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著民族不但人口大量减少,在经济、政治方面也逐渐边缘化。在美国,印第安人被驱赶到保留地中。近二三十年来,土著民族开始维护自己权益的行动,形成了地域广泛、规模较大的土著民族运动,以争取和维护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为了人权、自决、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文化完整性进行斗争,包括对保留区内部的各项权利、经济和社会发展、教育、语言、卫生健康、司法、征税、土地、环境等问题提出诉求。在文化领域,土著民族主义运动也形成了较为强劲的力量,体现在民族身份诉求的各个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土著美国文艺复兴就是土著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
在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身份话语展开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关于土著社会和文化的知识?这个问题必然地引出下列问题,即,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土著美国身份是什么?谁是印第安人?这些既是认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如果印第安人是具有独特文化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民族或族群,其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印第安学者伊丽莎白·库克琳指出,“之所以提出‘谁是印第安人?’这个问题,是因为美国印第安人被视为被殖民的民族,具体说,因为美国的‘最初国家’的自治和主权一直被视为某种偶然性的结果,理由是印第安人和印第安国很快就会消亡,其作为国家公民的公民权也因此不复存在或很快消亡。自殖民时期以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界定和描述土著部落的。”因此,自治、主权、土地、血统和社区政治必然地成为土著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内容。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土著研究在学科论战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历史和现实看,很难说美国联邦政府与土著社会在主权问题的论争上会有实质性的进展。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土著民族不大可能获得辞典意义(独立和自治)上的独立主权。如阿诺德·克鲁帕特所说,“政治自治和文化主权只有在特定语境下和特定关系中才具有意义”。在政治层面,自治是基于土著部落与联邦政府在不同层面上谈判的实质性的和有形的结果;在文化层面,主权则是在部落文化习俗与欧美文化接触、冲突和对话的过程中确立的。
所谓土著民族性与主权的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外在的身份,如“美国联邦政府印第安事务局”关于印第安人身份认定的条例。美国政府承认印第安人为独特群体,这是关系到种族生存的政治性表述。二是从内部确定身份,认为确实存在尚未被殖民经历侵蚀的印第安文化,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挖掘那个文化并为其代言,表达“印第安人的声音”。在当代学术界,“印第安人的声音”一语的基本理论含义是:印第安文化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宇宙观和价值观,这是民族主义批评的基本信条。民族主义者认为,印第安身份是个政治问题,隐含着土著社会对主权的坚定诉求,必须由印第安人来决定。历史地看,部落主权是基于17世纪以来土著人和欧洲人签订的各种条约和法律文献之上,这些文献记载着历史上存在并始终坚持不懈地试图建立或重建部落主权、被欧洲人称之为“印第安国”的政治实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治、主权与部落传统有着相辅相依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是土著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民族性的主要依托。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土著社会对自治、主权和传统的诉求步履维艰、充满矛盾,但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已成为身份话语的强有力支撑。
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印第安文学异军突起,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剧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不仅受到美国主流学界的关注,还吸引了世界文学界的眼球。随着创作的日臻成熟,印第安文学批评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印第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和知识形态一直存在争议,也面临传统学科内部诸多的知识误区。历史地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院派一统天下的美国文学界,土著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复兴。无论任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印第安人研究是民权运动的结果。在美国大学,最初的土著研究课程更多地是对既定知识范式或学科结构的回应,而不是致力于关于土著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这些学术行为的初始动机是政治性而非学术性的。应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多元文化政治和土著文学创作的繁荣为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机构化奠定了基础。
虽然印第安文学创作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印第安文学批评则发轫于20世纪中叶稍后。第一部具有民族主义视野的批评著作当属查尔斯·拉尔森(Charles Larson)的《美国印第安小说》(American Indian Fiction,1978)。拉尔森摒弃了时下流行的人类学方法,致力于“文化政治与美学之关系的评判”。拉尔森指出,“一部小说不仅是人类学的研究资料,还为土著人民提供了从自身的视角去讲述历史、消除误解的重要手段。”拉尔森描述了20世纪印第安作家对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所做出的回应,把土著文学视为抵制殖民主义、挑战主流文学和历史再现、表现民族性的重要手段。拉尔森触及了民族主义的关键性问题,有一定前瞻性。不过,虽然他把土著文学界定为产生于土著社区的文学,但他认为其功用“主要是向美国白人社会呈现土著美国人的生活画面,在人们忘记他们之前记录印第安人的生活”。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是成问题的,反映了时代的局限。
在拉尔森的《美国印第安小说》出版五年后,肯尼斯·林肯的《土著美国文艺复兴》(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1983)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批评的里程碑式著作。林肯的关注点是传统(口述)与现代(书写)的关系。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林肯与拉尔森之间的分歧开启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林肯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是“以书写形式将土著口述表现形式翻新和翻译成西方文学样式的尝试。当代印第安文学与其说是全新的创作,不如说是传统的延续和更新”,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去“探寻文化传统与其当代表述之间的传承关系”。林肯以诗歌、小说和自传为例,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了土著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传统、神话和仪式的功用。在林肯看来,土著文艺复兴乃是土著社会在殖民语境下恢复部落传统并使之永久化的政治行为,但与拉尔森不同,林肯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文本与土著社会现实的关系。其实,林肯把“土著传统”作为一种隐喻结构的修辞性表述有将传统束之高阁的危险,是有悖于其政治初衷的。对后来的印第安批评家而言,建构连接土著传统、社区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政治美学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阿诺德·克鲁帕特的“族裔批评”(ethno-criticism)就是这样的尝试。作为高屋建瓴式的理论架构,“族裔批评”锁定土著性、民族性与反殖民政治的关系,揭示“霸权所赖以确立的两元逻辑”,这种逻辑导致排他性的文学典律的确立、对土著文本的忽略和非语境化的批评定势。克鲁帕特主张采用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来阐释土著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并通过“反霸权翻译”(anti-imperial translation)实现“本土与西方的对话”。为此,克鲁帕特把“族裔批评”界定为旨在探索“以土著视角观察社会、化解或抵消西方视角、颠覆西方认知模式和伦理价值体系”的跨学科比较研究,“重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影响乃至改变现行社会秩序”。可见,在克鲁帕特看来,对话与承诺对于颠覆学术体制内部的殖民关系是必要的。为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分离主义,因为文化分离主义试图回避土著社会与主流社会之关系的复杂性,也无法反映出土著文学的融合性特征(syncretic nature)。
“族裔批评”是克鲁帕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阐述。自20世纪80年代起,克鲁帕特一直努力搭建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政治美学框架。早在《边缘的声音:土著美国文学与典律》(1989)中,他就通过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多元文化主义”和“族裔批评”等概念的阐释将其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纳入其独特的民族主义框架。在《边缘的声音》中,他探讨了传统与典律的关系,认为全面恢复印第安文学合法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克鲁帕特的主要关切是印第安文学的边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失语状态,为此,他敦促学界“重新勘定美国文学之疆界,将印第安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正典”。
克鲁帕特的对话和融合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可以在后来的土著批评家的著述中找到其影响的印迹。例如,格里格·萨里斯(Greg Sarris)的《土著妇女生存》(Keeping Slug Woman Alive,1993)考察社会实践、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的关系。詹姆斯·鲁伯特(James Ruppert)在《当代土著美国小说的媒介问题》(Mediation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Fiction,1995)中把土著文学创作界定为旨在完成认知重构和视角转换的“意识形态翻译过程……利用土著文学和西方文化传统的互补性来表现艺术和思想的跨文化创作”。艾尔维拉·普利塔诺(Elvira Pulitano)的《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Toward a Native American Critical Theory,2003)则提出一种介于土著传统与西方美学之间的话语策略。这些批评家都强调跨文化对话的政治意义,并将这一概念融入民族主义话语之中。可以说,对跨文化语境的强调代表了克鲁帕特之后民族主义批评的走向。
身份政治的复杂谱系
历史地看,以克鲁帕特为代表的介入式批评突破了拉尔森和林肯以来的民族主义局限,把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这种批评范式仍有可能演化成为另一种形态的权力话语。克鲁帕特认为这主要源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批评家不得不去生搬硬套、挪用或曲解印第安文学的创作实践本身。”因此,“文化翻译”是一柄双刃剑,极有可能成为主流社会的工具,将研究对象转化为知识对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替‘印第安人’说话,从而将其绑架在主流话语之下”。
的确,殖民关系是印第安文学批评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深层含义是,土著社会与欧美社会的接触、交往和冲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土著社会本身?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这个问题又会引出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否存在泛印第安核心价值和文学范畴?要回答上述问题,民族主义批评家的任务是论证作为政治和文化主权主要内容的身份话语的性质,包括印第安人的地理文化、历史变迁、语言习惯及其文化表述的独特性,说明印第安社会一直维系着独特的身份特征,这些特征建立在部落文化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并以独特的、可识别的形式表现出来。林肯就曾对泛民族主义价值观做过界定(“印第安社会的凝聚力源于部落与宇宙万物的亲和关系”,“人的声音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等)。杰西·韦弗把“社区的重要性”视为土著社会共有的特征。罗伯特·沃里亚则在不同地域和社区的作家(Vine Deloria,Jr。and John Joseph Mathews)的作品中寻找共性。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致力于探索各部落历史经历之间的联系,把“在殖民主义之后重新发现或再现身份认同”视为“美国印第安小说的核心。”克雷格·沃玛克把文学分析建立在对民族性的挖掘上,认为口述传统及其所蕴含的世界观是“主权民族主义”的基石。
虽然上述批评家对民族性的定义过于宽泛,但它却道出了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相关性。毋庸置疑,这种民族主义立场隐含着一种静态文化观和本源论,在文化层面往往导致本质主义,在政治上具有分离主义指向,在日趋多元化的当代社会,要维持这种身份话语越来越困难。文化分离主义的基本假定是:印第安人思维方式(民族性的代名词)在殖民入侵前就已存在,是印第安文化以外的人无法理解的,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挖掘并恢复被破坏的土著文化。这种呼声不仅使得作为部落身份和主权载体的文学话语变得异常复杂,还使得多元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双重制约下,民族主义批评家对克鲁帕特的族裔批评能否避开诸如此类的话语陷阱深表怀疑。他们认为,批评家不应纠缠于主流话语的评判问题,而应当致力于探索主权的可能性。库克琳认为“探索21世纪土著或部落主权的重要性”乃是批评家的首要任务。由于主权关系到土著社会的切身利益以及批评家(或作家)的政治立场(为谁代言、为谁写作),因此,美学、政治、法律问题盘根错节,构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复杂谱系。沃里亚的《部落的秘密:重获美国印第安文化传统》可以说体现了这样一种视角。沃里亚认为,土地权利、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构成了印第安文学的大背景,印第安文学的批评和阐释应直接产生并服务于土著社会为争取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第安人的未来取决于土著社会能否在政治主权的前提下回归土著仪式和传统”。《部落的秘密》力图实现这种回归。不过,沃里亚回避了诸如民族性和土著性等传统论题,而是强调“社区主义”(communitism),关注与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平均收入低、患糖尿病率、婴儿死亡率、辍学率高等)。萨利·洪多夫(Shari Huhndorf)也强调民族主义批评最重要的政治承诺就是关注土著社区、主权、民权、土地、健康和贫困等紧迫问题。杰西·韦弗在《土著美国文学与土著美国社区》(1997)一书中延续了沃里亚的思想,强调文学创作与社区核心价值的关系。沃玛克在《土著美国文学中的分离主义》(1999)中把克里克族(Creek)作家(Alice Callahan,Alexander Posey,Louis Oliver,Joy Harjo)的作品放在克里克文化史中进行阐释,把文学批评提高到主权维护与民族性建构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
土著文学和由土著学者所从事的土著文学批评是土著主权的一部分。印第安人有呈现和探讨他们自己形象的权利。土著作家进行创作、土著批评家对这些作品进行评论是建构民族性的重要步骤。虽然主权的文化属性并不能等同于土著民族的政治地位,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族性的重要一面就是人们对自身的看法,对身份的再现。通过想象、语言和文学作品来表现部落的声音有助于强化公民对主权的诉求,赋予主权由部落而不是局外人所界定的意义。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沃里亚的思想痕迹,把主权视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尺度。
总之,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始终充满了张力。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文学的含义已变得非常复杂:它既是民族性的体现,又是文明冲突的见证和殖民历史的符码,反映了部落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或许,印第安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话语,该领域内部愈演愈烈的派系化之争就是这种矛盾最直接的反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多元文化已经体制化的今天,印第安文学批评内部悄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确面临巨大挑战,需要重新审视该领域内部的诸多问题。
跨民族视野中的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
徘徊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印第安文学批评走到今天,可谓步履维艰,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德里克在论证后殖民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时把这种张力称为“全球主义与地域想象”的冲突,指出跨国规模下的文化变形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复杂的表意形式。民族主义、种族认同、本土主义已经在全球作为文化政治的标识出现,种族地位问题移至政治舞台的中心。人们努力去发现或恢复真实的过去,把它当作现今文化身份的基石,这种努力同时也伴随着拥有文化真实性的声明,这在饱受“历史带来的痛苦”的人看来尤为迫切。就印第安文学批评而言,这种紧迫性在于如何处理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与美国主流学界的关系;二是与世界文学总体进程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构成了德里克所说的“全球主义与地域想象”的宏观架构,喻示了超越民族主义局限的新思路。
在2002年美国研究学会(ASA)年会上,三位土著批评家罗伯特·沃里亚、菲利普·德洛里亚(Philip Deloria)和让·奥布莱恩(Jean O’Brien)在谈到土著文学与美国研究的关系时都提到土著文学的边缘化问题:美国大学印第安学者、土著研究博士学位和学术期刊寥寥无几,普遍的冷漠导致土著研究“学术上无家可归的局面”(intellectual homelessness)。十年过去了,这种机构性歧视仍然存在,“土著学者无所归依的局面”反映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土著民族主义的悄然兴起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坚持政治化原则,确立“土著学派”,“把握知识和学术走向”,“坚持土著民族的民族性和自治权力”等。这种激进的措辞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与政治话语的平行关系。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殖民主义已经发生并决定着土著与非土著的关系,因此“殖民化”仍然是理解印第安文学的基本框架。从发生学角度看,土著文学源于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这段历史及其后果构成了土著作家的写作背景和素材。有鉴于此,克鲁帕特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在美洲大陆对土著居民的压迫无处不在,而且这种压迫(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今天仍在继续,因此,必须把土著文学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不过,如何界定印第安文学与后殖民研究的关系,学界内部也存在分歧。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抵抗”模式,把文学理解为“解构殖民主义和重建文化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后殖民理论家通常优先考虑民族国家问题,而印第安人的殖民经历更多地涉及法律、政治和经济控制,后殖民理论的移植还需根据殖民主义的表现形态(如“内部殖民”)做具体分析。无论如何,后殖民研究框架可以为印第安文学批评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接口,而比较视野的缺失则有可能导致印第安文学的进一步边缘化,这也是许多土著批评家所担心的。克鲁帕特就曾强调这种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土著美国小说是在持续的殖民主义语境下产生的……许多作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后殖民小说创作遥相呼应。”克鲁帕特的思想轨迹对于理解民族主义很有启发性。在《土著转向:批评与文化研究》中,克鲁帕特关注民族主义的国际化语境,赋予“世界主义”以复杂的、个性化的解释,拓展了该词的含义,强调民族主义、土著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共性,注重国际化资源。在《红种人的重要性》中,他重申“国内外被殖民群体的政治斗争中主权问题的重要性,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把反对殖民主义作为其共同目标”。
近年来,随着印第安文学创作日渐成熟,在跨民族语境下重新定位印第安文学批评具有了一定的紧迫性。艾瑞克·谢弗茨(Eric Cheyfitz)指出:“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并非从后殖民研究那里套用术语,而是为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这一论点后来成为谢弗茨编辑《哥伦比亚指南:1945年以来美国印第安文学》的主要依据。库克琳也强调印第安文学对世界文学(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独特贡献,关注二者的亲缘关系和主题相似性(如压迫、离散、错位、殖民、种族主义、文明冲突、流放、抵抗、主权、民族性、自治等)。库克琳认为,印第安文学的世界主义已经出现,而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探索“部落主权的重要性”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性。查德威克·艾伦(Chadwick Allen)的《血的叙事:美国印第安、毛利族文学与社会文本中的土著身份》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跨民族视野的著作,探讨美国印第安文学和新西兰毛利文学中“定居殖民地语境下的土著性建构问题”。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还建议把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内部殖民和帝国扩张时期的作品平行比较,探讨“扩张、征服、冲突和抵抗的多重历史经历”。在这方面,约翰·卡洛斯·罗(John Carlos Rowe)关于帝国与文学生产的相关著述都是颇有见地的研究。在此框架下,土著女性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另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波拉·G·艾伦(Paula Gunn Allen)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她的《神圣之圈:重获美国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品质》(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1986)对新生代土著女性批评家(Cheryl Suzack,Monique Mojica,Janice Gould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们以特有的视角切入种族、阶级和身份政治,践行着女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关注社区物质环境和现实问题,成为连接土著学界与国际批评界的重要纽带。
宏观地看,在跨民族政治语境下来规划印第安文学批评有着广阔的空间。跨民族的研究视域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基本问题(部落主权、政治自治、文化身份、现代性)纳入宏大的政治架构,注重民族主义的世界语境和国际化资源,从而摆脱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单一模式,在“全球主义与地域想象”的交汇中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切,使印第安文学批评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