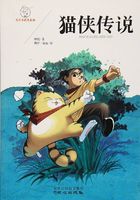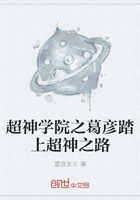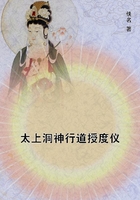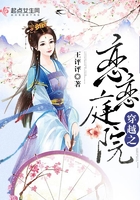(一)婚礼是自由的挽歌
1988年,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
“据《纽约时报》二十四日报道,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女士,已在上周六(二十一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曼哈顿寓所,享年八十八岁……”
张幼仪去世了。
她的离开,终于定格了近代中国文坛上一幅鲜活的情感画面,而那出被几代人评讲的,关于自由与爱情的现实剧,也仿佛随着她的离开,终于散了场。
张幼仪是这出戏中最早登台的演员,最后离场的角色,但她似乎从不是戏台上的主角。直到她谢幕的那一刻,也直到今天,她的名字仍然与“徐志摩元配夫人”的头衔形影不离。不能怪世人忽视幼仪的光芒,只是与她同台的徐志摩如同喷薄的朝阳般,太耀眼。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难免陷入他制造的阴影中。其实,不单是张幼仪,哪一个与徐志摩有关的女人,在被人提及时不带着一点儿徐志摩的味道?更何况是被徐志摩拿来,为“新思想”祭旗的张幼仪。
张幼仪最初上场的那一年是1915年。那一年,中国的飘摇与动荡与往年相比,或许并没有不同。每个人都在历史的航向上,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这一年,袁世凯正为了他的千秋帝国梦,紧紧攥着跟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竖起了人权与科学的旗子;孙中山与宋庆龄刚刚在东京举行完婚礼;蒋介石的肇和舰起义并没有圆满的结果……
国是大家的国,家是个人的家。帝制,人权,科学,革命,这一切似乎都与海宁硖石徐家的婚礼无甚关联。若一定要说有关,也不过是这场婚礼多少受了些时髦的西洋观念的影响,脱离了中国传统婚礼的形式,是一场 “文明”的西式婚礼,没有“拜堂”。
十六岁的张幼仪纱裙曳地,那份被热闹的人群与欢乐的仪式催发出的兴奋、好奇与不安,化作红晕爬上了她的脸庞。尽管她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打量身旁的丈夫,但婚礼的规矩与礼仪阻止了她的视线。年轻的新娘能做的,只是低顺着眉目,安静等待仪式的结束。
这场婚礼对于张幼仪来说,或许有点突然。在得知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前不久,她才刚刚说服父母,送她去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尽管幼仪深晓,作为女人,自己的前途并不在家人的期望中,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牢牢扎在父辈的心里的女德标杆,千百年了,没有变过。但是,在她生命底质中,潜伏着一种特质,应和了汹涌灌进中国的西方新文化。这让她鼓起了勇气向父母提出上新式学校的要求。
在学校里受到西方教育的张幼仪,聆听了新的主张,但对婚姻的观念,她顺从了中国传统女子的另一种特质,父母之命。不过,确切点说,帮幼仪挑选夫婿的是她的四哥张公权。幼仪还记得那天,她的四哥兴冲冲地从外头回来,告诉她,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一表人才,才气不凡。论人,他配得上张家的女儿,论家世,海宁首富徐家也配得上张家的显赫的声势。张幼仪,这个聆听了新思想的女性,此时听从了旧言论,甚至没有一点怀疑。
她的丈夫……张幼仪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将视线移向了身旁的徐志摩。与所有旧中国的婚姻一样,她在婚前与这个男人并没有交集。现在,她也只是看到一个清瘦的侧影。她的丈夫有圆润的额头,鼻子很挺,俏俏地立着,薄的嘴唇抿出温柔的线条。尽管她不了解他,但也并非一无所知。毕竟,徐家公子,硖石的神童,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有谁没听过呢?现在,他已经是燕京大学的预科学生了。他的学问应当要比自己好的,他的思想自然也超在自己的前面;将来,他还要留洋去的。所以,这时的幼仪最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丈夫的为人与前程,四哥疼她,替她看中的人不会有错。显然,她现在最在意的,是她能否跟上这个聪明而新潮的丈夫。
正因如此,张幼仪的心里对二哥张君劢的感激,在今天涨到了顶点。二哥在她三岁那年解开了家人裹在小幼仪脚上的厚厚白棉布,放开了她的小脚。所以今天,她有了一双大脚。尽管这双大脚曾被家里的婆婆,姨妈,姐妹们很是嘲笑了一番,但大脚代表着“新式”呢。所以,今天的她站在这场西式的婚礼上,与西装革履的丈夫,看上去才能如此般配。
张幼仪此刻庆幸她有一双大脚,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她的那双大脚放在眼里。就是到后来,也没有。
徐志摩不时瞅瞅身旁的新娘,想起两年前,父亲递给他一张姑娘的照片,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照片里的张幼仪看不到特别的好,但也不难看。只是生得有些黑,嘴唇似乎也厚了一些。其实,幼仪长着一张典型中国少女的脸,圆润而柔和,沉静的眼里刻着大家闺秀应有的大气端庄。可徐志摩没由来的一阵嫌恶。
他知道,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徐家的生意,张家的声望,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这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如果这桩婚事被安排在十年以后,徐志摩也许会高喊着:“我要追求爱的自由与婚姻的权利。”并拒绝父母送给她的新娘。但此刻的他,没有。
也许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还不够坚韧,也许是父母的命令与张家显赫的声势一起制成的牢笼太坚固,总之,那天他只是将自己的不满,变成了下垂的嘴角,吐出了一句:“乡下土包子。”他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甚至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妻子,便用自己的妥协,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中。
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最大的心结。这个结,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捆住了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通道。他觉得,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但却与自己的灵府如此不搭调。新式的衣装,与这骨之里的旧,让自己显得这样滑稽。
徐志摩与张幼仪一起向“旧”妥协了。在那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徐志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对抗的东西究竟是何等深刻,或许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当他妥协的那一刻,他与“小脚”的女人并没有质的差别。但徐志摩毕竟曾立志,要“冲破一切旧”。只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冲破的方式时,一切就在他毫无准备的思想里发生了,而他灵魂的一部分仿佛还留在北京的锡拉胡同里。那里,住着蒋百里。
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弟弟。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拜梁启超为师。回国后,蒋百里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尚武的血液,怀抱着爱国的热诚。更难得的是,学贯中西的蒋百里,在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同时,在文学与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他的《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立论独到,文辞流畅,颇有梁启超之风;而他的书法也深具晋人气韵。
徐志摩在1915年考上燕京大学预科班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平日里,徐志摩与蒋百里谈时事,聊文学,评历史,讲政治;他敬蒋百里,爱蒋百里,虽然蒋百里长徐志摩十四岁,可徐志摩与他甚是亲近,无话不谈;他徐志摩口中最亲的“福叔”。与蒋百里的交往,让当时的徐志摩在思想上趋向政治。在一次闲谈中,蒋百里曾对徐志摩说:“青年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你何不与他们一起出洋去,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
这话正说到了徐志摩的心里,此前,他已经有了留洋的想法。当初,他之所以报考了燕京大学的预科班而非本科,就是因为当时的燕大预科班注重外语的应用,学成之后可以尽快地留洋;此番,加上蒋百里对他的影响,徐志摩更是觉得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充满了奋斗的热情。他在锡拉胡同与学校图书馆两头跑,埋头在西方新思想中,闲暇时与友人聊聊戏剧界的“菊选”,别人爱梅兰芳,他独爱杨小楼;兴致到了还会跟朋友打打网球……
福叔劝他留洋时的神情还在眼前,杨小楼的腔调似乎都萦绕耳边,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墨香还都能闻见,怎么一转眼,自己就与这个不认识,不爱的女人站在一起了?做梦一样。父亲频频的电报是催命的符,那些“男大当婚”“识大体”“有利家业”的话是魔咒;祖母最疼自己,可她殷殷的期盼却把她那份深厚的荫慈变成了最重的包袱。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其实徐志摩心里清楚,与张家的联姻,不过是他的父亲在为独子规划前程的棋盘中,落下的一颗棋而已。
父亲徐申如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一生都在用精准的眼光打造生活中的一切。在他所有的实业中,有两件事最值得骄傲:第一件,是他在1908年联合了海宁的绅商,克服了重重阻力,硬是让拟建中的沪杭铁路生生拐了个弯,穿过了硖石,成就了海宁硖石地方几代人的福祉;第二件,便是儿子徐志摩。别的不说,单单是他为了让儿子的书法水平有所长进,便将当时的上海寓公,后来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著名书法家郑孝胥,聘作儿子的书法老师。这次,尽管儿子已经与张家小姐有了婚约,尽管他本应让儿子尽早将张幼仪娶进门,但他仍然顶着张家人的反对,亲自将儿子送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可以说,这个精明的父亲在儿子的培养上,同样用上了他敏锐的经商头脑。现在,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回来成亲了。
张家现在的名望不一般。看中自己儿子的张公权是当时的浙江都督府秘书,将来大有作为;而他的兄长张君劢则是有名的法学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徐申如再次以他精准的眼光,准确地预见了未来的张家兄弟在中国未来的政界与财经界中,呼风唤雨的地位。与这样一个有钱权有名望有修养的上流社会家庭联姻,徐申如没有再拖延的道理。于是,给儿子拍几封电报,对他进行几次动情的说理,徐申如便为他自己谋回了一个好儿媳。
这种境况下的徐志摩,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成了那个变革时期的精神缩影。或许很多东西可以在朝夕间改变,但也有许多东西无法轻言抛弃,比如孝道。这一点,即便是在他走出硖石,跳进那些欧洲思想家行列的那一天,也仍然无法割弃。
但他仍然得做些什么。于是,一场热闹的婚礼之后,他选择了冷漠。
(二)一个人的婚姻
冷漠,是这场婚姻唯一的韵脚。它的第一个音节奏响在张幼仪死寂的新房里。新婚之夜,洞房的花烛下,徐志摩一句话都没有对幼仪说,幼仪也不知该用什么,来打破她与这个陌生丈夫间的沉默。后来,徐志摩离开了,躲进了奶奶的房间。只是,他的行动力仍是敌不过长辈的希望。几天后,徐志摩在佣人的簇拥下,踏进了新房。
两年后,张幼仪怀孕了。关于这一点,浪漫的诗人有自己的解释,他说:“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徐志摩并没有因为肉体而将他对幼仪的爱推到顶点,相反,他对张幼仪的厌恶,却因肉体达到了顶点。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忽然觉得背痒,于是便唤佣人帮忙。一旁的张幼仪想,这样的事情何必佣人动手,于是便凑近了替丈夫解痒。可是她没有想到,徐志摩仅仅用一个眼神,便拒绝了她的献出的好意。那个眼神轻蔑,不屑,冰冷刺骨,多少年以后,张幼仪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幼仪其实是个很好的太太,但凡认识她的人总是对她印象极佳。时人曾评价张幼仪:“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也说:“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幼仪也是个很好的儿媳妇。她在徐家克守着一个好儿媳的本分:她帮着公公徐申如操持庞大的家族生意,照顾婆婆,管理徐家的下人,家事人际操持得井井有条。为了照顾公婆,她甚至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婚后的幼仪曾经写信给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表达了继续学习的愿望。但校方提出,幼仪必须重新修业一年,修满两年课才能毕业。新媳妇要离开公婆两年,这对幼仪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于是,她从外面的世界退回了硖石的老宅。幼仪的大脚并没有带她踏出自由的脚步。
幼仪是公婆眼中的好媳妇,甚至可能是许多人眼中的好妻子,但她却不是徐志摩心中的好太太。在徐志摩眼里,幼仪嫁过来以后很少笑过;她办事主动,有主见,有主张,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但徐志摩要的,是一个能与他的思想共呜,与他的浪漫情调合拍的女人;她的妻子应该有思想,有个性,应该是个开放,新潮的新女性;但张幼仪只是宝山县首富张家的小姐;她的偶像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的人生在徐志摩的眼中,始终沾染着铜臭;她的角色在徐志摩看来,不过是纠缠于家业中,翘着双腿对下人的指手划脚的管家婆。因此,张幼仪无论再怎样地温顺体贴,恭俭礼让,她在徐志摩眼中,也不过是旧婚姻的傀儡,旧制度下的陈旧女性。这个妻子于徐志摩,不过是个“守旧”的代名词,平庸而乏味地立在了浪漫与自由的对立面。他与她的思想,分明是站在时间的两端,空间越近,心灵越远。于是,一座旧式婚姻的围城困住了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