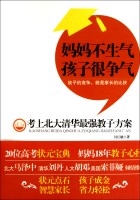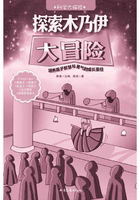或许,你的妈妈正年轻,有一口洁白的好牙;或许,你的妈妈一辈子也不用为你操心这些事儿。可年少的你,也要记得常怀感恩之心,好好与妈妈相处,因为不管是怎样清闲的妈妈,在子女的事情上,无不是耗尽全身力气。你的微笑,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愿母自私
我时常能读到学生的作文。年幼的学生们用稚嫩的小手给我写着,他们的妈妈是多么平凡而又伟大,因为她们吃尽了人间疾苦。为了力求感人肺腑,他们不惜把自己的妈妈写得万般悲惨。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足以打动我这位铁石心肠的老师吧。
孩子们的目的达到了。我时常被他们这些不知真假的故事糊弄得泪眼涟涟。整个清晨、午后,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忧伤之中。
几年后,这些孩子都长大了,陆续上了大学。再翻阅他们之前给我写的作文时,我竟有了一种惶惑:为何所有的妈妈都得这样悲苦?难道不悲苦的妈妈就不是好妈妈吗?
经常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类似的报道:某省某市的某位妈妈,为自己的孩子,甘愿捐出肾脏,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以保全孩子。某镇某村的某位妈妈,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步入学堂,接受教育,甘愿下洞挖煤,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
铺天盖地的新闻、纪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明白,并坚信,尘世中的每一位妈妈都有着一块无私的角落,用以安放自己的孩子。我们为此哽咽,为此流泪,甚至觉得,这样的妈妈是伟大的,也只有这样的妈妈才足以堪称妈妈。
我们要求这样的感动,要求这样的悲苦来填补我们日渐麻痹的心怀。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些妈妈站出来,作为代表,为我们诠释妈妈这个职业的伟大。
实质上,从过医的人,全然不用看这样的报道或是故事。他们明了,一个女人要从妻子变成妈妈,势必要经历尘世中最沉重的苦痛。
医学上,把人所能感受到的疼痛等分为十级。蚊虫叮咬为一级,分娩生子为十级。
我们尚且不说,这疼痛的等分合理不合理。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譬如,一个男子,因癌细胞扩散至下肢,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倘若,让他不施麻醉,毫无怨言地承受这整个手术过程所给他带来的苦痛,行吗?
我想,尘世中,没有几个男人能承受这样的苦痛。而类似这样的苦痛,每一位妈妈,却真切地尝试过了。
落笔之前,我曾去医院了解,每一位即将分娩的女子来此,医生都会问,要不要施用麻醉?施用的话,就不会有那么痛苦,只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
据这位医生的言辞,没有一位妈妈要求施用麻醉。她们宁可承受尘世中最大的苦痛,也要避开这万分之一的会影响到孩子身体健康的几率。
单从这一点来说,就足以让我们感动了。
前些天,妈妈过生日。有人问及,你送你妈妈何物?我答,仅四个字:愿母自私。
我觉得,已没有任何能送妈妈的礼物了。唯可让她高兴的,怕是我与弟弟的身体尚且安康吧。
未曾小学毕业的妈妈不明白我这几个字的深意。但我想,此时的读者是明白的。我只希望,全天下的妈妈能自私一点,把从天性里赋予我们的爱护,收回一点儿,分配到自己身上。
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任何一位妈妈再经受苦难。唯能督促她们,多爱自己一点儿。若真如此,那全天下的儿女,才算是尽了真孝。
最闪亮的明星
我曾被邀请参加一次有趣的活动。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挑选出校园里“最闪亮的明星”。而这些参赛选手,全都是不满十周岁的孩子。
他们个个傲气十足地站在台上,大有藐视群雄,“一览众山小”之感。
男孩们都西装领结,头发油亮,走起路来皮鞋噌噌作响。女孩们则身着连衣裙,扎起高高的马尾,眉心点起一颗鲜红的朱砂痣。
从装束上就不难看出,为了赢得这次比赛的胜利,他们都着实精心打扮了一番。
比赛分为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是个人才艺表演,分数颇低,不到总分的一半。那么大半的分数去哪儿了呢?看看评分细则才发现,原来都把它分配到最后一个环节里去了。
最后一个环节是双人游戏,意在测试参赛选手和自己妈妈的默契程度。谁要是在这一阶段得了高分,那八成就是冠军了。
台上的小选手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评委宣读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很简单,哪位妈妈要是背上自己的孩子,在第一时间里冲到终点,中途没有歇气,或把孩子放下,那就算赢了。
赛场是一个圆形跑道,足有400米,起点和终点是同一条线。我很想写,路仅400米,可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台上的这些孩子,每一个都不下六十斤,而他们的妈妈都长期生活在城市之中,未经受过什么磨难。如今,却要她们背上一个六十多斤的孩子奔跑400米,不歇气,不间断,这谈何容易?
没有一位妈妈弃权。
她们默默地背起自己的孩子,等待哨响,一路狂奔。
孩子在妈妈的背后相互嬉笑,打骂。被背着奔于前列的孩子,不停地大声催促自己的妈妈:“妈妈,快点,快点,他们就快追上来了!”
那些被甩于尾后的孩子则更大声地责备自己的妈妈:“妈妈,你快点啊,你看,他们都快到终点了!你太慢了!”
既然是比赛,那就一定会有输赢。第一位到达终点的是个小男孩,他欣喜地看着台下的观众,一脸神气,好像他已经知道自己将是“最闪亮的明星”了。
最后一位到达终点的是个小女孩,她把嘴撅得老高,不停地向后斜瞅自己妈妈所在的位置。好像是在抱怨,今天之所以没有胜出,完全是因为她的妈妈。
评委开口了:“现在,比赛结果已在我手中。请允许我宣布,‘最闪亮的明星’是……”一阵隆隆的擂鼓声中,所有孩子都瞪大了眼睛,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你们身后的那位!”
话毕,所有的孩子都转身而望。此时,他们才发现,因大汗淋漓而狼狈不堪的妈妈。看着看着,有的孩子哭了。跟着,所有的孩子都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他们的哭泣是不是由于失败,或是受到了惊吓。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些选手们已经明白了,此生中,谁是把他们看得最重要的人。
是啊!孩子们,这一路走来,有人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一直不变。因为在她的心里,你最重要;因为在她的眼里,把你看得最重。
天黑的时候
夜幕缓缓地从星辰的眸子里散开。所有在阳光里丧失了寻找机会的星星,终于气喘吁吁地探出眼睛,慢慢搜寻,这温暖的尘世中,还有一些什么值得他们次夜再临。
夜幕里,一位男孩儿紧紧抓住了妈妈的大手,他的思绪像大风一样在野外的路上狂奔。恐惧成山野里的荒草,卷裹着他,让他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他需要妈妈的手,温暖,宽厚,使他在寒冷而又漆黑的夜里,瞬间得以安定。
他知道,不论前方的路途怎样,妈妈一定不会松开他那双无助而又柔弱的小手。于是,他只管好奇地问:“妈妈,到了吗?到了吗?”
我看不清这位妈妈的脸庞,黑夜让她隐去了身形。可我坚信,此时,她的神色只有一种,她的回答,也只有这一句:“快到了,别急,孩子。你要是累了,妈妈就背着你,你靠着我睡。”男孩儿真困了,那么长的路,那么黑的夜,他细碎的步子往往要小跑起来才能跟上妈妈的速度。
他轻靠着妈妈的后背,在寂寥的星辰中沉沉睡去。妈妈双手向后,用手腕拦住孩子的大腿,用手掌托住他虚空的屁股。慢慢地,艰难地在黑暗的路途中前进。
妈妈曾是一位少女。她曾和男孩儿一样,惧怕黑夜,惧怕不可未知的世界。可此时,她却不知为何,心里竟没有了当年的惶惑和惊恐。她需要放慢脚步,哪怕这条路会因为她的迟误而变得漫长。她害怕的不是黑夜,而是黑夜里的石子会让她猛然摔倒,伤及此刻正在背上甜甜睡去的男孩儿。
她的步履变得越发沉重而又缓慢。她累了,像男孩儿入睡前一样,睁不开眼睛,手心里溢满汗珠。她努力闭上嘴巴,用鼻孔呼吸。这静谧的夜啊,谁知道前方有什么东西。她生怕自己厚实的呼吸会引来一阵黑暗中的狺狺狂吠。那么,男孩儿势必会从梦中忽然惊醒,泪水决堤。
她不害怕男孩儿的哭泣。她害怕的是男孩儿的惊慌,抑或男孩儿对黑夜的恐惧。她想要男孩儿勇敢些,于是,她就必须全面考虑。她不能因为一时的舒畅,而给男孩儿造成童年的阴影。她不希望在很多年后,男孩儿仍旧记得,在这条漆黑的路上,他曾被莫名的吠声给吓醒。
妈妈想要给男孩儿的,永远是温暖而又恬静的记忆。她腾出一只麻木的左手,捋了捋额前被大汗浸湿的乱发,站在原地,缓缓地弯腰,将男孩儿朝自己的背上抽了抽。而后,又缓缓地抬起身子,朝着前方的路,艰难而又镇定地前行。
妈妈在一盏亮着橘黄小灯的屋前停住了脚步。她没有放下男孩儿。男孩儿是在翌日的晨光中安然醒来的。他不知道昨夜妈妈的心中所想,他习惯了这样的夜。
很多年后,即便日光散淡,妈妈也只能一个人走过那条荒凉的小道。因为,此刻的男孩儿已然长大,而他的背上,也同样背着一个人。或是女儿,或是儿子。
妈妈没有伤悲,仍旧为男孩儿时刻准备着后背。因为在漫长的黑暗中,我们需要妈妈的手。那是孩子的需要,人性的归属。同样,那也是人世间温暖的源泉。
妈妈,把爱留给你,你把爱留给了你的未来。有一天,记得也陪妈妈走一段那熟悉的路,给那无私的爱一些温暖。
妈妈的勇气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2006年12月14日,深夜11点24分,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位头发花白的东方女人引起了所有乘客的注意。
她挎着黑色的背包,背包上贴有一张用透明胶带层层缠绕的醒目的A4纸,上面用中文写着“徐莺瑞”三个字。
那些从萨尔瓦多飞到洛杉矶的乘客,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他们根本不懂中文。这位衣着朴素的东方女人在等待了许久后,终于开始在人群中用蹩脚的普通话挨个询问:“请问你会说中文吗?请问你会说中文吗?”
临近午夜12点,她终于找到了救星。一位黑头发的男人驻足她的身前,低头端详她手里的纸条:“我要在洛杉矶出境,有朋友在外接我。”
其实,在这张揉得皱烂的纸条上,还有另外两行中文,每行中文下面都用荧光笔打了横线,方便阅读。
第一行中文:“我要到哥斯达黎加看女儿,请问是在这里转机吗?”下面,是两行稍微细小的文字,分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
第二行中文:“我要去领行李,能不能带我去?谢谢!”接着,同样又是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
原来,她的女儿在十年前随女婿移民到了哥斯达黎加。如今刚生完第二胎,身子很虚弱。女人思女心切,硬要从台湾过来看她,伺候她坐月子。女儿执拗不过,便在越洋信件中夹带了一堆纸条。
如今,她已伺候女儿坐完月子。原本女儿要陪她到洛杉矶机场,结果却因买不到机票而作罢。女儿为了让她有安身之处,特意请求远在洛杉矶的朋友帮忙。为了方便相认,女人便特意在背包上缠裹了醒目的A4纸。
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行程。可深知航班内情的那位黑发男人,却不禁被这简单的描述感动得热泪涟涟。
从台南出发,要如何才能到达哥斯达黎加呢?
首先得从台南飞至桃园机场,接着搭乘足足十二小时的班机,从台北飞往美国。再次,从美国飞五个多小时到达中美洲的转运中心——萨尔瓦多,然后才能从萨尔瓦多乘机飞至目的地——哥斯达黎加。
她曾在拥挤的异国人群中狂奔摔倒,曾在午夜机场冰冷的座椅上蜷缩,也曾在恍惚的人流中举着救命的纸条卑躬屈膝……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位真实而又平凡的中国妈妈。她来自台湾,名叫蔡莺妹,67岁;生平第一次出国,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西班牙语;为了自己的女儿,独自一人飞行整整三天,从台南到哥斯达黎加,无惧这三万六千公里的艰难险阻与关山重重。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妈妈因爱而萌发的勇气。这种匿藏在母性情怀中的勇气,从始至终都不会因距离和时间而改变心中的方向。生活中的你,或许不曾见你的妈妈用这些行动来证明她那爱的力量,可谁又能说,给孩子的爱,哪位妈妈不是用尽全身力气。
相送
阳春三月。妈妈执意放下所有农活,从小镇赶来送我。临行前,她再三询问贵重物件是否已经备齐,所需食物是否充足,车票是否保管妥善,等等。为了这次初春的相送万无一失,昨夜她特意安静地坐在电视前面,聆听我将到之地的天气预报。
我又一次跟在了她的身后。灰蒙蒙的天际下,远山冒出了隐约的葱绿,大风刮过田野,携卷着一股亲切的泥土味儿。我牵住妈妈,挡住她的匆匆去势,央求她就此别过。她如同当年顶着九月烈阳送我外出求学时一般倔强,让我无奈而又倍觉心疼。
站台上挤满了将去天南海北的乘客。妈妈穿过混杂的人群,在候车厅的角落里寻到了一方空地。她将笨重的行李搁下,示意我坐在柔软的包裹上。我没有推让,我知道,此刻一切的推让都等于无用。
她在候车厅里走了半天,终于捡到了一张废弃的报纸。待她席地而坐之后,我便将背包里的白手帕递给她,她笑笑说:“你一路上还得用呢,要是被我弄脏了,你在众人面前掏出来多难为情。”话毕,她自顾抬起粗糙的袖管,擦拭额头上的滚滚汗珠与鼻翼两侧的风尘。
她令我前去买了站台票,她说务必要将我送上列车。她又忘了,我所乘坐的列车要凌晨才会到达,而凌晨,便又意味着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