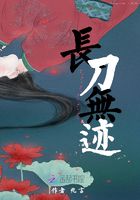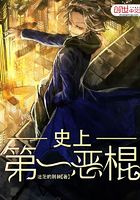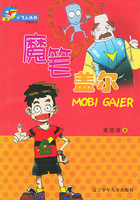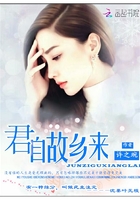王元化先生是当代精神生活中一棵参天大树。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也是毕生倡导独立思考的人。在他去世以后,对他的最好纪念,我以为,莫过于像他那样去思考。至少,我们目前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当代精神生活史上,他何以居于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哪些成就是别人可以取代的,哪些则是谁也无法取代的?他的最重要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最早,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是一个青年作家,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作品后来大多编入小说散文集《脚踪》。这些作品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几乎在这同时,他以各种笔名撰写理论批评文章,开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到1952年,当这些理论批评文章集为一部《向着真实》出版时,他在文坛的影响已经相当大了。三年后,反胡风运动席卷全国,在他即将被打成胡风分子时,周扬曾惋惜地表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周并未能挽救他的厄运,但从周扬的话里已能掂出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分量。我觉得,当时他其实已和解放区来的、应该说是红得发紫的文艺批评家陈涌齐名了。虽说《向着真实》只是一本薄薄的书,但那时的理论书都很薄,陈涌的批评集子几乎都要比这一本单薄许多。那时两人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也有不少相通之处,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如关于创作主体的重要性等)。陈涌是批胡风运动的积极分子,可在反右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帽子。两人复出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时他们在思想观点和学术能力上的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陈涌渐渐被人遗忘;元化先生的后劲却越来越足——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水准出现的生气勃勃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操着陈旧批评武器的眼界局促的写作者。
元化先生后来自己表示,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工作,也不能再写评论文章了,这才促使他沉下心来,大量读书,从事学术研究。他被安排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在郭绍虞教授指导下研读《文心雕龙》。他从小在清华园受到潜移默化而养成的,那种学术的向往和潜质,这时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写出一篇篇思维细密严谨而又充满创见的论文,令郭绍虞等前辈惊讶赞叹,郭认为:“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元化先生的兴趣在剖析《文心雕龙》中有关艺术规律、艺术方法的命题,尤其是从中发掘现有的文艺理论中所忽略的东西或中国古代与西方美学(比如他所熟悉的黑格尔美学)所暗合的东西。我以为,元化先生后来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在这一时期已经显露出来了。他不喜欢陈词滥调,不屑于人云亦云,别人已发现的他没有必要再写,一旦下笔为文就一定要真有自己的心得;他喜欢高度抽象的思辨,在纯理论领域探幽析微是他最乐意的工作,而这时他又心细如发,决不容忍半点轻率和粗疏。在他复出后,这些论文公之于世,其中如《刘勰的虚静说》、《陆机的感性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释体性篇才性说》、《释情采篇情志说》等,均让人耳目一新,它们为文艺学和美学开拓了新的境界。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和发现,仍然让人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新意。对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补订也是元化先生治学的特色,他的这组研究成果最早以《文心雕龙创作论》于1979年出版,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了文艺理论界与古典文学研究界,他后来又一再推敲,到1997年才作为定稿,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重新出版。在元化先生一生中,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主要就是这一部。
也就在这一段“靠边”的岁月里,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勤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训练。他向父执辈的韦卓民教授请益,在与他通讯交往中研读黑格尔,对黑格尔《小逻辑》与《美学》二书用力最勤,后来影印出版的《读黑格尔》就是他那一时期的笔记。经韦卓民介绍,他又向熊十力先生求教,在熊的指导下研读佛教哲学,读《佛家名相通释》。在写《文心雕龙创作论》时,他借来了库柏编译的英文本《文学风格论》,为借鉴前人的研究,他把其中的四篇论文全译了出来。他还与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二十余万字的西方学者论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正是这种中学西学齐头并进的埋头苦修,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王元化。
元化先生复出之初,在文艺界的一些会议上亮相发言,每每语惊四座,让人惊叹上海居然还有如此了得的人。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听过他两次发言,一次是谈黑格尔美学与《文心雕龙》,其中说及“情志”的概念,至今印象深刻;另一次是谈鲁迅,也是新意迭出,这好像就是后来整理成文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随后,又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读到他的论文,最受震撼的是《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它对传统的认识论与文艺学,都有一种涉及根本的冲击力。接着就买到了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与新出的修订版《向着真实》,渐渐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的他,主要还是一个有着浓厚哲学兴趣的文艺理论家,但在深度上和观念的新颖上,则远非文艺理论界的同行们所可比拟。当时凡有他的文章,我几乎一篇不拉地拿来细读,即片言只语的报道也不肯放过。我发现,他的长处并不在于对具体作品的鉴赏,要说艺术体验的细切深透,他可能不如钱谷融先生。记得他曾对作家水运宪的某一中篇小说大加激赏,这一作品的概念大于形象,后来事实也证明它未能赢得读者的认同。(这一点在元化先生晚年又有变化,主要体现在他对京剧的品赏中)然而一旦将文艺问题上升到抽象领域,成为一种理论,那时他的辨别力就变得异常敏锐,任何一点轻微的含糊之处都能被他发现,而他的条分缕析,总能将你的思路引到一种新的高度,每每有豁然开朗的喜悦。所以他的文艺理论,更接近于艺术哲学,更应在美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能与元化先生齐名的,是北京的美学家李泽厚。
但很快,元化先生与李泽厚先生的学术兴趣都发生了转移,他们从文艺学和美学转向了思想史,着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与中西文化碰撞的课题。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新课题。李泽厚早在成为美学家之前,就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这也成为他后来的名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主干)。元化先生则除了《文心雕龙》研究,在复出之前,还写过《韩非论稿》和《龚自珍思想笔谈》等颇具分量的长文。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元化先生出访归来,在作协做完报告,我问他对于阿城小说《棋王》的看法,本以为他会从艺术上谈,不料他很有兴致地谈了小说背后寻找文化之根的倾向,美国学者杜维明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热,等等,一气谈了好久。这一次,对于他的淹博,以及善于联系广阔的文化背景思考问题的习惯,我算有了充分的领教,也仿佛第一次明白了学者和理论家之间的区别。而从中,我也看出他的思维重点已不在文艺,而在于文化的研究了。李泽厚正当壮年,思路活,下笔快,很快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又着手撰写《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元化先生则写了《传统文化中的常与变》、《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后大多收入《传统与反传统》一书。这种文化研究的热情,与当时海内外的“文化热”是同步的(作家们也纷纷在这时写起了“寻根”文学),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探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感和责任心。元化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在撰著之余,都频频接受采访,以对话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还积极从事编辑工作。李泽厚主编了一套几十种的“西方美学译丛”,想通过翻译来弥补中国学界视野的不足;元化先生则编辑了丛刊《新启蒙》。他们在当时的精神生活领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进入90年代后,李泽厚移居美国,他在国内的影响渐渐小了。元化先生编起了一套《学术集林》丛刊(同时也出丛书),其性质,与《新启蒙》大异其趣,其中包括了很多相当偏僻的学术课题(诸如《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等)。其实,他是有意要改变当下中国人的治学习惯,即粗疏、浮躁、一窝蜂和“意图伦理”。他想用提倡真正的学术精神来慢慢改变这一切;而他从小在清华园养成的学术兴趣,也在编这套丛刊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当年研究《文心雕龙》时,他得到过这种满足。为什么每当不处于顺境,总会通过这种源于童年的学术情结以获得消解?这也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吧。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他在认真编这套《学术集林》时,自己写的这类纯学术文章并不多,只写了每一辑的“编后记”及一些“与友人书”,从中谈一点关于学风和学术的看法,以及近期的思考。他的这一工作也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批评,他们觉得自己心目中的元化先生变了,变得消沉了,沉入到纯学术中去了。于是有人提出,现在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针对这一点,他作了有力的辩解。他认为,不应将这二者截然分开,现在要提倡的,应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一观点,得到了知识界较为普遍的赞同。
那么这段时间,元化先生究竟在干什么呢?编刊只可能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永远是思考和写作,而这段时间,他正进行着一生中最紧张的思考——他在反思。我以为,元化先生之所以会有现在这样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了这一段的反思。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把自己所崇仰的一切,把中国传统中被尊崇被颠覆的一切,统统进行了一番新的衡量和思考。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也是神圣的。这以后,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它们在思想界不断引起新的震动(这些文章大多收入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一书)。其中有《杜亚泉与中西文化论战》,牵涉对“五四”反传统与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涉及对激进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对“五四”的思考》与《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明确提出了对“五四”的新的评价;《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涉及民主与国家权力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文章中,还分明带出了对鲁迅的评价问题。这些文章的逐一发表,几乎都成了中国思想界令人难忘的“事件”。
我在想,虽然元化先生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但这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在他去世之后,有好几位朋友问起:你看他主要是一位学人呢,还是一位思想家?这其实也就是说,他或他的文章,是偏于这两句中的前一句,还是后一句?我以为,他主要还是偏于“有学术的思想”,他的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位思想家。他不同于那些单纯政治性的喜欢振臂一呼的思想者,他更专注于“有学术的思想”;他也不同于那些“有思想的学问家”——他们的兴趣和工作落点还是在学问。元化先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就是作为一个注重学术思维的、有极高学术含量的重要思想家。这也就是他的无可取代之处。
具体地说,我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使元化先生区别于其他的学问家和思想者,而这四点,也正是我们后人所应永远记取的:
一、勇于反思。他的反思是无禁区的,只以历史事实作唯一的依据,什么都不能阻止事实基础上的思想的自由驰骋。所以,他可以否定自己的许多旧说(例如对于“五四”就是)。与此堪可对照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但他很少否定自己,总是把过去的观点很巧妙地融入新说之中。
二、勇于提出明确的创见。即他在反思之后,敢下断语,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这其实不只是敢的问题,而是要有真正的构建理论的能力。仍以“五四”为例,他提出“五四”的主要成就在于个性解放,即“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主要缺失则是四个方面:庸俗进化观、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如不是大量掌握材料并有过人的理论才华,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精到的概括的。
三、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善于构建理论而又决不轻下断语,一定要把所有问题尽最大努力弄懂弄通,这是实现“有学术的思想”的唯一途径。元化先生一直说自己“看书慢”,他有时一本书可以看好几个月,原因就在这里。
四、始终关注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前文说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元化先生只有一本《文心雕龙讲疏》;他在编《学术集林》时,自己并没有写多少这样的纯学术文章。他虽有学术兴趣,但那都消融在编刊以及构建“有学术的思想”上了,他没办法在能够思想的时候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纯学术上。他多次说到,自己是个“急性子”,而他的最大的兴趣,其实也是在思考最迫切的大问题上。所以,听他谈话,即使是谈京剧,谈读书,谈故人旧事,你总能感到它们不只是闲聊,而总有现实的感悟。反过来,谈任何的理论或学术,你又总不会觉得它们只是概念的游戏,而总有十分切实的生气在。过去说“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为什么元化先生的理论总能让人觉得生气勃勃,有一种清新感人的活力呢?我以为,就因为它们总是紧扣着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他一直在紧张思考的都是与此有关的问题,他的强大的生命力早已融化在这思想和理论中了。
写于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