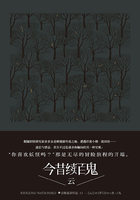她是永远也无法把自己所犯的这场错误、这荒唐无比的笑话,说给别人听的。要是她真的说了,别人会认为她也太没有教养,太不照顾别人了。而在讲述时,被误解的那一头——自杀者被轧烂的身体——似乎还不会比她自己的经血更加污秽和可怖呢。
这事可千万也别跟任何人说呀。(事实上,几年之后,她还是说了,跟一个叫克里斯塔的女人说了,不过这会儿她还不认识那女人呢。)
可是不跟别人说些什么,她心里憋得难受。她取出她的笔记本,在有格子的纸上开始给她的父母亲写信。
我们尚未抵达马尼托巴的省界,可是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埋怨风景未免太单调了,不过他们倒是没法抱怨这次旅行缺乏戏剧性的事件。今天早晨我们在北方森林上帝遗忘的一块林中空地里停了下来,这里的一切都刷成了沉闷的铁路红。我那时正坐在列车尾部的望车厢里,简直冻得半死,因为他们为了节约暖气竟把这儿的给关了(这主意必定是由这样的思路产生的:壮丽的风景能吸引住你,让你忘掉环境的不舒适),而我又懒得回去取我的套头衫。我们在那里坐了十到十五分钟,这时火车重新启动了,我可以看到火车头在前面拐弯,这时,突然间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强烈震动
她和她的父母亲一直是认真注意这样做的,但凡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便一定要带回家来告诉大家。这就需要有一种精致的判断力,不仅是对事情而且也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得有这样的判断能力。至少朱丽叶是这样认为的,当时她的世界就是学校。她让自己成为一名高屋建瓴、无懈可击的观察家。如今她虽已远离老家多年,但保持这样的姿态已经几乎习惯性地成为她的一个职责了。
可是她刚写下强烈震动这几个字,就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往下写了。再也无法用她习惯的语言写下去了。
她想看看窗子外面,但是风景已经变了,虽然仍然是由原来的基本元素构成。往前走了还不到一百英里,却仿佛已经换成了更温暖一些的气候。冰仅仅是镶嵌在湖的四周,没有覆盖住整个湖。冬云底下,黑乎乎的水和黑沉沉的岩石,使得整个气氛都显得很阴沉。她看腻了,便又捡起那本多兹的书,任意翻到一页,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她以前是读过的。每隔几页她便像是得了在文字下面乱画杠杠的毛病。她被吸引到这些段落上来,可是重新读时,她发现自己曾以为大有收获之处现在却显得晦涩不清、模棱两可。
在活着的人偏颇的眼光中看来是妖魔一般的行为,从死者更宽厚的角度看却无非是宇宙正义的一种现象。
书从她的手里滑了开去,她双目闭合,她现在是和一些孩子(是学生吧?)走在一个湖的冰面上。他们每踩一步那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五爪痕的裂纹,都很均匀,显得很美,因此冰面都成为一片铺了瓷砖的地板了。孩子们问她这些冰砖的名称,她很自信地回答说,那是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可是他们大笑,笑声使得裂痕延长了。此时她明白自己犯错误了,也知道只有说出正确的答案才能挽救局势,可是她当时没能把握住机会。
她醒了,一睁开眼就见到了那个男人,也就是她曾追踪并在车厢间用问题烦扰他的那个人,此刻他正坐在她的对面。
“你睡着了,”这么说了之后他也微微笑了,“显然是的。”
她睡着的时候头耷拉了下来,跟老太太似的,嘴角还淌出了口水,而且她知道她必须立刻就上女厕所去——但愿没有在裙子上留下点儿什么。她说了声“请原谅”(就像方才他对她说的那样),就拎着旅行包走开了,想尽量别显得太唐突与过于匆促。
她洗过、收拾过也调整好了心态走回来时,他仍然没有走开。
他马上就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得表示抱歉。
“我方才想到我对你太没有礼貌了。当时你问我——”
“是的。”她说。
“你说得没错,”他说,“你形容他模样的那些话。”
看来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礼貌的表示,不如说更像是一次直截了当且必须要作出的事务上的交代。倘若她不想说什么,他很可能也就会站起身来走开了,不至于感到特别失望,反正他走过来想做的事情他已经做了。
朱丽叶感到很羞愧,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这事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她甚至没来得及将眼睛转开。
“好了,”他说,“没事了。”
她急急地点点头,一连点了好几次,可怜巴巴地吸了吸鼻子,并且把鼻涕擤在好不容易才从手包里找出来的餐巾纸里。
“没有事了。”她说,然后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之前所发生的事。说那个男的怎样弯身问她对面的位子有人没人,他怎样坐下来,她自己又怎样一直在看窗外的景色,这时候没法再看了,她便试着或者说假装低下头看书,可他还问她在哪儿上的车,还问出了她现在住在哪个城市,而且一个劲儿要把谈话进行下去,使得她只好收拾起东西离开他。
她唯一没有告诉他的是搭伙儿聊聊这个说法。她有一种预感,一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她肯定会再一次泪流满面。
“拦住女人说话,”他说,“肯定比拦住男人更加容易些。”
“对的。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女人态度肯定会温和一些。”
“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跟他说说话罢了,”她说,立场稍稍有些改变,“他想跟人聊聊天的渴望要大过我不想和别人交谈的程度。这我现在明白了。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小气。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冷酷。可是当时我就是那样的。”
停顿了一小会儿,这时她总算再一次把鼻涕眼泪都控制住了。
他说:“你以前也想过要对什么人这样做吗?”
“是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从来没能走得这么远过。这次我为什么真的做了呢——那是因为他是那么卑微。他穿了一身新衣服,也许是专为这次出门买的。没准他很潦倒,想着还不如出门一次吧,这倒是个办法,可以遇到人,可以跟他们交上朋友。”
“没准他仅仅是短途走走——”她又说,“可是他说他是去温哥华,那样我就不得不老陪着他了。有好几天呢。”
“是的。”
“真的很有可能会是那样的。”
“是的。”
“所以啦。”
“运气太差了,”他说,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你头一回鼓起勇气让别人换换挡,可他却投身到火车底下去了。”
“很可能那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她说,此刻她稍稍有点从防御的角度出发了,“很可能是的。”
“我想你以后会更加留意的。”
朱丽叶抬起下巴,眼光定定地盯着他。
“你是说我是在夸大其词。”
这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跟她的眼泪一样突如其来、不请自来。她的嘴巴开始在扭曲了。眼看就会有一阵很不严肃的大笑爆发出来。
“我想,这事情是有一点点极端。”
他说:“是有点儿。”
“你认为我是在把事情戏剧化吧?”
“那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她说,已经把笑意控制住了,“你觉得负罪感仅仅是一种自我放纵?”
“我的感觉是——”他说,“我感觉这件事并不太重要。你的生活里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一些事情没准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相比之下这件事情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对于别的那些事情你才会产生负罪感呢。”
“不过人们不是老在这么说吗?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他们说,哦,有一天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你等着瞧好了。就像是你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严肃的感情似的。就像你没有能力这样做似的。”
“感情吗,”他说,“我方才说的是经验。”
“可是你不是等于在说有负罪感一无用处吗?大家全都这么说。难道不是吗?”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们接着谈这个话题,谈的时间不算短,用压低的声音,但是很热烈,使得经过的人有时会显得很惊讶,甚至很不以为然,就像人们耳边偶尔听到一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的抽象辩论时一样。过了片刻,朱丽叶认识到,虽然她是在论证,论证得还挺好的,她觉得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中有负罪感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她一时之间丧失了这种负罪感。你甚至可以说她是在自我欣赏呢。
他建议他们上酒吧那边去,在那儿可以喝杯咖啡。一到那边,朱丽叶才发现自己肚子很饿了,然而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棒状饼干和花生米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仅有的东西,她对着它们大嚼大咽,那副狼狈相使得方才进行的那场很有思想性的、略微有些针锋相对的辩论不可能再死灰复燃了。因此,他们就改而谈起自己来了。他的名字是埃里克·波蒂厄斯,住在一个叫鲸鱼湾的地方,在温哥华北面,就在西海岸的边上。不过他并不马上去那个地方,他要在里贾纳停上几天,去看好久未见到的几个人。他是个渔夫,以捕大虾为生。她问到他讲起的医药经验是怎么回事,他说了:“哦,算不上很广博。这方面我学过一些。你在大森林里或是在船上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就发生在你工作同伴或是你自己的身上。”
他结婚了,太太的名字叫安。
八年前,他说,安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好几个星期都昏迷不醒。后来总算是清醒过来了,但全身瘫痪,不能走动,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她像是认得他,也认得照顾她生活的那个女人,有那个女人的帮助他才能让她在家里住。可是希望她能够说话和明白周围的事情,这样的念想很快就断了。
出事的那天他们是去参加一个派对。她不怎么想去可是他想去。后来她决定独自走回家去,派对上的一些事情使得她不太愉快。
从另一个派对出来的一伙醉鬼把车子驶离了马路,撞倒了她。是些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
幸亏他和安没有小孩。是啊,真是幸运啊。
“你告诉别人这件事,他们总是感到必须说上一句,太可怕了,多么悲惨哪,等等等等。”
“可你能怪他们吗?”朱丽叶说,她自己方才也差点儿说出一句类似的话。
不能,他说。不过问题就在于,整个事情要复杂得多。他的太太安会感觉到那是一场悲剧吗?也许不会。他会吗?那是他自己必须去习惯的一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事情无非就是这样。
朱丽叶对于男人所有比较愉快的经验都是幻想式的。一两个电影明星啦,那位曼妙的男高音歌唱家啦——不是歌剧里真正的那个没有心肝的男主人公——她是从《唐璜》的一张老唱片里听到的。还有亨利五世,那是她从莎士比亚剧本里读到的,也是从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电影中看到的。
这是可笑和悲惨的,可是谁又需要知道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总免不了有屈辱性和令人失望的事,她总是设法把它们尽快从自己头脑里驱赶出去。
那样的经历还少吗?在高中舞会上想在一大堆吵吵嚷嚷没人要的女生中脱颖而出,在与大学男同学的约会中,尽管心里很厌烦却又冒冒失失地表现得格外活泼,其实她不怎么喜欢他们,他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还有去年,指导她写论文的导师有个外甥来访,她和那外甥一起外出,深夜在威利斯公园的草地上被他占了便宜——那也不能说是强奸,她自己也是下了决心的呀。
在回家的路口,他解释道,她不是适合他的那种女孩。她一棍子给打闷了,都没有想到要反驳说——当时她还没醒过味儿来呢——他也不是适合自己的男人。
她从未对一个特殊的、真正的男人有过什么幻想,更不要说是对她的任何一个老师了。在她看来,在真实的生活里,年龄比较大的男人好像都有点儿不太干净。
这个男人年纪有多大呢?他结婚至少已经有八年了——也许还得多上两三年。这么看,他总得有三十五六岁了。他头发黑黑卷卷的,两鬓稍稍有些花白,他前庭宽阔,皱纹不少,他双肩很结实,稍稍有些前伛。他身材几乎一点也不比她高。他双目隔得很开,深色的,眼神很热切,但同时也很警惕。他的下巴圆圆的,有个小凹坑,像是很好斗似的。
她告诉他自己做什么工作,学校的名称——托伦斯学校。(“你想不想打赌说那应该叫‘拖人死’学校?”)她告诉他自己并不是正式教师,但是校方能找到任何一个主修希腊语、拉丁语的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现如今简直就没人愿意学这些老古董了。
“那你干吗学呢?”
“哦,仅仅是想显得与众不同罢了,我猜。”
接下去她告诉他的,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应该告诉任何一个男人或是男孩子的,说了他们就会立刻对她不感兴趣了的。
“那是因为我喜欢。我就是喜欢和这门学问有关的一切。我真的喜欢。”
他们一起吃了晚餐,还一人喝了一杯酒,接下去他们上望车厢去,在那里,他们坐在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人。这一次朱丽叶带上了她的套头运动衫。
“人家都以为到了晚上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他说,“可是你瞧天上的星星,天气晴朗时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的确,夜空十分清明。没有月亮,至少是还未升起,星星或明或暗聚成团地辉耀着。就像每一个在船上生活与工作过的人一样,他对头顶上的那幅地图熟悉得很。而她呢,能认出来的只有那只大勺子[11]。
“这可以作为你的起点,”他说,“先看勺把对面的那两颗星。看到了吧?那是个指针。顺着它们的方向。往前一点。你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如此等等。
他帮助她找到了猎户星座,那是北半球冬季最主要的星座。还有天狼星,那只大狗,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那是整片北方天空里最最明亮的星座。
朱丽叶很高兴能有人指点她,但是轮到自己当老师时她也同样高兴。他知道星座的名字却不知道它们的来历。
她告诉他猎户俄里翁的眼睛是被俄诺皮翁弄瞎的,而他的眼睛又因为盯看阳光而得以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