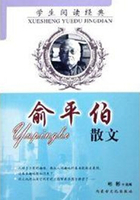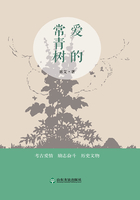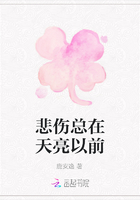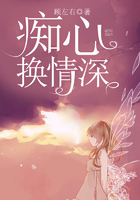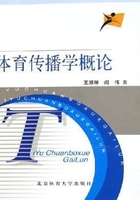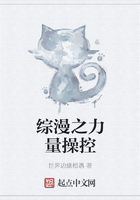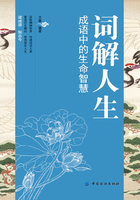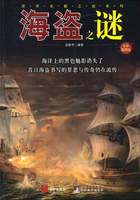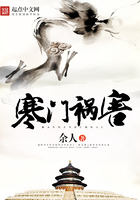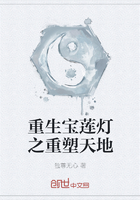假如我没弄错,“杰作”一词大约是在十八世纪中期才用于文学的,至少我找到的最早表述出自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世纪》(1752):
但我们应依据一位伟人的杰作对其进行评判,而非他的错误。
大约是在同一时期,文学的概念出现了,它将作家们从娱乐消遣行业解脱了出来。文学出现之前杰作即已存在,但与前者一样没有名称。恰恰是在获得名称的同时两者得到了拯救。事物总是经由命名获得拯救。大权在握的人们喜欢将一切新事物扔进壁橱,而一经命名,它便可从这个“无名之物”的暗橱中脱身而出。否则纵然它拥有才华,要求一席之地,又能怎样?倘若没有杰作,文学恐怕根本无法自立于世。它将杰作据为己有,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尊敬。就像一个在海滩上筑城的小男孩,文学摆出荷马,嗨哟!但丁,嗨哟!歌德,嗨哟!还有其他许多杰作,嗨哟!嗨哟!嗨哟!为自己筑就一道城墙。权贵们,杰作在此,谁敢动我!三个世纪过去了。三个世纪的杰作。可是,假如我依然没弄错,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文学杰作的书。就是因为这样,这本书里才可能出错。我权且做一名园丁,完成开荒前的清场。
比起思想,人似乎更喜欢为自己制造显而易见的事物。他对于信念支撑的需要无穷无尽。于是我们建立起文学杰作这样一个既不十分明确又难以撼动的概念。
它稳固沉静,历尽艰辛。十分符合理想中的作家形象。这一形象在十九世纪得到完善,也就是一个坐着的人。他做出手艺人的姿势,仿佛在抛光台前写作。这个形象的典范是马拉美,还有他的椅子,他那平凡却动人的工作椅,那是一个属于抄写人、史诗复写员、因专注工作而步步高升的谦逊者的座位。总而言之,平凡。我曾在2010年梅斯蓬皮杜中心[3]开幕展览时展示过这把椅子,它是塞纳—马恩省马拉美博物馆的藏品。当时我负责开幕展的文学部分,博物馆主席洛朗·勒庞把整整一个大厅托付给我,恕本人狂妄,这在我看来十分明智,因为我恰恰相信创造的各种形式是相通的。在一个颇具日本风格的仪式中——这在法国绝对罕见,因为我们对类似事物并无感觉——我亲眼看到《追忆逝水年华》的手稿在展厅中行进。国家图书馆同意出借普鲁斯特手稿的第一卷,并指派一位搬运工和一位女图书馆员将它送来。博物馆正值布展阶段,现场的混乱(即便有秩序也已散落四处)对瞻仰手稿并不十分有利。一幅巨大的西蒙·昂泰[4]的油画斜靠在一面隔墙上,像一个放学后没人来接的孩子。地板上,各式工具像鱼儿一般轻轻掠过不干胶贴纸留下的十字记号。散放在四周的木箱静静等待着,仿佛有一个身躯硕大的婴儿玩过积木把它们扔下了。一组组工作人员脚上包裹着蓝色鞋套,安静地走动,忙于各自的任务,神情专注。当《追忆逝水年华》的手稿抵达现场,展厅内出现了片刻停顿,四周鸦雀无声,一个动作随之出现。所有人都向它看去。搬运工戴着白色手套,双手平展,上面托着一个箱子。女图书馆员礼貌有加却坚定有力地向他下达着指令,他也带着崇敬的庄严和沉默一一遵照执行。他打开箱子,取出了手稿。应该就是它了,实实在在的一部文学杰作!它像一只纸做的朝鲜蓟,期待着张开叶瓣向人倾诉!果然,当搬运工把它放进玻璃橱窗,安置在我指定的地方,它就像一个刚醒来的新生儿张开了嘴。天才的新生儿,才华无法与他匹敌的我们则在发觉这份天才的时候满怀幸福。
马拉美的椅子已经运到,此刻就在我们身后,安静地等待我为它安排位置。这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藤背木椅,两支纤细的扶手,座垫下的椅腿交叉成菱形。马拉美不可能用一把“简单”的椅子。这椅子与他圆花窗式诗歌的精巧别致十分相配。他以努力勤奋获得了这种精巧别致。马拉美曾经这样答复一位记者:“每一次在文体上付诸努力,诗学必然产生。”(儒勒·于雷[5],《考察文学演变》,1891)努力。文体。端坐。马拉美地位稳固[6]并时常以坐姿示人,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坐在这把椅子上。历经几个世纪,作家的地位已经变化,但狭小的房间、书桌、固定不动的形象仍然未变。此时出现了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第五歌》(1923)。“但他们是谁?告诉我,这些流浪者,这些灵魂/比我们更加短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象牙塔走进了飞机机舱。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了三千年之后,我们开始日复一日地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为了确保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伟大的先辈们已在原先的姿势里维持了太久,现在我们可以尽情地淘气胡闹。从马拉美到马尔罗只是一瞬之间。在文学里,演变是跳跃式发生的。没有逐渐的进步。那纯粹是幻想。杰作破壳而出,如同动画片里的蘑菇。不过,经济舱的座椅也没能赶走漫长和艰苦的意象,就像榫舌和榫眼,二者密不可分。仿佛如果没有艰辛的劳动或者艰辛劳动的表象,天才便不可原谅。我们依然坐着写作(在飞机里也是),但杰作已经改变了。
从十九世纪开始,我们便遭遇了对杰作的质疑,而对杰作形式的质疑多于对概念本身。庞大厚重的杰作开始令一些人害怕,于是他们尝试创造自己的杰作。擅长冷嘲热讽的洛特雷阿蒙[7]只想写出《马尔多罗之歌》(1868)。实际上,杰作并没受到太大的质疑。在反对杰作的阵营里,安德烈·布勒东[8]本人就颇具杰作之风。他工作室的那面墙——如今已被收入蓬皮杜艺术中心——与十八世纪的一间珍奇陈列室没什么不同,仿佛出自一间雅致的门厅,布满了“我最美的中非纪念品”。他将另一个自我放进书中,仪态威严,像挥舞权杖般挥舞着手中的笔。布勒东编制过一部文集,其编纂所依据的是杰作的最高标准;他曾尝试写作“自动诗歌”,但那是为了从中提炼出夸张;更何况他的手稿还表明,写作《磁场》的过程中,他曾对自己的文稿做过订正、修饰、润色,而苏波[9]却没对自己的文稿做任何改动。“我们应该跟那种只留给所谓的精英群体,而大众都无法理解的杰作说再见……”阿尔托[10]在《剧场及其复象》(1938)中如是说。这不是在质疑杰作。这是在质疑“一种”杰作,阿拉伯语中touhfa一词最能表达它的确切含义,这个词还派生出另外一个词mathaf,意即博物馆,字面意思是“寄放杰作的地方”(Touhfa, mathaf, kessaku, jiezuo。可惜我认得的语言不如认识的朋友多。他们做我的朋友实在是品格高贵。每个民族都太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杰作)。
人们在1840年至1920年间写出了若干部或若干系列长达三千页的小说,只有游手好闲的有产者才有时间阅读。它们是杰作中的堡垒,比十八世纪末的杰作还要厚重,但后者却并不比它们缺乏精妙的构造。工程之神知道工程师头脑的拉克洛[11]是否通过《危险的关系》写出了一部工程师式的小说;上帝知道五幕悲剧和悲剧诗是否如建筑般构造完整。可上帝并不存在,写悲剧的伏尔泰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将上帝称为“建筑师”。伏尔泰屈从于这项乐高游戏(尽管这游戏如此有悖于他可爱的神经官能症),创造出多部悲剧,其中有几部极为优秀。他也写过一些符合他紧张个性,却与繁文缛节和缓慢迟钝所支配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书。那是些像松鼠般灵巧轻便的书,一百页的世纪历史,简短的词典,以及所谓的哲学通信,实际上就是他拿手的独白,法国人称之为谈话,说穿了就是不断转换话题。它们都是那个有血有肉、名叫伏尔泰的男人的作品,写他的神经官能症,写他年轻时对跳舞的喜爱和一直存留到老的美好回忆,写他对咖啡的迷恋(“别喝这么多,伏尔泰,你会把自己害死的。——我生来就被害死了”),写他对腓特烈二世的热忱,还有对那个人的,他叫什么来着,《四季》的作者,莎特莱夫人[12]去世的时候他还大哭了一场,说“她要了我的命”![13]写他的胃病和他那颗温柔的心,人人都断定那是颗恶毒的心,可它却让他写出了这样的话:“人都会死两次,我已看清:/停止爱与停止被爱,/那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死亡;/停止生命,却算不得什么。”书籍是生动的、扣人心弦的东西,由真正的人写成。
没有作家,文学就不存在。我认为人们要谈论文学就不能不谈到作家。谈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欢笑,他们糟糕的行径和出色的表现,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品位,他们热爱的事物。我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影响我对写作所投射的理想,并且防止这种理想走向幼稚。我不希望人们谈起我的书的时候就像我什么都没做一样。但我也觉得说出下面这种话的人十分奇怪:“我啊!我的生平就是我写的书。”那他们二十五岁的时候干了什么蠢事?我们通过写书试着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无论我们的书形式如何,是长是短,是三句诗,还是三百页的小说,都要求同等的用心;这或许是神灵对我们自诩为创造者的一种报复。杰作的作者通过他们的书来嘲弄这些不存在的神灵,而他们的书则给人以神圣之感。有谁知道它们是否离神灵最近呢?又或者,它们是否最能令我们接近神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