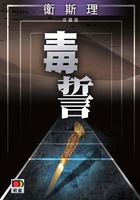小腹处的坠胀以及腿心那处的涌动似曾相识,却不似记忆中的某此那么锥心刺骨,我双手轻捧住小腹,怔怔望着前方,白茫茫模糊成一片的视线里,缓缓走来一人。
我眼都不眨一下的看着他,看他从越走越近,与李临恪擦肩而过,最终站定在我面前。其实他的功夫那么好,走路怎么会有太大的声音呢,但听在我耳中,却觉得他每一步都走得分外沉重,好像一口沉重的大钟,每一下,都正正敲击在我心底最柔软的那块肉,震撼得我手脚冰凉,全身都忍不住簌簌的抖了起来。
他好像走了很远,从一个分外冗长却甜美的梦境走进现实,那个梦是我的,眼前这份让我陌生到产生淡淡厌恶的现实,也是属于我的。
如同过去的每一次,我扬起脖颈看着他,脸上凉冰冰的一片,我看到他伸出手指过来,却感觉不到他手指接触我脸颊时肌肤相贴的温度。
我紧紧捂住小腹,手指深陷入那处软乎乎的肉里,好像在挽留那个早已不存在这个世上的小生命。我看着眼前这个在前一刻还被我当成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去爱慕、仰望、珍藏的男人,却难以控制那从骨子里泛滥而出、如同潮水一般将我湮没的恨。
我恨这个人, 在我没有失去记忆的最后一刻,但我更痛恨自己,在我恢复了全部记忆的第一个转瞬。
是我傻乎乎的将他奉为神祇顶礼膜拜,捧着一颗真心上赶着任由他人糟蹋;是我明知道不可能有回报,却依旧不知天高地厚的处处追随时时留恋,即便知道他是在利用我,也要强留下那一夜温存;是我在明知道有了孩子的情况下,宁愿牺牲掉自己和孩子两条性命,也要拯救一个从没把我放在眼里的人渣!
从头到尾,他又有什么过错!
他只是对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冷漠无情、不问不闻,他只是从不将女人这种生物看做与之平等的可以好好对待的个体,他只是把摄政王的责任地位把手里的权势金钱把其他所有一切都排在我前面,可这真的算过错么?在我与他初遇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并且从来没有过一丝半点的改变。
如果我一开始只是因为他出众的外貌而为之倾倒,那么接下来长达三年的日夜追随足以让我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我明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明知道爱上这样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所有的一切不是我自找的又是什么?!
曾经那么恨他,可还在失去意识之前说什么约定三生三世的话,到底是表达自己的不甘,还是不自量力的想给他留个念想?现在想来,还是因为爱吧。
爱的太深,太浓烈,太让人猝不及防,才会让自己一点退路都没有,在心底说怨恨,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尊严,给对方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罢了。
可在长达半年的失忆后,再重新回顾过往的所有,我更痛恨的是过去那个自己。知道这个人不可亲近,要么就远远躲开,要是舍不得,那么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都应该没有一丝埋怨的认下。路都是自己选的,到最后觉得太苦再去怨恨别人又有什么意义?
脑海里不断回放着过去三年里与他相处的点滴,对过去那个自己的愤怒、怨憎让我全然忘记了之前这个半年他对我种种的体贴温存,也忘了就在不久前还不断劝说自己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至少现在我俩是彼此属意、互相珍视的。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放着手边的温馨快意不去理会,反而任由自己沉浸在已经过去的痛苦和怨怼中难以自拔。很多时候,会选择这样做的人,是因为潜意识里想给对方一定的惩罚,让他尝尝自己吃过的苦味。殊不知,在惩罚别人的同时,也是让自己重新经历一遍所有的苦痛。
彼时我远不够豁达乐观,也早将当初那位方丈大师的好言告诫抛在脑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对,就是那个最庸俗的念头,我当初吃过的苦,也要让他尝尝!
心里这样想着,我一把打掉他为我擦泪的手,也不顾小腹的疼痛和双腿间的不适,起身就往外跑。
被他从后头搂住腰要往榻上抱,我立刻又捶又打,泼妇一样尖叫着不让他碰。他到底还是有点顾忌,松开一手来捂我的嘴,我一口咬在他虎口上,直到嘴里尝到了甜腥味都没撒开。
过了好半晌,他身体僵直贴着我后背站的一动不动,环在我腰间的手臂却渐渐松脱开了力道。我眼见机不可失,松开小犬齿,往地上啐了一口,反身狠狠推他一把,看都不想看他,使着轻功几步蹿到屋外,拽起那个深茶色的身影就往前跑。好在李大叔关键时刻还挺给力,问都没问,顺着我的手势反手拽住我的胳膊就朝着那片湖泊飞去。
他这一施上力,我是一点力气都不用出,借着之前跑起来的惯性整个人腾空而起,轻飘飘任由他拽着我跑。眼前依旧白茫茫一片,被泪水湮的看不真切远处风景,脸上也因为迎面吹拂过来的凉风有些刺痒,连带嘴唇都干裂的微微刺痛。
他带着我一口气飞出六七丈远,几句话也刚好说完:“侄媳妇儿有我带着,你小子就好好操心血灵芝的事吧!再办砸了,我看你也不用娶这媳妇儿了,反正她现在也生不了娃,大不了你再另找一个,丫头跟着我过也忒差不了……”
说完又是大笑几声,等我回过神来要反驳的时候,猛地发现我俩正行在湖泊上方,自然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闹啥别扭。身后并没有追逐过来的声响,我心里难受,也不知道是解恨还是怅然。
湖泊上停着几只小船,大叔带着我进到其中一个,拿起船桨就摇,一边还从怀里掏出个与衣裳同色的帕子扔进我怀里:“坐稳了啊,这船我也是头一回摇,你可别在这儿跟我闹气。”
我拿起帕子将整张脸抹乎一遍,又擤擤鼻涕,最后张着一双比兔子还红的眼,可怜巴巴的瞅他:“……这个搁哪儿?”
李大叔深吸一口气,咳了两嗓:“扔湖里吧。”
我把手绢一攥,很是鄙视:“多环境污染哪!”
李大叔摇着船桨的手一出溜,差点没让木浆脱手,好在人还是老当益壮,当即又一把握住拽了回来。接着就眼皮儿一抖,看都懒得看我一眼:“那就揣你自个儿怀里。”
我立刻双手环胸,手绢也不要了,一脸警惕的瞪他。
大叔嗤了一声,划桨的动作比之前顺畅不少:“怎么,跟着我不好么?”
“我可比我那个侄子强多了,跟过我的女人,可没一个不念我好的。”
我嘴一撇:“那怎么一个都没留住,到这把岁数还孤家寡人?”
李大叔巧言令色,擅长诡辩:“我要是有媳妇儿了,还轮得着你这小丫头片子坐我的船?”
我坚贞不屈,誓要划清界限:“我就是不跟他,也不可能跟您,天底下又不是除了西夏人就没别的男人!”
美大叔眯眼一笑,格外阴险:“哟,这是瞧上哪个倒霉小子了?”
我还没来得及还口,他又来了句:“不会是你们那个什么账房先生吧?”
他这一说,我倒是回想起打从我失忆这半年,徐梓溪三番两次的温言示好,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倒不觉得怎样,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分外别扭。
他见我不说话,还以为是说到点子上了,又啧啧道:“一个软趴趴的书生,有什么好的。不说别的,光是床上,绝对比不上我们家的小子!”
我听得脸上发烫,狠狠白瞪他一眼:“您……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么,有长辈这么跟小辈儿讲话的么。”
他啧了一声,脸不红气不喘的教育我:“就因为是长辈,才跟你讲大实话。”
“那小子过去是不咋地,打小让他爹给炼的面无表情,我见了都想扇他两巴掌。不过自打……”
我赶紧叫停,扭脸看远处山水:“您能不提他么!”
大叔停顿片刻,又开腔了,不过他说话的嗓音确实好听,只要他不提那个人,我还挺愿意听他瞎墨迹的:“丫头,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我朝着船头行进的方向望了一眼,发现我们已经行入一条两边是山壁的小溪流,两面高峰俊显,看得人一阵心慌,好在水流却不湍急。这船只虽小,却也结识,李大叔船划的也好,因此一路行来,倒也平稳的很。
我想了想,问他:“前头通向哪里?”
李临恪显然对这条路很是熟稔:“前头有个三岔口,继续往前再行一段,便又一圈绕回谷里。往南往北都能进城,不过方向不同。”
“那进城吧。”
总说桐城富庶,可桐城具体啥样,我见都没见过。听闻李临恪游历天下,想来淘换点好吃好喝好风光也是极有经验的,这一路有他作陪,想来不会太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