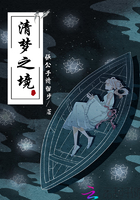子谦的目光在两人身上一打转,便明白了什么,嘴角噙起洞若观火的笑,无所谓似的把话题引到别处:“夫人,你是叫何漱衣吧,梨花谷的梨花巫?”
何漱衣的思绪自然被引走,“嗯。”问道:“小公子也是七花谷中人吧。”
“我来自河洛国的昙花谷,谷主司命夫人是我师父,‘子谦’是她给我取的表字。”
既是司命夫人的男弟子,那这子谦,应该就是列国闻名的“司命公子”了。
世人之所以称他们的“司命”,便是因他们的武功路子是以银线绞杀敌人。这些年不知多少高手栽在这一招上,宛如是被决定了命运的提线皮影。
然这子谦观来,倒是毫无杀戮戾气,反是超然于纷争之外,有些游戏人间的味道。
他吃了个莲子,笑盈盈道:“人生短短几十载,何苦让自己不开心呢?你们还不算很了解对方吧,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磨合。没法一蹴而就的事,就不必多想。顺其自然,结果未必不好。”
这样的话语,竟然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说出来的,何漱衣有点不敢相信。
她淡淡道:“原来你心如明镜。”
“嘿嘿,过奖、过奖。”子谦大概是被夸得不好意思,摸了摸后脑勺。正要再吃个莲子,不想雪貂闪闪凑过来,按住他手里的筷子,作势要把莲子打落。
子谦无奈一笑:“闪闪,你的莲子这么快就吃完了?”
“嗷嗷、嗷!”把你的莲子给我!
子谦本想不理会它,但闪闪使劲扒他的筷子,还张嘴要咬。子谦只好笑笑,把自己这碗冰糖湘莲也给了闪闪。闪闪乐坏了,脑袋都快钻进碗里去,又是一场大快朵颐。
在这南歌子客栈用过冰糖湘莲后,谢珩把子谦请去国师府。
因知道何漱衣的心情不好,谢珩一路上都在安慰她,柔情软语,邪魅调弄,才换得何漱衣的眼神微微亮了些。
抵达国师府,府中已有访客在等待主人回归。
这访客不是别个,竟是穿常服的皇帝,戴着顶有点歪斜的乌纱帽,因等谢珩等的无聊,居然和安安玩起了翻绳的游戏。
“皇帝哥哥,你又翻成死结了,你已经连输给安安七次了!”
这就是谢珩他们走进正厅时,见到的场面。
安安得意的甩着红绳,说道:“我们约好的,谁先输够七次,就要付给对方十两银子。皇帝哥哥,快给安安银子吧,谢珩哥哥和漱衣姐姐都很需要银两呢!”
对皇帝来说,十两银子还不跟石头似的?随手一甩,就赏给安安了。
皇帝道:“真是个贴心的幺妹啊!谢珩老弟怎么就这么有福气呢?媳妇好、妹妹也好,再看看朕的媳妇和妹妹……”那是何等的惆怅。
“你来做什么?”谢珩不客气的问道。
皇帝似也习惯谢珩这态度,不以为意,却是打量着何漱衣,眼底有明显的猜疑和不能置信。
谢珩威胁:“你眼睛是不想要了?”
皇帝心下一凛,忙摆摆手说:“不是、不是,朕只是没想到,你夫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梨花巫。”
谢珩的脸色顿时一紧,问皇帝:“你从何而知?”
“白教。”皇帝说:“今早你带着夫人进宫见朕那会儿,朕就想说这件事呢,却被御妹给打断了。要不朕跑你这里来做啥?不就是为了和你讲这事的?”
“这么重要的事,你就不能一开始说吗?”谢珩用一种“你真不识好歹”的目光凌迟皇帝。
皇帝颤抖了下,是真的觉得谢珩老弟有时候样子好可怕,就像是下一刻就会把人咬得尸骨无存那样,他这当皇帝的也招架不住。
他道:“前两天白教的使者来宫里了,说是奉教主的命令,要求这次腊祭典礼不能由老弟你一人主持,而是要加上你夫人一起。他们说,你夫人是梨花巫,名声不好,白教希望借此机会洗白你夫人的名声,让百姓们能另眼看她。朕很吃惊,就赶紧征求了黑教那边的看法……杨显同意让你们两个一起主持祭祀。”
谢珩和何漱衣的心里,疑惑不断涌动。
往年的跳腊大祀,都是由在任国师一人主持,这次白教想要破例,虽说不是不可以,但是,为何要为了一个不在白教任职、且臭名昭著的梨花巫而大费气力?
“还有一件事呢。”皇帝又道:“白教的教主已经来乾州了,要亲自观看腊祭。”
这的确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黑白两教的教主,向来是个谜,除了他们的心腹,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甚至连他们的年龄和性别都不知道。
何漱衣不明白,那样一个与她完全没有交集的人,为什么要特意为她洗白,还专程来看腊祭?
她问:“能引荐我去见白教教主吗?微哥哥曾说他在白教中任职,我想可能是他和教主说了什么。”
皇帝露出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抱歉,朕也很想帮你,但是奈何没办法。白教教主是让使者跟朕联络的,那些使者来去无踪。”
何漱衣的神情凝重,蹙起眉头。
皇帝叹着气安慰:“唉,想那么多也没用是不是?还是专心准备腊祭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自然会什么都清楚的。”
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
湘国百姓在这个月里,要酿酒、生火、用烟熏走老鼠、清扫垃圾、准备美酒、日杀羔羊。不但要祭祖,还要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而皇族与黑白两教更要举行大典,祭神,驱傩。
早在刚入腊月,国师府除了准备典礼,也在准备自家的腊祭。何漱衣体谅谢珩的“穷酸节约”,在自家腊祭的置备上,没有奢华大办,只是让温茗置备了一些必须品。
谢天谢地还去城郊猎来些野味,交给天嫂地嫂,制成腊肉,庆祝丰收。
三戌之日,乾州举行祭祀大典。
谢珩黑衣加身,披一件拖地斗篷,斗篷上九黎的图腾鲜艳如血。
他主持驱疫行傩,有黑教巫师头戴大红头帻,穿皂青衣,手持大兆鼓,跳着巫舞。主舞者扮演驱邪之神方相氏,头戴面具,身披熊皮,手持戈矛盾牌,同时率领十二人扮成的野兽与诸多男觋呼喊舞蹈,击鼓而行,气势震撼。
驱邪罢,便是祈年求福。
何漱衣领三十六位白教女巫,翩翩起舞。
这是何漱衣两年多来第一次恢复梨花巫的装扮,全城百姓无不对她探讨议论。有国师和白教扶持她,百姓们或多或少的被洗脑,不再用看赶尸女的鄙视眼光看她,而是渐渐的充满了敬佩。
在他们眼中,这位国师夫人正在与神灵相通,为他们祈福。但在谢珩眼里,他看到的只是他的爱妻,那么空灵美丽,仙姿玉骨。
这么冷的天,她为了跳巫舞,只穿着件雪色的广袖薄罗长衫,内里的抹胸和素雪绢裙同是雪白,在胸口用白丝线绣出湘国信仰的蝴蝶图腾。
她很冷吧?祭台是高地,风大,她的身体受得了吗?
明知祭祀之时,该心无杂念,可谢珩还是一股脑的扎进对她的担心中。
何漱衣忽而朝着他睇来一眼,印着血梨花纹样的白色面纱,轻轻起伏。
只一个眼神,谢珩就明白,她在让他放心。她眼角飞起微微笑意,那颗险危危的桃花泪痣,惊艳不可方物。
在三十六位女巫的簇拥下,她踏着巫步,折腰、翘袖,用那空灵有质的声音,诵念祈福颂词。
每一个动作,都精妙绝伦,发髻上缀着的三朵血梨花,轻动翩跹。她像是浅浅雨色中的莲河,像是薄雾空蒙中的孤山……
最后,女巫们散去,祭台上只剩下她和谢珩。
谢珩牵住她的手,高举过头顶,祭台下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一时之间,满城之人皆若狂。
远方的三层酒肆,早已空荡无人,唯有三层的阳台栏杆旁,立着一个如竹清逸的男子,正望着祭台上的景象,眼底泛开一片浓墨重彩般的情绪。
“漱衣,我来接你了。”
他朝着那缥缈若仙的白衣女子,轻轻说道,可他的视线,却紧锁着祭台上两人牵系的双手……
午时前夕,祭祀典礼结束。
谢天谢地早就在马车里铺了厚厚的皮毛垫子,谢珩一进车厢,就把何漱衣放在软垫子上,拿起她的胳膊给她按摩,按摩的差不多了,就又把她的腿抱起来揉捏。
何漱衣被伺候的很舒适,姿态也多出几分慵懒,干脆倚在那里任谢珩温柔对待。
“冷坏了吧,宝贝?”谢珩不知从哪里搞出一杯热羊奶,“来,喝点。”
“唔……好。”何漱衣懒洋洋的接过,很鲜美啊。
谢珩见她享受到了美味,心里一喜,按摩的更殷勤了,回国师府后,又把何漱衣抱到躺椅上,继续揉捏她的关节。
何漱衣趴在谢珩身上,舒服的都快要睡去。可偏在这时,有人破门而入。
谢珩不悦的望去,见破门的竟是温茗,而温茗此时的神情,十分的不淡定。
“国师,夫人,有人前来拜访,他说他是……白教教主宋豫。”